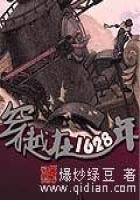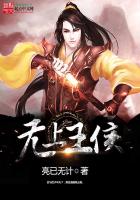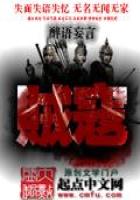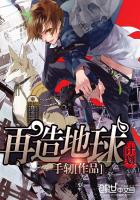郭万新
去年11月中旬的一天,张发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坐着大巴正从太原往山阴县赶来。我问他到山阴干什么,他说写了一部以山阴农村干部彭云为素材的电影文学剧本《山阴好人》,打算征求当地有关人士的意见,并希望我也能帮他看看。
张发先生曾经是山西省作家协会大型文学杂志《黄河》的主编,一直甘为人梯热心培养作者,在文学界德高望重,素有“大侠”之名。像我之前陆续写过的中篇小说《初一到十五》、《遥远的红嫁衣》以及人物传记《正说尉迟恭》等,也都是经张先生看中,在《黄河》发表推出的,所以在我心中,他是难得的良师,而且多年相处下来,感觉和亲人一样。现在听闻张先生要来,我立即决定赶去见他,心想或许能为他做些什么。
我们在山阴县政府对面的一家宾馆见面了,只见他风尘仆仆,自己拉一个不大的旅行包,显得形单影只。刚刚寒暄几句,他就兴致勃勃和我说起下喇叭乡口子梁村支部书记彭云的故事,如何如何生动感人,如何如何让他激动。彭云我也知道,是山阴县和朔州市树立的一位先进模范人物,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后受到媒体广泛宣传。交谈中得知,他是从市文联王平主席那里知道彭云事迹的,受了感动,生发了创作激情,而且我知道,他本人的老家就在朔州,他对这方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才决定创作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从而有了他的山阴之行。
这类创作,不是应邀而来,也不是作家协会指派,纯属个人行为,地方上不同于圈子里,谁知道他张发的大名?虽然山阴县长南志中也是知名文化人,但他一定是日理万机,谁知道有没有时间见面?反正我发现除了县委组织部一位小后生接待张先生,连文联的相关人员都没见惯例陪同。难免让我感觉,张先生所受礼遇与他的身份有些不符。张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说,南县长和他是几十年前就相识的老朋友,上次来,已经跟县委组织部打了招呼,孟福荣部长亲自为他的采访作了周到的安排,下喇叭乡的薛拉格书记、徐晓圆副乡长也都非常热情地陪着进行过采访。
进了房间,张先生马上打开他那老式的手提电脑,翻出文档让我阅读。我一边看,一边听他说起写作过程。他说上次来就去过口子梁两次,进行了深入采访,返回家后激情如潮,每天足不出户趴在电脑前埋头苦干,不到十天就完成了三万多字的剧本《山阴好人》。张先生的出手速度令我吃惊,因为他那码字功夫实在不敢恭维,连双拼都不会,只能用一根指头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打,可见《山阴好人》的问世绝非轻而易举。再看他那电脑,屏幕都是咳嗽上去的唾沫星点,乌七八糟的,证明写作时抽烟无数,我拿两张纸巾都没有擦干净。
开始时,我并不看好张先生的剧本。其一,因为曾经听人不屑一顾地说过,彭云并没有做出什么有分量的工作业绩,比如村民的PCDI啊,比如发展了什么产业啊等等,均在偏远的口子梁没啥体现,那不就是个留守村么?其二,据悉,著名大导演张绍林已带领他的编创团队来过山阴,对编写彭云剧本及拍摄电视剧有了意向。因此,即使张发先生写好了剧本,可能也慢了一步,无法搬上屏幕。我把这两层意思跟张先生讲了,他倒丝毫没啥担忧,说:“你先看完再说吧。我只是想把彭云的故事用最合适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至于拍成拍不成电影,先不想那么多。”
我就继续看下去。没想到当我进入张先生笔下营造的场景和细节中时,才知道我错了。我发现,彭云对一个贫瘠山村的坚守、对一群孤寡老者的关怀、对他自己及家人的付出和牺牲,无不闪现着品德的光芒,这样的好人难能可贵。从而我想到一个命题:为什么我们非要把崇高上升到不平凡的高度?随着城市化进程,年轻人都进城打工谋生,许多小村庄几乎都被边缘化了,而留下的老弱病残谁来负责呢?城里也能接纳他们并给他们一块立锥之地么?就像口子梁村,彭云辛辛苦苦引来一股清泉解决了村民的吃水,难道真的就不如官员在任上建起一幢漂亮的标志性的形象建筑重要?彭云把自己的一车炭让给更需要温暖的村民度过寒冬,难道跟电影明星高调掏出的十万元百万元捐资济贫相比真的就微不足道?难道感动人、感动中国,非得是叱咤风云的英雄?
当然,我这些反诘句的运用,并不是为了夸赞彭云。我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评说,《山阴好人》无疑是一部沉甸甸的含金量很高的作品,无论人物形象和布局结构,无论选题和艺术感染,都可称为成功的范本。归纳原因,撇开张先生是内中高手不说,关键是它来源于社会的最底层,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来源于作者质朴的人文情怀。
不由得回想起十几年前,我在太原参加省作协组织的青年作家创作会,曾经听张发先生谈起过关于文学的走向。他给我读了一条很时髦的短信,大意说写作“不是记录一场冒险,而是进行一场冒险的记录”,指的是许多年轻作家写小说时刻意淡化故事情节,着重追求文字艺术,故意让人看不懂,也就显得高深莫测水准不凡了。作为当时涌动的一道文学暗流,大有变成主流之势,甚嚣尘上。但我肯定是搞不来的,只好中断了自己的小说创作,同时也愤愤的,心想脱离生活一味玩弄文字游戏,或者挖空心思胡编乱造一些类似意淫的和男盗女娼的闹剧,怎么能为大众所接受?硬生生要把文学推向边缘化和妖魔化啊。而张先生身为大型文学杂志主编,也不知是怎么想的,我又不好问他。当我看完他的《山阴好人》,忽然间好像得到答案。在他挥洒的行文中,那一草一木的乡土风景,那弥漫着的熟悉的泥土气息,那坚韧乐观的父老乡亲,无不亲切而鲜活地再现于我们眼前,同时也已赋予了《山阴好人》强大的生命力。应该感谢张发先生,他以他的文学自觉,他以一位资深文学前辈的执着和实践,告诉了我,什么是文学创作的方向和真谛。
我是农村出来的,我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作家韩少功说过:“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这是我们的安慰和希望。”还是回归城镇化这一话题,不管将来城镇化进展到何等程度,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文学之根,不能说非得盯着农村,起码也要像张先生践行的那样: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是我阅读了《山阴好人》的又一番感慨,只是涉及到文学理论,不一定完全准确吧。虽然我不能在张先生面前班门弄斧高谈阔论,但不影响我对他创作出《山阴好人》而倍感高兴,倍感开心。
那天我和张发先生分开后,他留在山阴县全心身投入对《山阴好人》的精益求精。听说他后来又去口子梁采访过几次,如他在剧本的后记里所说:“……受到了村民们一次次热情的接待。我吃他们的饭,睡他们的炕,听他们叙说‘当家人’的往事。”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回到省作家协会后,他前前后后请了将近数十人对作品进行了品评,其中,不乏一些大腕作家和评论家。张先生还特意把南志中县长审读剧本的批语发给我:“深挖彭云这个人物。展示时代,展示社会,展示人性,展示生活(晋北风土),展示人物性格,还有空间。积淀了几千年,沉默了几千年,晋北一个贫困小山村,是出一个故事,出一个人物,出一部伟大的艺术品的时候了。看张大作家!”“打月饼一定要写好,充分反映民风民俗和其乐融融的生活。”想不到南大县长从政多年,谈及一部剧作,还是比较在行,比较地道,也切中了当下文学创作的要害,不由得让人起敬。
最近得知,《山阴好人》已经在《中国作家》影视版今年第一期发表。随即,张发先生集思广益,对剧本进行了第六次修改,先是更名《口子梁上的云》,继而改为《留守书记》,可能为了更具时代特色。而有关方面也准备于近期召开一次研讨会,请更多的业内人士给剧本把脉,以期尽快得到开机拍摄的机会。
虽说拍不拍电影另当别论,但我还是真心期待有一天看到这部电影——《留守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