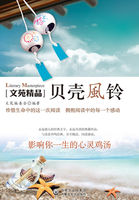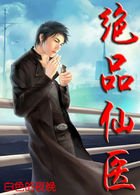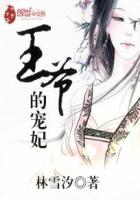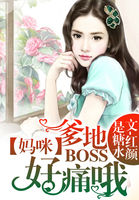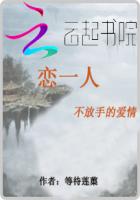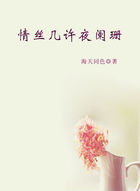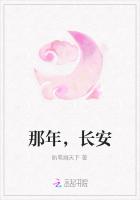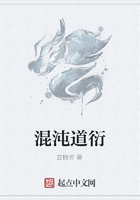陈希我
我曾经应邀到一所中学讲座,来的基本是文学少年,他们是来听作家鼓励的。可是,我却告诉他们,写作对人生是有害的。提问环节,有学生问:那么如何能既写作又不遭到伤害?我答:到《读者》为止。大家大笑。我知道,文学写作者基本对《读者》的趣味不认可。但是不可否认,《读者》确实能让你“诗意地栖居”。“诗意地栖居”是海德格尔借用荷尔德林的诗句,在纳粹时代活得滋润的海德格尔,“诗意”当然是可能的,但这不是文学的“诗意”。文学写作者应该明白: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
3年前,在学院的要求下,我开了一门文学创作课程。开设这课程,我极为犹豫。在我看来,在这急功近利的时代,学生学习写文学作品,不如学习写论文;学习写论文,又不如学习写公文。所以第一节课,我就把丑话说在前头:一,我不能教,鲁迅说过,教人写作的是骗子,我不想当骗子;二,我不敢教,因为写作会害了你们。确实,要毁掉一个人,就让他爱文学。我见过无数被文学害了误了的人。
文学(乃至人文科学)跟自然科学一样,都求“真”,但文学的求真却是对“真”的无休止的纠缠。自然科学追求“真”是理性的,但文学是非理性的。自然科学总是雄心勃勃说:“我能够!”文学总是忧心忡忡怀疑:“我能吗?”自然科学牵着人类向前奔跑,文学则拖着人类步伐,不停地问:“我是谁?”“我在哪里?”“为什么?”所以文学是可怕的,它与其说是追求客观的“真”,毋宁是沉湎于自我的纠结中,那才能成就“美”的感觉。这种情况下,“美”成了《金阁寺》里那个阻碍沟口生存的金阁寺,成了“恶”。当然,自然科学也不那么令人惬意,“真”是不能一追到底的。鲁迅在《立论》里说了一个故事:一个人家里生了孩子,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得到了感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他被大家合力痛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所以,我们归根结底也是不需要“真”的,处在“真”的世界是可怕的,我们将一刻也不得安宁。所以我们必须有宗教,由它来淡化“真”,给人慰藉,那是“善”。有人说,文学也具有慰藉功能,但通过文学来达到慰藉,基本是饮鸩止渴。
既知文学有害,那么我自己为什么要写作?因为被套住了。当然,更因为写作让人受苦,因而也让生命获得丰富。虽然“头脑简单是多么的幸福”,但是没有谁愿意当个傻子。写作让我体验到了生命的丰富性。我欣喜地看到,这次获奖的不少作品,也有着丰富的生命体验。我读到了这样的诗句:“仿佛身体从来就都不是自己的/以致有人害怕拥有/仿佛时间从来只能属于他人/顺从内心之时反而如履薄冰”(卢悦宁《私奔》);我听到了向疯癫发问:“你疯了吗?/我没疯。/你疯了吗?/我疯了。/说疯了的人是真没疯。”(祝瑞娟《神经病》);我跟着一个木讷的人去探病,用眼睛跟病人交流,体会到了这种无声的表达跟能言无语“简直像是天堂之于地狱”(唐诗人《探病》);我看到了这样的微笑:“……微笑着打扫着敬老院/微笑着面对人来人往/微笑直到死去。/总是要死的,但是谁也不能强迫我失去我的微笑/就像泛黄的我和我丈夫的遗像被儿媳妇端正地摆在正厅中央/她后悔得哭的时候,我在她身体上方,微笑着看着她/即使她看不见我/我用微笑告慰灵魂,笑又不分生死。”(余振光《冢》);我还看到了向隐秘区域探索的努力(颜炳胜《记忆的永恒》……看到这些,我的心情可以用舒婷的诗句来表达:“一半为你担忧,一半为你骄傲。”
但是我还是担忧,是对写作本身的担忧。虽然我看到了向孤独敬礼(高沁《孤独的大多数》),但我看到了更多作品,思维还是比较贫乏,对世界的理解还太扁平。当然,毕竟作者还是学生,还年轻,但是有些思维定势似乎恰是年轻时、甚至年幼时被塑造了的,比如道德化、致用化地理解文学。我们从小学到中学,都被这种评判取向所引导,所谓文学,只不过是世俗培养计划之下的奴仆课程。我记得我中学时,就有老师告诫我,如果你不能端正好思想,到了大学,对图书馆里的那些书,就不能分辨出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你的人生就会走邪路。这种教育理念,现在仍然没改变。看看给学生什么样的文学食物:我们的中小学教材,基本上是二三流作家的作品,或者是一流作家的二三流作品。我们的学生从小就是被这样的养料培育出来的。所以当他们接触到真正好作品,只会惊惶失措,无所适从。比如经常有学生问我,某个作品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指导意义?又比如有的学生跟我谈起作品中的人物,在意的是他们做得对不对?符合不符合道德?甚至是好人还是坏人?不少人认为文学就是歌颂“真善美”、批判“假丑恶”,丝毫不知“真善美”与“假丑恶”之间并非“二元对立”,它们的关系是十分吊诡的……即便是入选此书的作品,也不少陷入了这种误区。
还有“文学反映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教科书仍然灌输学生,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虽然授课教师企图脱出这个窠臼,但是教科书摆在那里,“紧箍咒”仍在。在这样的思维下,是无法阅读《地下图书馆之最后一个见证人》(王晨旭)的,更不可能去写这样的作品了。
常有学生问我:文学有什么用?我说: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用。文学是不讲世俗价值的,文学不是比进步、比科学、比道德,更不是比赢——要比赢,可以去当官员、商人、专家。文学是比弱的,它亮出的是软肋,那也是我们最隐秘的部位。如果一定要问文学有什么用,那么,文学是告诉我们,世俗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因此,文学的逻辑也不是世俗的逻辑。曾经在一所大学演讲,有学生站起来问我:按你的理论,你是个作家,等下散场,大家都从门口走出去(会场在三楼),你是否要从窗户跳下去?我答:如果跳下去能成就文学,我可以跳下去。当然,我并不是说作家是疯子。所谓文学逻辑,是更本质的逻辑,它被世俗所遮蔽,作家通过他的敏锐甚至神经质,洞察到了它。洞察力,是一个优秀写作者的根本能力,当今中国文学所以不尽如人意,很大程度上就是写作者洞察力缺乏。此次作品中,我读到了这样的内容:“她越来越相信自卑者的美德/越幸福越感到孤独存在”(卢悦宁《这不过是春天》),我看到了对王子灰姑娘爱情童话的冷峻审视(刘育君《我所知道的“童话”》),但大多作品,仍然不尽如人意。也许仍应归咎于年轻?我们的作者毕竟缺乏更多的人生经验。但我不免担心,在平庸化的文学大环境下,一代代写作者,即使年岁增长,恐怕也不过是数字的增加。
我还有一个担忧。我小时候学画,我的父亲最担心的,不是学得不好,而是学“老”了。学得不好,可以继续学,“老”了则完了。丘吉尔说:一个人20岁还没成为自由派,那就是无心,30岁还不是保守派,那就是无脑。这里的“无脑”,是指理智,但这是世俗的告诫,与文学无关。对文学写作者来说,活到100岁,仍然必须具有20岁的心。永远不“老”,也就是永远不油滑。在这次阅读中,我觉察到有的作品,也有油滑的倾向。如果说陷入误区还因为被引导、被催眠,还可以“救救孩子”,那么油滑则可能无可救药。看现在的学生的文章,技巧上大多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应该承认,现在学生的总体写作能力,是比我当学生时增强了。也许有人不同意,过来人总是觉得孩子不行。想想自己当年吧,我读大学的20世纪80年代,即便是中文专业的,也不是都能拿起笔来写得有模有样的。即便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名家作品,在技术上其实也很勉强。所以当时有挟洋人的话说:中国作家在写作技术上还没有入门。这对中国作家刺激很大,于是紧张,于是检讨,于是赶紧揣摩技术。到如今,即便是初学写作者,也都能玩几手花招,就连《白鹿原》的作者,也会学着马尔克斯口气,一开头就是“许多年后……”来个“现在”、“未来”、“过去”的时空穿越。我曾经在文学杂志社当过编辑,那些不能用的稿子,都不难找到可圈可点之处。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人聪明了,中国文学也聪明了,中国人的孩子们当然也聪明了,他们写出的文章漂亮了,笔头快了。但是,也要防止肢体灵活了,就疏于过脑了。技巧固然需要,但不可迷恋技巧。迷恋了,就可能陷于奇技淫巧,成了油滑。当然这是更高的要求。就是这次获奖的作品,有的也难脱油滑。很会描情状物,很会营造气氛,很会设置情节,很会编故事,有的作品虽然企图触及禁区,但是因为情节编得太电视剧化,反而失去了力度。当油滑成了自觉,那么写作就可能变成工艺活,所谓“写作难度”就不可能了,只有技术上的难度。相比之下,我更欣赏《三喜临门》(潘晓玲)、《菊花殇》(黄永茂)那样的文字,简单而明了,质朴而有味。
但是我仍然还是骄傲的,毕竟有这么多的人拿起笔来,企图走近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有人拿起笔来追逐文学,就已经值得欣慰了。如果还有人成为文学的“殉道者”,那更值得敬佩。他们的存在,让我相信,人虽然有着求生的本能,也仍然有浪漫的天性。其实,把线性的生命历程变得波澜壮阔,把一辈子变成两辈子,哪怕刀痕处处,哪怕毁灭,也应该是值得骄傲的。这种骄傲让写作者如同扑火的飞蛾。当然,飞蛾扑火是因其复眼构造所误,写作者则应该清醒地明白自己必然要遭受的命运。你想清楚了吗?你愿意接受吗?如果你愿意,那么,我很高兴引你为同类。
最后,我想借用《没有向日葵的夏天》(吴玮珵)里的一句话来作为结束语:“如果有一天,我听到了这么一句:‘虽然你一边码字,一边流鼻涕,我依然觉得你很是文艺。’这便是我听过最动听的言语。”其实,恰是因此,才很文艺,是真文艺。真爱文学者,都会同意这是最动听的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