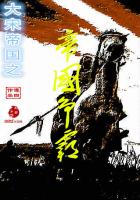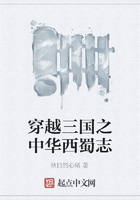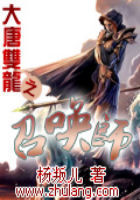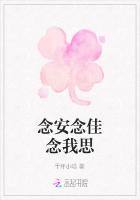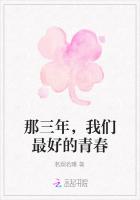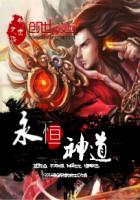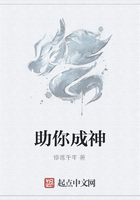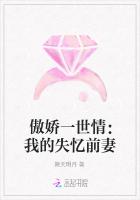1923年,张筠秋从海盐县城辍学回家,那一年她十三岁;到1937年,她二十七岁;及至1939年出嫁离开宣家浜家中,她二十九岁。整整十三年时间,若以出嫁论,则整整十五年间,在她所有的履历登记表中,只有“1923—1937年3月:海盐县西塘区宣家浜家务”寥寥不足二十字。除了前文已述的拒订婚、欲办小农场、参加“奔腾”文艺社,与闺中女友刘佩贞的交往外,——而这些也只是她日常生活中短暂的几个片断,远不是她在这十三或十五年中的生活常态。
“家务”两字,仿佛使她那段生活的记载成了一段空白,这对于一个人的经历来说,是不能容忍的阙如,——几乎囊括了她的整个青年时代。本章,我们将以张筠秋本人1950年在浙江省委党校学习时向党交心的亲笔材料为主线,辅以笔者尽力搜觅到的一切文字资料,以及知情者的口述回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她在那十余年时间里的其人其事。
张筠秋的家境情况,她自述如下:“有收租田八十亩,自耕田12亩。我们每年以分到的八十亩田剥削度日,素菜自己种的,不参加主要劳动。我们这时人口七个人和二个佣人。”
七口人是:祖母、父亲、生母、筠秋,振乾;还有两人是被长兄接济的方甫夫妇。祖母、生母死后,家庭人口变化为:父亲、继母、筠秋、振乾、继母所生的女儿大宝、二宝,失去妻子的方甫,仍为七人。
佣人是王二观和宣善祥。
1955年9月29日,中共平湖县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统一部署,制定《审查干部计划》,意欲从政治、历史上进行审查,清除混入党政机关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在这场极其严格的审查和筛选运动中,对家庭的经济情况,张筠秋仍保持1950年的说法:“我的家庭成分在表格上是填地主。家里有80亩收租。父亲又开过店等情况,我在省委党校学习时,历史材料中已写明”。
土地的数量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中,是家庭的最重要财产,为了慎重我们还查阅了张筠秋弟媳即张家唯一的媳妇刘佩贞的全部档案资料。在刘的档案中,有关张家田产数量的填写,共有五处,但数量多寡不一。少者如1950年3月25日《干部登记表》所写:“有自耕田地共拾壹亩,租入地田共伍亩叁分,尚有柒亩伍分租出田。”比较接近张筠秋说法的是1956年“审干”时写的“自耕田十六亩,还有出租田三十余亩,雇半个长年(长工)”。
1956年“审干”时,为了弄清张筠秋家庭的问题,张所在的组织进行了调查,对张家的田产也进行了核实。其中一份调查证明材料,被调查人是海盐县海塘乡十一村的陈玉亭,现择要摘录于下:“我叫陈约(玉)亭,现年62岁。我在抗战前干过伪乡长两年多,从小未出外过,在本村到现在。我所知道的张礼甫的情况……当时有100余亩田”。此份材料有“五一社长张顺金”的副署证明,还有海塘乡总支书记曹钊葆签署的“同意上述意见”文字,具有代表村、乡二级政权组织的权威性,陈玉亭当过国民党的乡长,又一直在本村居住,对情况应该是熟悉的;而解放后是新政权的“专政”对象,又使他在提供情况时,只有如实交代才能免于非祸的心态,所以“张家有田100余亩”的说法,是一种比较符合事实的说法。
质以此,张筠秋本人的“自耕田12亩,租田80亩”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而且在1950年、1956年,组织上也均未提出异议。
那么,刘佩贞对张家田产的说法为何五处各不相同,总让人有藏藏掖掖之感呢?在人被划分为阶级的时代,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事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家庭田产的拥有数量,根据“一定量的积累会引起质的变化”的哲学理论,是决定个人、家庭是人还是鬼,或者说是敌人还是朋友的生死攸关的大事。虽然张筠秋、刘佩贞都坦说自己出身、生活在地主阶级家庭(这是众所周知,无法掩饰的)。但由于当时张、刘的政治处境不一样,张在掌握政权的县级机关里工作,而刘在短暂的5个月政权机关工作后,即已被调入海盐城郊区粮库工作。再加上刘佩贞胆小敏感的个性,在田产数量上有所藏掖,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扯远一些,当时的伟人,在1935年对斯诺的自述中,即后来成书的《西行漫记》里,自称“出身于农村小地主家庭”。而1949年解放后官方对伟人的出身一律统一于“一般农民家庭”。一边是为尊者讳,一边是为自己讳,对刘佩贞的所为也确实无需苛责了。
从1923年到1937年乃至1939年,这十几年中张筠秋家的家境,也会随着时局变化、年成丰歉、家运盛衰而有些起伏。大致是:
1916年后,家境渐差,“空了几百元债,加利的”。1929—1933年,“家庭经济渐渐好转了,父亲春蚕时,在茧店做一个协理,薪俸六十元,又自己弄蚕,可一百多元收入,后来可买金镯。做酱豆(油)生意,一爿小油酱店。后来种人家租田十八亩,买荒田12亩,不还租。雇长工二个人,家又增加了三人(表妹及父的一个没有家的朋友)”。可以接纳供养着亲友,家庭财力是有点根基的宽裕了。
1933—1938年,时值战乱,“生意不好,田内亏本,弟弟生病。此时还租田不种,开支大,长工也不用。开设的油酱店被日本鬼子毁掉。一年粮食缺了一个月,因此破产卖田。”
但不管家境起伏如何,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整个经济基础是以田租收入为主要来源支撑的。用张筠秋自己的话来说是过着“不参加主要劳动,剥削度日”的日子,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诠释,“主要劳动”是指田间耕作的主要农活。
张筠秋自述中说“白天做家里的事务,晚上看书”,看来,张还是比较忙碌的,白天做家务事,只能晚上看书,那么,“白天做家里的事务”又何所指呢?
张筠秋自成年(十八周岁,1929年)至1937年谋得教师职位乃至1939年出嫁离开家庭,共8~10年中,她的自然态的生活状况,或者说她表上填写的从事“家务”,大致可以描述如下:
辅助继母魏五宝带领继母所生的两个妹妹。1929年,筠秋十八岁,大宝、二宝分别为十二岁、十岁,还是需要人照料的年龄。而在那时的社会风尚,兄姐带弟妹是常见的事,不如现在独生子女时代,一家几代人围着一根独苗转。
我们在《姐弟之恋》中,已经叙述了张筠秋缝纫衣服的事,可以想见,一家六七口的针头线脑的事,张筠秋也会张罗一些,在全凭手工缝制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针线活是相当费时间的事。鞋袜虽是小件,但自制却非易事,做鞋先要“糊百纸”,即将旧布用糨糊层层的粘贴在门板上晒干,剪成鞋底大小后,纳成密密麻麻的“千层底”。配鞋面是个技术活,讲究式样与料子。最后一道工序是“上鞋子”,可以自己上,也可以请鞋匠代劳。一双布鞋的做成,前后需七八天时间,样式上除了单鞋还有棉鞋。在买鞋穿着的今日人们看来,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浩大工程。布袜的缝制较为简单一些,然而袜底易被磨破,且稍后流行的机织棉纱袜,俗称“洋袜”,更易磨损。所以补袜子、上袜底就成了那时的一节女红常课。往往孩子一觉睡醒,主妇们还在昏黄的灯下缝补袜子。
张礼甫家没有雇女佣,一家六七口人的饭菜,农忙时人多十几个人饭菜的烹制,这是张筠秋在这十几年中必需天天做、常年做的事。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的说法,称之为“附带劳动”。当然合作者还有继母魏五宝,但相衡之下,继母还有两个孩子要哺育扶养之累,筠秋此项工作的承重决不下于继母。
据金舜仪的回忆:“张筠秋会做菜,小妹金月蜍在宣家浜出嫁时,酒席是张筠秋烧的。八样头官菜酒,八只冷盆,八只热炒。”官菜酒是平湖、海盐乡村中一种高规格的酒筵,故冠之以名曰“官菜”,技艺稍逊的厨师还不能烹制,她敢揽表妹婚宴的活,足见其厨艺非同一般。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几年的操练,也决不能技臻如此——这是张筠秋长期操持家人饭菜的佐证。
据张欣华回忆:“那时的姑母已是比较能干,处理家里的一切事务都是她。祖父说,可惜她是女儿身。”
张家开着茧行,经营着油酱铺,养过蚕,种田一项又可细分有:雇人种十二亩田,八十亩田出租,田最多时还买过十二亩荒地,租种人家十八亩田。
一家七八口的衣食住行,顾及自治委员脸面的礼尚往来……收入项中,一年生产经营计划的谋定,人员的安排,资金的调度等等。支出项中,轻重缓急的掂量摆布,各款用途的撙节,遇到突发事件时的应急,虽不属躬身劳作的“主要劳动”,或许,更是马克思所言的“复杂劳动”。“处理家中一切事务”的张筠秋,只能在晚上自修读书,是无意间毫不矫饰的真实情形的记述。
“当家姑娘”的称谓在嘉兴一带约定俗成,是对那些极能干,未出阁就在娘家持家理财的姑娘的称谓。“当家姑娘”的故事也时有耳闻,不过造就她们的情形各不相同。又一位新中国的伟人,在其幼女十二三岁时,就将夫妇两人每月的工资八百多元——那时一个工人定级后的月工资是三十元,一个定级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按老人家的一句话,大学生工资半百,被定为五十元五角——交由她安排,以历练女儿的持家管事能力。果然女儿长成后,不但持家有方,还能陪伴乃公走北巡南。伟人对女儿的安排是有意为之,而张筠秋的当家,却是事之所致。
父亲忙于主外,或者说是热衷于家外的“公务”和应酬。无暇顾全家事的具体经营。
继母魏五宝不识字,不具备担当此事的能力,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夫妻之间虽不曾反目,但也远非琴瑟相和。除了成婚拜堂时的不欢,一直在往后的口角中被妻子屡屡相讥外,婚后月余的一次争吵,更显示了两人时有的同床异梦。张欣华回忆道:“他(指张礼甫)第二次去江西是娶祖母后一个月(前妻病亡),说要再去江西看看,祖母是个通情达理之人,当时应允,而祖父却把房门一摔,负气而出。他认为女子应是依恋丈夫的,想不到这位夫人到是与平常女子非同一般。”张礼甫貌似无由的出尔反尔,妻子魏五宝的无所适从,折射了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从内心深处讲,把家事托付给女儿,父亲更放心一些。
张门独子振乾只小筠秋两岁,照理应儿子当家操持家务。但一则振乾之志,远不在齐家而在“治国”,据张筠秋在1985年12月的回忆:“张振乾三六年夏,考取了汤水湾小学,虽有了职业,……振乾一心想办好文艺社(指奔腾文艺社),汤水湾小学由我代课”。张振乾的志趣,可见一斑。再则,还有张振乾长子张欣田的回忆:“爸爸从小就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一生病往往就卧床不起,短则十天半月,长则三四个月。早晨当我睁开眼睛刚喊了声妈妈时,妈妈就跑过来嘘了一声,说:轻点声!你爸爸昨晚又发病了,现在刚刚闭上眼,别吵醒他……父亲一生病,即使醒了,也会挥挥手叫我离开,怕烦也怕病会传染给我。”三则姐弟自小相依为命,失去母亲后,又长姐为母,筠秋带着振乾长大,在振乾眼里如母亲的姐姐掌管家务也是理所当然,比他更合适。——振乾娶妻后七天,张筠秋就出嫁,就由“少奶奶”刘佩贞接替张筠秋,掌管张家家务。
在地主的家务事中,土地的购置出让和田租的收取,是最重要的项目,因为这是一家经济最重要的命脉。但在解放后,因为事关本人成分是否会成为地主或漏划地主,变为一个上天堂抑或下地狱的有关政治生命的问题,张筠秋在其1956年以前的所有档案自述材料中,都没有提及,组织上也没有深究。
时过五年,在审干运动中,是否收过租这个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到张筠秋面前。事出海盐县海塘乡朱阿妹的一纸检举信,由调查张振乾而牵涉到张筠秋。现择要摘录如下:“我叫朱阿妹,我在19岁时,被张礼甫霸占良田三亩,以讨陈租为名,实际是没有欠租,结果被霸占,……哭了好几次,穷人无法办,结果其女大宝(即是张筠秋)把我的手印。手印内容就是以陈租为名,抵押给她们,说是欠陈租20元。”
事情非同小可,组织上立马找张筠秋,她作了如下的书面回应:“我的生活来源,未做小教时候依靠父亲。自从小教、结婚后是依靠自己,没有做小教时,是跟着金洪声做生意过生活。我在家做家务,没有直接参加过剥削。”然而对于朱阿妹的指陈,她在同一页纸上又只能作出如下应对:“关于剥削方面,我虽没有直接进行剥削,但由于我家庭出身地主,婚后对方(指金洪声)曾经一度经商。因此在他们剥削中,难免有些事情经过我手。对于父亲的地主剥削,我虽没有帮助收过租,据朱阿妹说,在朱阿妹的父母双亡后,把田抵押给父亲。写纸时,我叫他盖指印。但是在25年前的事情,已想不起来。估计自己是剥削家庭,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原则上的断然否定,具体上模棱两可的承认,整页文字一点不改动,显然是誊清的,可以想见起草时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在那种情势下,她也只能如此了。
朱阿妹的检举也牵扯到刘佩贞,好在时间上给了刘回旋的余地:“当时也是父亲手里的事。听说朱阿美因父母双亡,无力耕种,交还张父自种(叫退租),我当时还没有到张家,具体不够了解,也不看见。”但对另一双佃户俞阿长、俞阿林的指陈,刘佩贞就承认了:“1943年,具体参加过收租剥削。”
历史经过了一个甲子的轮回,褪去意识形态的偏颇与现实生活中的功利,张筠秋出嫁以前,在娘家当家时经手处理过包括置地、收租在内的重要家务,应该是比较符合当时当地情形的事实,我们现在何庸为她讳言。当然,经手不等于掌管,当家不全然是作主,整个家庭财产权利中最重要的处置权一项,仍然掌握在一家之主的父亲张礼甫手中,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创建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基础的两位哲人,或许他们对信仰或现实的态度,可以成为信奉他俩理论追随者们的圭臬:一位口中诅咒着该死的资本家,手里仍经营着父亲留给他的工厂,而将“剥削”所得支援他的最亲密战友。另一位是接受他人“剥削”所得的馈赠,以维持家庭与本人的生存,从而使自己创立推翻资本主义、解放无产阶级的理论方能够得以完成,前一位的中文译名叫恩格斯,后一位的中文译名叫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