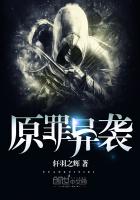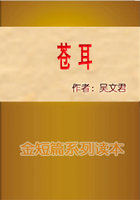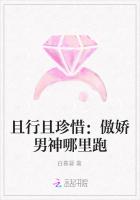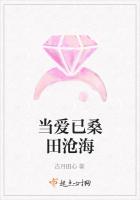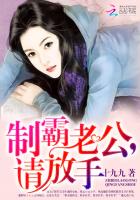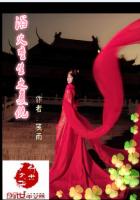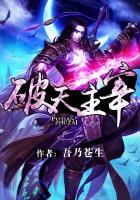1597 年在意大利出版了第一本中国题材小说,可谓17、18 世纪欧洲盛行“中国热”的前奏。这就是曼图瓦(Mantova)的阿里瓦贝内(Lodovico Arrivabene,约 1530~1597 年)写的一本以中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黄帝》(Il magno Vitei)。小说的特长标题好像就是作品的内容摘要。其中一部分这样说:“曼图瓦人阿里瓦贝内在《黄帝》一书中,除叙述了中国第一位帝王光荣的Vitei 和英勇的Iolao 可歌可泣之侠义事业外,也刻画了Ezonlom 的形象,他是最优秀的君主和十全十美的统帅……”
作者其实对中国了解很少,只能以亚历山大小说或骑士叙事诗里的典型故事来塞满全书的五百多页。两位主要英雄人物Vitei①和Ezonlom ②,则取自1586 年意大利文版的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通过与印度支那人和日本人作战的事迹,他们被描绘成智慧的典范,欧洲的君主应该从中得到启发。作者在小说里还进一步说:“最好的老师是中国人:据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推行道德。手册上所言出人意料,他们优于任何人,如同太阳的威力和光辉胜过每一颗星星。”① 可见,该小说是把中国神话为一个由贤明、正直、爱好和平的政府管理的正义国家。
至于在佛罗伦萨商人卡莱蒂② 的那些亲身经历的冒险故事中,则记载着许多并不美妙的中国经验。其中特别描述着中国人做买卖时的诈骗行为:“他们买卖每件东西都称重量,甚至活母鸡也称,这些母鸡的重量虽对,但是假的,因为他们喂的是糠拌沙之类的东西;在鱼的肚子里常能找到石子,是故意放在里边的。他们想方设法在各种事上作假,尽一切可能骗人,胜过吉普赛人,他们还以此沾沾自喜,因为这是他们的精明。他们不以作假为耻,反而认为,善于作假而又不会被抓住,那才是聪明能干的人。”③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3 年译成意大利文刊行,其中亦说中国商人做生意的方式,非常会耍手腕和奸猾,超过世上其他地方所能见到的。显然,由于人民的本性,还有整个民族的民族性,无论买者还是卖者,都偏向于欺骗。④ 可见,中国商人善于欺骗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大程度上成为欧洲人否定中国,进而解构“中国神话”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渐渐汇成为欧洲“中国热”里的另一种声音。
在17 世纪、18 世纪,意大利和欧洲“中国热”的另类声音中,维柯和巴雷蒂最有代表性。在他们身上较早呈现出欧洲人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是意大利阿卡狄亚文化期间那不勒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他也写过诗歌,29 岁时在那不勒斯大学教授过修辞学。尽管维柯的哲学观念有时不免自相矛盾,但其哲学思想对意大利现代文明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直至今日他仍被公认为意大利文化人类史的先驱。在其主要著作《新科学》(1725)① 及其经过修改补充的该书第二版即《新科学再编》(1730)中,认为上帝并不直接影响历史的进程,人也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并能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使之成为一门新科学。值得注意的是,维柯在其研究中大量提到了中国,某种程度上,把中国文化作为他研究的实例或对象。
中国诗性的思考方式
维柯的雄心是要创建一种人类社会的科学。他给自己的《新科学》提出了“第一条无可争辩的大原则”,即“这个包括所有各民族的人类世界确实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他发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荷马”,“凡是最早的民族都是些诗人”②。由此他以历史发展的观点研究美学,认为生活在英雄时代的人按其本性都是诗人,从而挑起一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真假荷马”的争论。③在他看来,古代人类具有“诗性智慧”,其特点是用具体的形象代替抽象的概念,其实质则是人类创造自己,创造历史的实践。维柯用这样的思想,尽他当时所能获得的材料,观照了世界上各民族的原始文化,其中包括中国。维柯多次提到“龙”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意义。他把这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古代文化,称为“纹章方式”,并由美洲印第安人的国王们拿干蛇皮来代替王杖,想到“中国人的国王徽帜上也有一条龙,把龙作为民政权力的徽章”,进而推论“用血写下雅典法律的那条龙(即Draco,德拉柯)也一定代表国王徽帜”。这种“纹章方式”在埃及与日本都存在过,他感叹:“中国和雅典这两个民族相隔那么久又那么远,竟用这样的诗性方式去思考和表达自己。”这正好证明了他关于“诗性智慧”的理论的普适性。所以他又说:“古代民族中的波斯人以及近代才发现的中国人,都用诗来写完他们最早的历史。”①
循着这种“诗性智慧”的普适性,维柯探寻了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共同历程,并借用埃及人所使用过的术语,将人类历史依此分为三个时代,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与此相应的有三种类型的政权、法律、语言。在谈到语言问题时,维柯又多次提到了中国文化,他指出:“中国土俗语言只有三百个可发音的元音词,它们在音高和音长有各种不同的变化(指平上去入),来配上他们的一万二千个象形文字,因此他们是用歌唱来说话。”按照维柯关于三种语言、文字与三个时代相对应的理论,中国的象形文字,只能属于英雄时代的语言文字,这种语言文字的特征是些英雄徽帜(所以维柯有时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的“龙”),或是些类似、比较、意象、隐喻和自然描绘,运用类似点是其最基本手段。但在另一处维柯又把中国文字放在第三个时代相应的土俗字母(文字)中去讨论,他说:“中国人至今还用各种方式从十二万个象形文字中造出少数字母,都归结到这些少数字母,好像就归结到总类一样。”这里有令人费解之处,因为他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知识间接得之于一些传教士,所以朱光潜先生在这段话后专门加了一个注,指出“维柯说的‘字母’似指《说文解字》中的‘部首’,其实‘部首’很难说就是‘字母’;也可能指一个字可以依平上去入而分成几个音”。正是依据中国至今使用的文字,维柯得出他的结论:中国的历史并不长久古远。①
关于中国历史的古老性
在维柯看来,中国历史并不像中国人所“枉自夸耀”和一些欧洲推崇者所相信的那么古老。他说:
人们已发现中国人和古埃及人一样,都用象形文字书写。不知经过多少千年,他们都没有和其他民族来往通商,否则他们就会听到其他民族告诉他们,这个世界究竟多么古老。正如一个人关在一间小黑屋里睡觉,在对黑暗的恐怕中觉醒过来,才知道这间小屋比手所能摸到的地方要大得多。在他们天文时历的黑屋中,中国人和埃及人乃至迦勒底的情况都是如此。②
在《新科学》中,维柯不断重复着他的这一结论,即中国历史不可能那么悠久。他的主要依据就是“中国人直到今日还用象形文字书写”,主要原因则是“闭关自守”,生活“在黑暗的孤立状态中”,于是“他们就没有正确的时间观念”。维柯进而又说:“各民族在野蛮状态中都是不可渗透的。”要不然,在如此多的千年里,中国人肯定会发展出不同的书写方式,而现在中国仍使用象形文字:“中国在几百年以前还和世界其他部分隔绝,出自虚荣地夸口说中国比世界哪一国都更古老,可是经过了那样长时间,现在还在用象形文字书写。”①
维柯把汉字当作象形文字,显然受到了传教士的影响。16 世纪后期,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让欧洲人第一次见识了中国文字的面貌。17 世纪初,利玛窦指出中国文字“很像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而17 世纪德国最伟大的东方学家、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的《中国图说》(1667)②,这部被称为17 世纪关于中国的最有权威的百科全书第六部分对中国文字的介绍中,就认为中国文字和埃及文字一样都是象形文字。在他看来,中国人是根据事物本身来创造文字的,他们和埃及人一样,从兽类、鸟类、爬行类、鱼类、草类等多种事物的图形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字。在对汉字作了介绍后,基歇尔提出了汉语方块字是从埃及的象形文字派生而来的看法,这代表了当时整整一派学者的观点。他借助《圣经·创世纪》第十章发挥想象,说诺亚的儿子曾将他的子民从埃及移居到中国,所以古代中国人和古埃及人同为一族,他们的文字亦有渊源关系。
维柯读过意大利籍会士卫匡国、法国籍会士李明,以及其他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著述,不过没有吸取他们关于中国历史古老的论说。
卫匡国在中国居住多年,深谙中国文史。他对中国史的研究水平,反映了那个时代欧洲人对中国历史了解的最高程度。其重要著作《中国史初编》十卷于1658 年出版后影响很大。① 根据《旧约·创世纪》,上帝曾用洪水冲毁了世界,只留下亚当的九世孙诺亚和他的家人及其选择的禽兽。洪水退后,世界上的人类和一切动物,都是诺亚及那些禽兽的后代。所以,诺亚之前的人类早就不存于人世,而诺亚应是后世人类的始祖。但是,根据卫匡国的《中国史初编》,当西方处于洪荒之时,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君主制国家,而且一直绵延下来,从未间断,所以诺亚就不可能是中国人的始祖,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全人类的始祖了。这样,按照中国历史的纪年,早在《圣经》所记载的大洪水时期以前,中国的历史就已经存在了。显然,这对西方的《圣经》历史观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历史成为一个极敏感的政治、宗教问题。因而为了维护《圣经》的历史观,有些传教士即从中国古书中考证,说明中国人是诺亚的后代,中国的文字是埃及楔形文字的变种,而埃及的文字可以和《圣经》相联系的。②
维柯说,卫匡国神父的《中国史初编》里断定孔子甚为古老,这导致许多人转向无神论;并举马丁·秀克(Martin Schook)《诺亚时代的大洪水》里的说法,有些人因此抛弃了天主教信仰,洪水只淹了希伯莱人的土地;还引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里的话:“印刷在中国的运用不过比在欧洲早200 年,孔子的昌盛也不过比基督早500 年。至于孔子的哲学,像埃及人的司祭书一样,在少数涉及物理自然时都很粗陋,几乎全是凡俗伦理,即由法律规定人民应遵行的伦理。”① 他宁愿相信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而不愿相信卫匡国的《中国史初编》。维柯把孔子看作是他所谓的历史进程中的第二个时代的“风俗智慧的作家”,因而,并没有像当时许多欧洲传教士和文人学者那样,给予孔子崇高的敬意。
传教士李明虽然不能接受某些中国野史关于中国历史有四万年的说法,但承认中国历史的古老,这从中国圣人孔子的著作中得到证实,根据年代学,算起来有四千年,这一算法也很难与拉丁文《圣经》的推算相吻合。李明虽然对中国许多事物倾情赞美,但对中国艺术却全面谴责。比如他对中国绘画的评价即是“除了漆器及瓷器以外,中国人也用绘画装饰他们的房间。尽管他们也勤于学习绘画,但他们并不擅长这种艺术,因为他们不讲究透视法。”② 这影响到了维柯对中国绘画艺术的见识。维柯说:“尽管由于天气温和,中国人最精妙的才能,创造出许多精细惊人的事物,可是到现在在绘画中还不会用阴影。绘画只有用阴影才可以突出高度强光。中国人的绘画就没有明暗深浅之分,所以最粗拙。至于从中国带回来的塑像也说明中国在浇铸(或塑)方面也和埃及人一样不熟练。从此可以推想到当时埃及对绘画也正如现在中国人一样不熟练。”③
这在洛可可风格正使许多欧洲人为之倾倒的时候,维柯的如此言论确实有些不同凡响,不过类似的见识在当时及此前的欧洲人心目中还比较普遍。
在中国各种艺术形式里,最难以引起欧洲人兴趣的大概就是绘画了。从17 世纪一直到19 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画的批评是同一腔调。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利玛窦。他说:“中国人广泛地使用图画,甚至在工艺品上,但是在制造这些东西时,特别是制造塑像和铸像时,他们一点也没有掌握欧洲人的技巧……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像是死的,而不像是活的。”① 在西方其他作家眼中的中国绘画艺术也都作如是观。
维柯相信,所有文化之间都存在着有机的、内在的联系,这些文化被某种精神、天性、气氛或民族观念联结在一起,局外人只有通过历史内在认同的方式才能进入某一特定文化。因此,按照他的历史主义审美观,维柯指出人们应当乐于用某种一视同仁的理解态度,欣赏不同时代的音乐、诗歌和艺术,因为各个历史阶段和各种民族文化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关于中国人文地理,维柯写到:“鞑靼区的可汗统治着古代的丝国人(Seres)那样一种萎靡文弱的人民,形成了(元朝)可汗的一个伟大帝国的一大部分,其中一部分现在已和中国联合在一起。”维柯在这里将丝国人、(元朝)可汗、中国分别了开来,暴露了他关于中国的地理知识的落后。他关于中国人民特性的评说也变得前后矛盾。他从地理环境的影响出发,认为丝国人由于处在寒冷的地方,所以是“萎靡文弱的”;紧接着,说到中国温和地带时,则认为那里的人民秉性较平稳;又举例说:“中国皇帝在一种温和的宗教下统治着,崇尚文艺,是最人道的。”还进一步说:“东印度群岛的皇帝也颇讲人道,大体上只从事和平时代的技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使他们宗教的粗野教义结合上他们所统治的亚细亚人的温和,他们双方,特别是土耳其人,用富丽堂皇的排场,乐善好施的感激心情,多少把他们的骄傲软化了一些。”②
维柯对中国文明的了解,或许仅依据少量关于中国的读物,以及对中国艺术品的观察,也包括与随同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神甫到意大利的中国青年的交谈。1723 年年底,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马国贤由于传教事业陷入困境回国。从北京出发时,他带上了五位中国青年,一路颠簸回到家乡那不勒斯,经过了近十年的磨难,1732 年,他们在这里办了一所专门培养中国留学生的中国人公学(Chinese College)。① 这样,维柯得以有机会在家乡那不勒斯见识这些中国青年,借以了解到中国的某些信息。
总之,维柯充分关注了17 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介绍评述,他的中国知识主要得自于此;同时也以其令人注目的中国文化观,成为意大利中国学传统的承启者。不过他的批评却是经过冷静思考后作出的,体现出一个哲学家独立反思后的收获。
如果说维柯的中国文化观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巴雷蒂对中国文化的指责则是其情绪冲动的产物。
朱塞佩·巴雷蒂(Giuseppe Baretti,1719~1789)是18 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文学评论家。1719 年出生于都灵,早年曾在帕尔马和米兰生活,1751 年起侨居伦敦,同当时名闻遐迩的英国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友情甚笃。1760年,他在游历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之后回到意大利,先后客居帕尔马和威尼斯。1766 年,由于他的作品在威尼斯文学界引起激烈的争辩,他再次前往伦敦,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789 年去世。
巴雷蒂因翻译法国戏剧家高乃依的作品和发表47 首讽刺诗而名噪一时。在侨居伦敦期间,他编纂了一部英意词典,用英语撰写了不少文学评论,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一篇为反驳伏尔泰抨击意大利文学而写的文章。1763 年10 月至1765 年1 月,他在威尼斯出版半月刊《文学之鞭》(Frusta letteraria),以退居乡间的一个老兵的名义在期刊上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对那些荒诞无稽的小说和歪诗拙文提出尖锐的批评,树敌不少,以至于他最后不得不离开意大利。1777 年发表《关于莎士比亚和伏尔泰先生的论述》(Discours sur Shakespeare de Voltaire),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该著捍卫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抨击伏尔泰的文艺评论观。书中流露出来的启蒙主义美学思想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风采。
巴雷蒂其著述中虚构了一个代言人“Aristarco Scannabue”。此人物“蔑视任何权威”,不宽恕任何人,包括伏尔泰。比如他不宽恕伏尔泰对莎士比亚的无所谓态度①,更不宽恕伏尔泰对中国和孔子的过分赞扬。为了抨击伏尔泰,他就批评中国文明、中国智慧、中国哲学、中国艺术等中国的一切事物。他为自己属于另一个种族和另一种文明而洋洋得意,头脑里混杂着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到了19 世纪的欧洲人那里更为显著。②
巴雷蒂这样表达他的愤慨:
我对伏尔泰先生,还有孟德斯鸠先生以及其他许多法国作家,实在失去了耐心,他们言必称那位伟大的孔子,他们不仅没有读过他的任何著作,要是追问得紧的话,他们也不能证实他的存在。那位孔子可能只是因为耶稣会士的恶作剧而虚构出来的。可是,许多法国人,尤其是伏尔泰先生把他说成是一个非凡的人,集科学、智慧和各种善事于一身。呸!呸!③
情绪如此激烈,指责如此尖锐,很难设想这是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的武断言词。确实,作为中国文化的热情崇拜者,伏尔泰俨然以欧洲的孔子自居。在他看来,孔子的只言片语,简直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幸福。孔子不以神或先知自命,他“不讲神秘,不炫惑世界”,只谈道德,“开启心灵”,没有将真理与迷信混同。① 与孔子的道德伦理学说相比,基督教则全然是虚伪的、迷信的,只会给人类带来不幸。正是在这种参照比析之下,伏尔泰主张根本废弃宗教,为重现人类的幸福与和平,以“道德哲学”代替“宗教”,而儒教可算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了,所以这样一种“哲学的宗教”的来源不能不求诸中国。伏尔泰尤其推崇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篇》)的格言,以为“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② 伏尔泰依据元曲《赵氏孤儿》法译本而改编创作的《中国孤儿》一剧,所加的一个副题“五幕孔子的伦理”也展示出其用心良苦。他在该剧第一幕第一场就借助于剧中人物之口道出全剧的主题,即“用我们中国文化的力量,把这一只野心勃勃的狮子(指蒙古族征服者———引者)收服过来,用我们的礼教道德感化这个野蛮的鞑子,叫他归化中国。”③
不过在巴雷蒂看来,没有强大军队的护佑,孔子为他辽阔的国家所设计的仅仅借助于礼教道德的所谓完美的政治体系,只不过是空中楼阁。他说孔子这个可怜的人似乎“忘记了政府应该有强大的军队:五六万鞑靼人,一个普鲁士兵团就能对付,犹如喝个生鸡蛋那样容易,可是鞑靼人在上个世纪竟轻而易举地摧毁了那个政府,如同将一块布撕成碎片。然后鞑靼人不费吹灰之力地越过长城,将皇帝从御座上赶走后,把他们中的一个人立为皇帝,只有老天知道他的脚上有没有穿袜子!幸亏,中国人没有比鞑靼更糟糕的邻居!”①
我们注意到巴雷蒂这样的论调,在他之前已经出现在英国作家笛福的笔下。后者在《鲁滨逊飘流记》中更是嘲弄与鄙夷着“不堪一击”的中国军队:“三万名的德国或英国步兵,加上一万名的骑兵,只要指挥得当,就能打败中国的全部军队”;看到几队鞑靼兵,鲁滨逊也不由得觉得奇怪:“中华帝国怎么竟会被这种不值一顾的家伙征服的;因为他们只是一批乌合之众,连个队形也没有,根本不懂得纪律和战术。他们的瘦马都是一副可怜相,也没有经过什么训练,简直一无用处。”相比之下,中华帝国的军队就更是等而下之了。② 利玛窦在1584 年写的一封信中也说:中国人是可怜的战士,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把中国人看作战士。③ 培根在《论国家真正伟大之道》这篇文章中认为:“任何国家之所以伟大,主要在于是否有尚武的人种”;只有通过军事活动才能建成世上最伟大的帝国;“一国若要成就帝国大业,最重要的事在于必须承认军事是我们的主要的荣誉、学问和职业。任何国家若不直率宣布以军事立国,就不能奢望强大会从天而降。”④ 巴雷蒂想必也会赞同培根如此的见识。
不仅如此,巴雷蒂继续揪住伏尔泰不放,指责“他(伏尔泰)怎么竟愚蠢到如此地步,以至认为中国的艺术和科学比欧洲的还好?他没有看见吗?中国艺术中那些造得拙劣的佛塔,就像我们烟囱上的装饰物……那些画在瓷器和纸上的丑陋的画,比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画差得远呢,就如月亮离我们的井底那么远。……伏尔泰先生如何有胆量将他们的火药与我们的相比,说他们是火药的发明家?我们很清楚,他们不会使用火药。”①
不过,巴雷蒂没有注意到,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典型代表,伏尔泰也在以一种理性的眼光看待中国科学的发展,认为中国的科技虽然历史悠久,但未结出近代科学的硕果:比如中国发明了火药,但只将它用来制造用于节日庆典的烟火,并未产生出促进社会变革的热兵器系列。相比之下,西方的科技虽然起步晚些,“但却迅速使一切臻于完善”②。
循着批判伏尔泰的思路,巴雷蒂又禁不住再次炫耀起欧洲武力的无所不能:“事实上,欧洲任何一座港口上没有一艘战舰不能摧毁中国和日本的所有船队,即使是他们的船队合在一起对付我们的一只战舰!请说说中国那些弱不禁风的战船,是否有一只能够穿过我们的海域,就如我们穿过他们的海域那样!他们最好先把海水喝干!假如有战船来的话,也许我们会说,它的船长在我们的港口上愿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就如同安森船队队长率领他的船队抵达广州的情形一样吗?”③
巴雷蒂对中国的情绪化攻击,显得肤浅,不值辩驳。他对伏尔泰的批评,也似乎并未弄明白这位法国作家的“中国热”是他借用的一种手段,是渴望用这种狂热来批评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意大利哲学家、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就为伏尔泰的这种做法辩护,同时批评那些同时代的人,因为这些人推崇所谓的亚洲智慧和宽容精神,却没有同样合适的动机:“今天那些为亚洲的宽容精神大唱赞歌的人,将这种宽容与欧洲的不宽容作对比,因其巨大的智慧和温顺而欣喜若狂,他们往往忽视了走伏尔泰的老路是没有用的,也是不合时宜的。伏尔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对历史智慧没有益处,但至少尽了他的本分,问心无愧,这在那个时代,在他那种条件下,是必要的。”①
其实,巴雷蒂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那一点点关于中国的知识,实在难以支持自己与伏尔泰的论辩,因而对中国文化无处不在的轻率评判也就毫不奇怪了。加之他长期侨居伦敦,自然颇受英国贬华派作家的影响,遂发出了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里一种刺耳的不谐之音。
汉学的更新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
在以上各章的描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文化中不仅有诸多域外的影响成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包括南北欧作家在内的不少欧洲重要作家都曾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发生过兴趣。他们或者从自己的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化发表议论,或者从中国文化中吸取创作的题材,写出自己的作品,或者根据自己的想象或构想,在自己的文学作品或学术著作中建构出一个个不同的但却与其本来面目大相径庭的“中国”。这个“中国”的形象既有其固有的原型,同时也更带有幻想和想象的成分。正如赛义德指出的那样,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实际上是西方媒体“建构”出来的“东方”,与地理上的东方绝不可同日而语。将其用于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分析是恰如其分的,因此我们的学术研究绝不能仅仅依赖这一“建构”出来的“中国”之形象来拓展我们的研究,而应当返回中国这个本体,对其博大精深的文化进行发掘和思考,使之真正以其本来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这方面,我们一方面要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和立场出发,发掘出中国文化的精华,并且不遗余力地将其介绍给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忽视西方的汉学家在过去的漫长年代里已经取得的成果。①
1 From“Grabbing”to“Sending Out”:A Historical 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