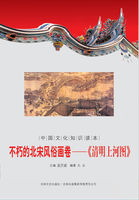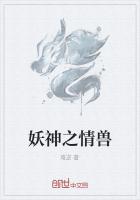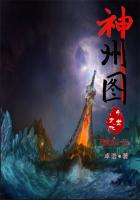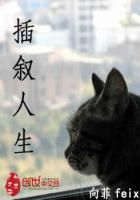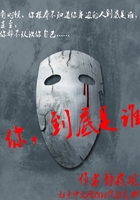既然荷兰有着如此得天独厚的汉学传统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环境,那么人们一定认为,中国文学在荷兰的翻译介绍较之别的欧洲国家来会更多,翻译的质量会更好了,其实际情况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乐观。正如伊维德所指出的,直到20 世纪70 年代,直接从中文译成荷兰文的作品实在是凤毛麟角,只是到了近20 年,翻译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和介绍才出现了较大的增长,大批中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学作品陆续有了直接译自中文的新译本。① 其实究其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是由于17 世纪时,大多数荷兰人只是致力于与南部沿海地区的中国人做生意,他们学会的那一点点中文带有浓厚的乡音和混杂的方言,再加之繁忙的业务使他们难以坐到北京的学校里专心致志地攻读标准的中国语言文化,他们在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一些关于中国的故事也大多取材于外交官的日记、旅游者的游记以及传教士的报告,加上他们的神奇丰富的想象,一个虚构的中国就建构起来了。因此这些关于中国的文字充满了对中国的误解和好奇,往往虚构的成分大大多于真实的东西,并不能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其次,作为一个毗邻北欧的西欧小国,荷兰人深知自己语言的局限,他们往往一生要学习好几种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等,所以一般的荷兰大学毕业生都会说上述三种语言,加上荷兰语,一般的学者都能用四种语言写作甚至发表文章,而且与德国人和法国人所不同的一点恰在于,他们更愿意用国际通用的语言,如英文发表自己的重要学术论文,以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受这种开放观念的影响,荷兰的汉学家,如薛力赫和许理和,便大多用英文发表自己的中国研究学术论文,因为他们从自己的前辈学者J。L 。M 。穆列所受到的冷落之命运中得到了教训:他对中国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语法的详细描述竟无法出版,只能以打印稿的形式在课堂上使用,而且很少被别的学者引用和讨论,这样久而久之便被人们遗忘了。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荷兰人尝试着直接从中文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第一位汉学讲师薛力赫于1866 年率先译介了一部名叫《花间集》的广东叙事诗,其后他还翻译介绍了一些中国志怪小说,撰写了评介文章,并用英、法、德文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但他获得莱顿大学的中文教职后便停止了这项文学翻译工作。德·高延所发表的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论文一开始也是用荷兰文撰写的,后来很快便改用英文或德文,而且到了后来,他的主要兴趣集中于宗教问题,而不是文学。戴文达的学术兴趣主要是中国古典哲学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当代的发展问题。他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意义,于1923 年用荷兰文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文学复兴》的论文,向他的荷兰同胞介绍了中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他在文章中还提及了一些新派诗人,其中包括刘半农、沈尹默、李金发等,这足以见出他的美学倾向和选择爱好。他还是荷兰第一位将鲁迅及其小说介绍给荷兰读者的翻译家和文学研究者,他翻译的鲁迅小说是《肥皂》,通过他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出荷兰汉学家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并非听从中国学者,而是有着自己的选择。由于他的主要兴趣是中国古典哲学,因而他花了很多时间编选了一本《中国古典哲学文选》并于1941 年出版。他还于1942 年翻译出版了老子的《道德经》,该译本后来于1946 年和1980 年曾两次再版。尽管戴文达用荷兰文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学的作品和论文,但这些决不是他的主要学术研究成果,他十分重视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因此他的主要学术著作一般都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他和另一位名叫R。H。凡·高罗佩的汉学家一起在《中国》季刊上发表这些介绍中国文学的译文或论文,可以说,他们的努力为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和文化在荷兰的传播和介绍起到了开拓的作用。
至于高罗佩(R 。H 。Van Gulik,1910~1967),作者汉学功力深厚,发表过不少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译作和专著,如米芾的《砚史》译本(1938)、《中国古代琴学》(1940)、嵇康《琴赋》译本(1941)、《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1944)、《狄公案》译本(1949)、《麦梦琐言》(1950)、《秘戏图考》(1951)、《棠阴比事》译本(1956)、《书画说铃》译本(1958)、《中国绘画鉴赏》(1958)、《中国长臂猿》(1967)及《中国古代房内考》(1961)。特别是《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对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的研究,被西方汉学界公认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权威之作。
作为一位学院派历史学家,何四维很少用荷兰文发表论文,而另一位历史学家许理和则一般用英文或法文发表自己研究中国佛教和早期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方文化关系中所起的作用的论文,但是,他于1964 年和一位名叫F 。沃斯的日本学研究者用荷兰文合著了一部介绍东亚佛教禅宗的专著,其中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原文文献。许理和用荷兰文编写的最重要的佛教研究文献出版于1978 年,其中包括了相当完整的早期中国佛教的文献译文,对于荷兰读者了解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正如伊维德所指出的,即使有着不少对中国感兴趣的荷兰读者等着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但是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并非直接译自中文,而是通过其他语言的中介转译成荷兰文的,因而其质量大可令人怀疑,这些作品也未在学术界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客观上广大荷兰读者恰恰正是通过这种直接的和非直接的途径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有所了解的。
从其他欧洲语言大量地转译中国文学作品可溯至18 世纪。英文版《好逑传》于1761 年问世,而其荷兰文译本很快便于1767年出版了。在诗歌翻译方面,译成法文和德文的中国诗歌在荷兰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但这一时期的荷兰文中国文学译本很乱,除了大量的作品由其他文字转译过来外,有些译本的任意发挥和删节竟然使之与原文面目全非,甚至连不少汉学家也无法找到原文的出处。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可谓鱼龙混杂,但在译成荷兰文的二三流通俗作品中,也不时地兼有一些第一流作家和哲人的作品问世,例如孔子和孟子的著述,以及李白的诗等,但这些作品往往发表在杂志上,很少成书出版。
应该承认,即使是通过转译或译述,中国文学作品的进入荷兰,也照样对荷兰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诗歌领域而言,中国诗歌的翻译介绍产生的影响还具体表现在荷兰诗人的误读和创造性建构上。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是J。斯洛尔霍夫。作为一位曾在海军中服役的医生,他游历甚广,并到过中国,因此他喜欢在自己翻译或创作的诗中引入一些异国风情。作为一位有着自己翻译标准的诗人兼翻译家,斯洛尔霍夫的翻译与他的前辈有很大的不同,他是最早采用英国翻译家阿瑟·威利的译本的荷兰诗人。他一方面忠实地效法威利,另一方面又不时地对这些中国诗进行一些全新的误读和有意的曲解,因而展现在荷兰读者眼前的中国诗实际上是经过翻译家—诗人带有创造性主体建构意识的接受之后用另一种语言重新书写的“再创造性”作品。可以说,尽管斯洛尔霍夫的翻译加进了自己的浪漫主义情调,但是对荷兰读者来说,读他那自由发挥的、带有创造性的译诗远远胜过读另一些诗人的译作。由于荷兰本身有着“诗的王国”之称,因而在20 世纪40 年代至80 年代,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诗歌的翻译始终占有很大的比重。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一年一度的荷兰鹿特丹诗歌节———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诗歌节———开始邀请一些中国当代诗人出席并朗读自己的诗作,这无疑也为中国诗歌在荷兰的翻译出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正如伊维德所总结的,中国诗歌并非仅由于其思想的深刻和意象的优美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欣赏,同时也因为人们认为中国诗歌使他们能够感受到东方的智慧。《道德经》的荷兰文译本第一版于1910 年出版,而第十一版则于1986 年问世,这足以见出人们对东方人的价值标准的兴趣。同样,孔子和庄子的著述也一版再版,一再地被不同的译者翻译、阐释。这充分体现了荷兰读者也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一样对以中国为首的东方文化思想有着由衷的热爱和向往。应该指出的是,如同所有的国别文学在另一国度的流传一样,中国文学作品在荷兰的翻译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取决于时代的风尚,而更多地取决于不同的译者的高超的翻译技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弗兰茨·库恩的德译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的一再被从不同的语言转译成荷兰文这一事实。可以说,早期的中国文学在荷兰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助于通过其他语言的转译,而转译者对第二手原文作品的神奇丰富的想象使新的译文实际上成了一种再创作。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中国文学在荷兰的传播和翻译,同时也体现于在北欧国家的传播,因为在那里,精通中文的译者实在是凤毛麟角,而可以借助于英文、法文和德文翻译的译者则大有人在。
4 Recep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Current Holland:Direct Translation and Com 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