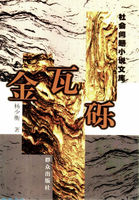事情的苗头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呈现了。比如你的多愁善感,你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对书本、或者说是对美和忧伤的热爱。等等这些,注定你男人的身体里永远潜伏着某种女性的东西。你不能忘记大概是你五岁那年的某一个晚上忽然袭上心头的淡淡惆怅和受到的亲密伤害。昏暗的油灯下,看着母亲抱着熟睡的妹妹一边唱着催眠歌一边走向房中的背影,你忽然感到了忧伤。你孤零零地站在自己的影子里,眼泪就不为人知地流下来了。泪水的热度给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怀疑,泪水是要流经鼻子才到达眼睛的,因为每当这时,你的鼻根总是先一阵发酸。在后来的日子里,你不止一次地考察过泪水的起源。泪水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呢?有一段时间,你认为是在胸腔里,因为你注意到很多人在哭泣的时候总是胸部起伏,就像大风吹过河面一样。虽然那时你还没见过河。你出生并居住的地方没有河流只有数不清的池塘,它们像是大地的眼睛,使你感觉到神秘。你以为它们通到了很深的地底。谁说池塘里面不会忽然窜出—头怪兽来呢?当时刺激着你想象的还有门口的坚山。后来你怀疑坚山应是肩山才对,因为它们看上去非常像人的两只肩膀。人的肩膀挑多了担便会像山那样鼓起来。你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它一定和这边不一样。它一定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河而不是平庸无奇的村庄。你不相信泪水与眼睛离得是那样近,就好像井和水桶的关系一样。母亲的催眠曲唱得是那么的甜蜜。母亲的白棉粗布衬衫,就像照在屋瓦上的月光。妹妹像一只小猫,熟睡在那月光里。对于妹妹,母亲总是奢侈的,即使妹妹已经睡熟,母亲也还是拿月光把她照着。而且,那月光会整夜停泊在妹妹的身上,不停地将她拍打。你多么希望母亲也像抱妹妹一样抱抱你。母亲从不会那样抱你,更不会用上腭或鼻腔哼出好听的摇篮曲。你觉得,母亲用鼻腔哼出的曲调尤其要好听一些。母亲满腔都是对妹妹的爱称。母亲把所有可爱的动物和植物都召唤来了。母亲的房间里大概有各种好玩的动物和各种颜色的花朵。你却是从小就跟着祖母睡的。祖母怕体力劳动损坏了母亲,便竭力让她年轻的身体保持良好的弹性。而母亲,也从未要求把你带在身边。本来,母亲在那些寂寞的青春岁月里是应该把你带在身边的。现在想来,母亲对你的不亲近也许是因为她生你的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当时她慌乱,害羞,因痛苦而心生懊恼和诅咒。后来,父亲离开她去河北当了兵,空间一拉大,爱情便在她心中慢慢生长了出来。祖母说,妹妹便是你妈妈去河北探亲带回来的(怎么带,祖母并未明言)。自然,用不着父亲吩咐,母亲也会精心抚养。她已经有了做母亲的经验。但是,母亲没有意识到她心中的爱情却给她的另一个孩子带来了痛苦,在你的身体上投下了阴影。它像一个疤痕留在你的额上(因为是母亲,你不会让它蔓延到心里去)。那里曾生过一个疖子,在疖子还没有熟透的时候,祖父便强把里面的脓挤了出来,从而留下了疤痕。母亲甜蜜的曲调,在你的心里酿造出了忧伤。你既喜欢这种感觉又有些害怕。其实你当时并未意识到母亲不爱你。因为有祖母,你从未感到缺乏过爱。但那个晚上甜蜜而惆怅的感受,却不知不觉使一个五岁的少年开始追问泪水的起源。
还有一次是你的十岁生日。从那一天起,你的十周岁的生命就开始了。它距离你的周岁生日已有整整八个年头。你后来翻到过一张照片,据母亲说那就是你周岁生日的前一天照的。为此全家人进了一趟城。照片上你被母亲抱在怀里,祖母露着仅剩的一颗牙齿,把半边身子藏在母亲身后。照片上的母亲温柔地微笑着,由于年深日久散发出一种老照片特有的梦幻般的光辉。可以想象祖父和父亲(当时还没有去参军)正在摄影师旁边鬼头鬼脑,企图把你逗笑。因为照片上的你正在向前扑着两手,笑容像一滴水荡开的涟漪。你还不知道母亲曾经是这样美丽。母亲穿着白府绸(其实是一种劣质的布料)褂,抱着你走在城里的大街上从容不迫。但你脑海里的幼时的印象是,周围都是玻璃。除了玻璃,你不记得任何具体的影像了。然而到了十岁生日这一天,你的生命与当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你的淘气和调皮捣蛋已在村里或更大的范围内出了名。你偷偷地去凫水,捕蝉,偷吃人家的洋芦粟杆(味道类似于甘蔗),在谁家的南瓜上破开一个洞,放一块石头进去,再合上。大概你以为那石头会和南瓜一同生长的。最起码,到时候咯嗒一声,也会把提着菜刀去破瓜的主妇吓一跳吧,以为南瓜里面生出了什么怪物,就像传说邻村的一个女人生下来一条蛇一样。有时,你会别出心裁地把这一家的南瓜藤接在另一家的瓠子藤上,谁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呢?当然,最令大人头疼的,是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不回家,或和别的孩子打架,用土块扔某一家的窗户。玻璃碎裂的声音让他们兴奋无比,就像老鼠见到了粮食。这时祖父便提了瘦竹棍,四处寻找,想不声不响抽在你的身上。平时,那根瘦竹棍便冷冷地站在门角,随时待命似的。有几次,你偷偷把它扔得远远的,可没多久,它又不声不响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当然,你的淘气和调皮捣蛋并不因此而止步,反而渐渐扩散到亲戚家中。以至在后来你已经文质彬彬了的时候,到亲戚家去,那村子里的人依然说,××,你的淘气鬼侄子来了。因为有一次,你和表弟把某一户的窗子扔了个稀烂。还有一次,祖母娘家的一个表叔结婚,你趁人不注意把新郎官珍贵的四块瓦帽子塞到了尿桶里。幸亏新郎官的尿桶还漆着红漆,没来得及用过。那时,祖父祖母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向上门告你状的人不迭地赔财物,赔小心。
到了你十岁生日的这一天,事情忽然有了变化。虽然在那天上午,你还和表弟兴冲冲地去偷了生产队里的瓜。你和表弟到瓜地里摘了瓜就走,根本不顾看瓜人的叫嚷而追赶。你们躲在一个什么地方把瓜吃了才若无其事地回家。因为是寿星,你避免了惩罚。生日过得很热闹,所有的亲戚都来了。姑奶奶,姨奶奶,舅母,姑妈,还有数不清的表婶(正如李铁梅唱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她们在一起说笑,吃喝。她们带来的孩子彼此之间也已经混熟。你和他们都熟但他们之间不一定认识。本来,你和他们要隔好几个月才能见一次面的。上一次见面还是在端阳节。但因为生日,过了一个多月,你们又惊喜地见面了。屋里从没有这样热闹,你从未这样快活过。可以肯定,假如天天这样你也十分乐意。吃了午饭,亲戚们都要走了。她们牵着各自带来的小孩在路口手拉着手。上了年纪的亲戚眼里有了泪花,惹得年轻的女客眼睛也不敢抬。祖父母和母亲也都送客去了,没有人注意到,你一个人坐在忽然空荡下来的屋子里,望着地上狼藉的爆竹皮和被抹布抹得水亮的桌面,忽然感到了繁华散尽的哀伤。你觉得胸口被什么堵住了。为了避开那压迫,你逃出了屋子。你朝着与散客相反的方向,朝着屋背后尽力跑去,脸上的泪水在黄昏的光线中闪烁。
也许就是从那时当然也可能从更早的时候起,你心中时常充斥着事物流逝带来的惆怅。用什么方法才能把它们留住呢?比如说缓缓而逝的太阳,温暖凉爽的季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些节日和节日般的欢乐。你一直弄不懂正月十六和正月十五有什么区别,窗外是一样的天和地,丢在被窝上的一样是新衣服,日子一样还是在寒假,然而正月十六的早上你一睁开眼,就觉得欢庆热闹的年已经永远地过去了。不用说,地上的爆竹皮早已被祖父打扫干净。农具从杂屋跳到院子里来了。因为上了锈,祖父要把它们磨一磨。摆到堂前中间来的桌子已经缩回靠墙的条台下面去了。挂在房梁上的用了十多年的大马口灯也已被取下来用牛皮纸包住,祖父小心翼翼把它送到楼上去。把它再拿下来的时候,将是下一个新年了。惟一醒目的是门上的对子还鲜艳,然而这就像是人在悲伤时听到了欢曲,或在春天里看见了落花,不过更添一份悲伤罢了。你惆怅着,迟迟不肯起床。仿佛这样,就能把那些欢乐留住似的。可是不管你怎样拖延,冗长庸常的日子还是开始了。
在你六岁那一年,母亲再一次去河北探亲。当时你快要读书了。母亲问你,希望她带什么回来给你,你想也没想就说,书。你说的书其实是小人书。你说了一部小人书的名字。你并不知道是否真的有这么一本小人书。你之所以要它,是因为当时到处都在演那部戏剧或电影。在你当时看来,它是多么美啊。它和你漫长无聊的童年生活完全不一样。但戏剧和电影稍纵即逝,从不肯在村里停留很长时间,有时当夜就被人拿走了,因为别村子里的人也在眼巴巴地等着。母亲没有预料到,这其实是关于她儿子一生的谶示。没想到此后儿子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母亲对文字的了解非常有限。祖父和祖母更是斗大的字不认识—升。但他们对文字很敬仰,虽然他们从未奢望过他们的后代能和文字产生什么像样的联系。在你上学念书后,祖母一看到写有字的纸,便要小心地拾起来,不让脚把它踩住。她把字虔诚地塞进灶膛。她想只有火才能让字的灵魂飞升起来。只有火,才是洁净的。字的灵魂,是不应该在泥地里的。为了让你在学校多认些字,祖母每星期都要煎两个油亮的鸡蛋,送给村学堂教书的先生。若干年后,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你发表了许多作品,然而你的母亲还不知道,或者说,对此漠不关心。但你仍然感谢母亲。那时她牢牢记住了儿子的这一卑微的愿望。在等待母亲从河北探亲回来的漫长日子里,你做了许多梦。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小人书的。在梦里,母亲回来了。母亲像—朵棉花忽然在村口出现。她好看得不像是母亲了。然而从村口到家门的那一段路,母亲怎么也走不过来,好像中间隔了一条河。等母亲终于走过来了的时候,母亲手里的书却全部湿了。纸与纸沾在一起,怎么也揭不开。你急得哭了起来。自然,—哭你就醒了。但醒了你还继续哭着,夜半的泪水如窗口的月光一样冰凉。后来,你又做梦了,又哭,但你到底是在梦里哭还是在梦外面哭呢,你自己也分不清了。母亲果然带来了那本小人书,还有几张比小人书大得多的彩色图片。你高兴极了。从此,你可以天天看那部戏剧或电影了。因为不识字,你依照记忆和想象把人物的语言和画页之间的空白填补了起来。书竟然有这样奇妙的功能,可以让流动或流逝的东西得到固定和重现。
有一天,下雨,祖父在修补桌凳,祖母在纺纱,你的小叔叔和屋前的偷贵来了。小叔叔大你四岁。小叔叔对祖父说,二爹,水今年还不读书么,学堂已动手报名了。
假如不是小叔叔的提醒,祖父或许要将你读书这么—件事忘记了。
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你还要懵懵懂懂地过上好几年,才能和文学的神会面。在此期间,你的顽皮并没有多少改变。除了成绩较好,你的其他地方并不为老师所称道。当然,因为个子小,你也没少受其他同学的欺侮。他们赠给你各种绰号(比如头上生了疖子就叫你“包公”,剃了锅铲头就叫你“猪屎蔸”),把墨水甩在你的白府绸褂上,在路上故意把你撞下地去。上课看小人书被老师没收,为了赔偿,你不得不从家里偷鸡蛋来卖。你喜欢钓鱼,有一次钓上了瘾,不想上学,祖父只好又动用了门角落里的细竹棍。和同学比赛尿尿,有一次竟射过了断墙,撒落在某一位老师的头上。上晚自习不守纪律,偷偷到旁边的供销社看电视或到哪一个村子里去看电影,被班主任老师撞上了好几次也不肯回头。但对于文学书本的接触,仅限于一两本破旧的《少年文艺》和从同村的小贵那里借来的《封神演义》。小贵很小气,借给你上本便不肯借给你下本。在初中的最后一年,你终于发狂似的迷上了读书。拿老师的话来说,是“这家伙终于入门了”。不过不是语文,而是数学。因为教数学的班主任老师对你很关心,送给了你几本列方程解应用题和几何证明的题集。你尝到了数学的快感。你天天列方程作辅助线,几乎到了夜以继日的地步。你一下子文质彬彬起来,并可笑地戴上了眼镜。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你的理科成绩突飞猛进,从而使你奇迹般地考上了师范。虽然你当时并不知道师范究竟是干什么的。
1983年9月,父亲和你坐船经由一个著名的大湖,把你送到一个破旧的县城,在小摊上吃了一碗二毛五分钱的肉丝面,然后拍拍膝盖上的灰,走了。因为这碗价廉物美的肉丝面,你对那地方的淳朴民风一直充满好感。十几年后,有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从省城回家时你特意绕道该县城,那里面貌已今非昔比。虽然在小酒馆里被人不轻不重地宰了一刀,你还是很高兴地露着笑容,就像被初恋的情人嗔怪地掐了一把一样。因为那里,不仅有你的初恋,还有缪斯女神莅临你头顶的那个神秘而光辉的夜晚。
事情的变化很快就要到来。相对于高中来说,师范里的课程要轻松得多。就好像刚刚起跑(那年暑假,你还买了许多学习资料,准备到高中去大干一场),可裁判忽然挥着彩旗,说他们已经到了终点。于是很多同学便把剩余的精力投射到体育、书法、绘画、音乐和文学上去。开始的一年,你没有发展别的,只发展了你的多愁善感。由于远离了家乡,远离了祖母和母亲,乡愁便时常把你小小的心裹紧。黄昏的时候,你站在高处朝家乡的方向凝望(当你第一次分辨出家乡的准确方位时,你是多么高兴啊),望着望着就把自己望成了—个古代诗人,面目悲然。你憎恨自己的柔弱。看上去,你都有些未老先衰了。为什么不去热爱体育呢?有一个学期,你的体育成绩居然没有及格。无聊时你也从图书馆借几本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来看看。没有什么目的,不过是为了打发时光。但中国文学中阴柔的一面和你的粘液质不知不觉就混在了一起,从此你看到春花就想到花落,见木落而怀悲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你是一个忧伤的温情的悲观主义者。你已渐渐知道“文学”这一个词了,但你从未想到文学会和自己产生什么联系。当时学校里的文学社搞得如火如荼,每天有很多人在教室里作深思状或略一沉吟然后奋笔疾书。青春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啊。你不知道你已经离他们也不远了。那是师范第一学年的暑假快要到来的时候。考完了试,同寝室的人都看电影去了。你不知是什么原因,没有赶上(后来你才渐渐知道,这其实也是一种谶示。后来你不止一次地发现,由于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在文学上,有很多东西你都没有或无法赶上,比如先锋派,意识流,新写实,结构主义,后现代碎片,物质化写作等等。后来你得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结论,那就是,当大家都在这个或那个的时候,某种有选择性的落伍才更需要勇气。或者,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真正的先锋是落伍)。离群你是不怕的。其实你挺喜欢独处。但由于思念家乡,或许还有对与某个暗恋的女孩子的离别的无能为力,你觉得房间特别的低矮和闷热。你来到了走廊上。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你和外面的月亮猛撞了一下。当然也可能是外面的月亮猛撞了你,以至你看清了她脸上的茸毛,触到了她毛茸茸的呼吸。就好像那一次你在排队从龙头上接水,手一抬,无意中碰到了一个女同学的胸部。那柔软的起伏使你身体的某一个地方猛然被惊醒,你耳根一红,慌得连桶也不要就逃掉了。这时走廊上空无一人,前面是空旷的平地,远远地有虫影的飘忽和蛙声的起伏。你忽然呼吸急促起来,匆匆回到宿舍,放下蚊帐(虽然室内并无他人),在昏暗的灯光下,用一支笔在纸上胡乱划了起来。然后,既甜蜜又忐忑不安。因为激动和急促,都是短句子。看上去,它多么像一首诗啊!你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转而又惊又喜。说不定,它就是一首诗呢(至少在外形上是如此,虽然你后来知道这个想法多么幼稚可笑)。你把它塞在枕头底下。那个晚上,你为拥有了这么一个秘密而快乐。
从此,你就和文学有了实质性的接触。你开始煞有介事地爱好起文学来了。你像所有的文学爱好者那样笨拙而诚挚地爱着文学。
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人,怎么能不爱好文学呢?每个人,是应该都热爱那么一段时间的文学的。
你不知道,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还有很多可笑的事在等着你去做。有一次,你在课堂上看小说。你记得是物理课,同学们却给年轻的物理老师取了一个和数学有关的外号,叫做ctg。一方面,是该老师名字的谐音,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头发自然卷曲如普希金,像若干字母C(小写)。那是一个好老师,他准许了学生在课堂上小小活动的自由,简直有着大学老师的风度。当时,你躲在抽屉里看《茶花女》。那是你最早接触的外国小说之一。对你来说,这本书的震撼力超过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当你看到阿尔芒沿铁路追赶不得不悄然而别的玛格丽特时,你忍不住伏在桌子上痛哭失声。哭声使老师的讲课戛然而止,同学们面面相觑。直到抽泣声越来越突出,最后只有它在教室里像受伤的鸽子一样扑腾着翅膀,你才猛然惊醒。此事虽在同学们中间成为笑柄,但在事隔多年之后,你仍为当年的自己动容而不认为可耻。有时候你会悲哀地想,你还能像过去那样完全浸润其中地去读一本书吗?你还有着那样的感动的能力吗?你不得不承认,有些书是应该在二十岁左在把它们读完的,过了这个年龄段,也许就读不进去了。
类似的经历要到1996年。那一年,你痛哭过两次。由哭而到痛哭,中间是有着一种沉郁、飞扬的过程的,就好像是从李白到杜甫的距离,或者是从西厢记到红楼梦的距离。一次是从电视上看一部很老的电影。严凤英主演的《天仙配》。不知是为什么,你忽然泪如泉涌。你为纯净的美和忧伤而感动,为朴素和想象而感动,为消失和毁灭而感动。严凤英,是一个大师。是她,让俗的黄梅戏成为雅而大气的艺术,是她让蛰居在山旯旮里的黄梅戏家喻户晓,一度成为戏剧大种。也许你的这种感动会遭到朋友们的嘲笑,但你相信这是因为他们还不真正理解你的缘故。一个人完全理解另一个人,是很难的。心灵与心灵之间,绝对有一条秘密通道,有时候,它们甚至比昆虫的复眼还复杂。读者(观众)和作品的关系亦是如此。还有一次,是在读《日瓦戈医生》的时候。你几乎是号啕大哭着读完了这部二十世纪的最伟大的作品。虚脱而愉悦的泪水让你对自己的感动能力感到放心。
倘若说到你对写作的最初的信心,那还得感谢你在师范里的一位老师。老师姓张。你记得自己投了一篇关于夜空和灵魂的散文给校报编辑部。由于里面有你的祖母,写的时候,你几次眼睛湿润。没多久,张老师就把你叫到了办公室。关上门,张老师便严厉地问你那篇散文是不是抄来的。张老师说,它写得太好了。言下之意就是,他不相信一个学生会写出那么好的文章。你望着张老师眼镜后面的两只眼睛,说,不是。张老师说,真的不是吗?你说是的。从张老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你很高兴。你并没有受到打击。相反,你受到的是鼓励。张老师的猜疑不正说明了你的文章写得还好吗?那篇文章后来被转载到一家关于读写方面的杂志上。
毕业后,你分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这一教就是十二年之久。在此期间,你娶妻、生子、上课、帮父母种责任田。当然,其间也免不了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女子产生感情上的纠葛。对于女人,就好像对于文学作品,不仔细读过,又怎么能领略其中的好处、知道其伟大性呢?你的妻子或许没什么文化,但善良、温柔、体贴,并有着良好的感动的能力。你非常看重她这一点。在种种事务的空隙,你购书,阅读,写作,发表。你因为充实而快乐。你听说有一个爱好文学的人,到他五十岁的时候才在市报的一个角落里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你想你比他要幸运得多。你是很容易知足的人。写作,只要为自己的内心服务就行了。你散淡,不求名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校里的同事都不知道你的笔名,甚至不知道你的写作,何况你的比文盲好不了多少的母亲呢?除去购置书籍和必需的生活用品,在毕业后的十二年时间里,你的存款从来没超过三千块钱。
所以有时候,你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私的人。假如妻子嫁给了一个普通的手工劳动者,比如泥水匠、木工、裁缝,哪怕是纯粹的农夫,会不会比现在更幸福呢?有一段时间,你认为是这样的。因为你爱文学,妻子没能托关系找门路弄一份正式一点的工作,逢年过节不能穿上称心的新衣服(甚至从结婚到现在还没有一枚有点重量的戒指)。因为你爱文学,父母不能得到你什么物质上的帮助,孩子不能得到城市里正规而严格的教育。当然,假如你把文学当作什么,想得到这些或许并不难。但你一直坚持着不肯这么做(虽然有很多人想法完全和你相反)。因为你觉得,文学永远是你自己的。你不能出卖她正如不能出卖那个神秘而光辉的师范夜晚的月亮。还值得一提的,是你的一位写诗的朋友。他的诗歌,曾得到过上海的周介人先生的赞赏。正是在他那里,你听到了向往已久的古琴。那是可以使灵魂纯净的声音。是天籁。你还在他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艺术和思想的教诲。他是你的兄长,你的师。假如说是他使你保持了纯洁和独立有些夸张的话,但至少完全可以说你们是在互相鼓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并不觉得对不起妻子和孩子。至少,你维护和鼓励了妻子的善良,而没有让她沾上世俗气。你也告诉了孩子该怎样做人。你不溺爱孩子,也不凌驾于孩子之上,你要让他们知道,你和他们是平等的,做人,永远不能失去尊严感。善良人的互相鼓励和爱护是一种福份。
有一次,你到县城里去寄一个比较长的稿子(镇上的邮政所极不负责任),在公交车上,你刚好碰见了两个昔日的同学。他们也曾经是文学爱好者。其中的一位当时简直可称得上是才华横溢。但现在,他们已经把文学忘记了(这其实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们研究的是厚黑学。现在,那才华横溢的是另一个才华不怎么横溢的同学的下属,或者说,那一个是这一个的上司了。三个人(具体说来,是那两个和你)寒喧着。谈到一件他们单位上的什么事,那位做下属的同学忽然向做上司的同学下作而谄媚地笑了起来,脸上堆满了油彩,而另一位,有些洋洋得意还有些傲慢地睨视着他。你不忍心看那可怜而令人恶心的两张脸,把头转向了窗外。你想,当时师范里那么多的爱好文学的人,并不乏有才华者,但他们,为什么没有坚持下来呢?有多少人,是在过着一种虚荣、没有尊严感的生活而不自觉啊。不过你不再憎恨某一个具体的人。那是非常肤薄的,或者说,还远远不够。茨威格有部长篇小说叫做《爱与怜悯》,这个标题使你深深地感动。
为了生存,终于有一天,你远走你乡,只身来到了省城。不过令你不好意思的是,你终于还是“用”了文学。因为你和文学的关系,才在一家杂志社找到了一份事做。那是一家通俗刊物,每期刊登些虚假的真情故事来赚取读者的钞票和眼泪。好像你把一个良家女子带进了魔窟,你常常觉得自己对不起文学。在枯燥乏味的文字垃圾里,你的对文字的感觉快要麻木了。你忧心如焚。但事情就是这样,想获得生存方面的略微宽裕,就得忍受种种对心灵的戕害和杀戮。在这段难熬的时间里,你靠阅读经典作品来保护自己的灵性。每每疲惫不堪地回到宿舍,是阅读慢慢滋润了你粗糙的伤口,使你得以休憩和振作。你写得很少,很艰难。你几乎对写作失去信心了。你在写作时,一向对环境的要求很高。比如要单独,安静,纸上不能有格子。你是个有洁癖的人。但现在,你被安排在集体宿舍里,小领导经常来表示对你们“业余”的关心,即使自己想租房子也不被允许,因为那样“不好管理”。简而言之,他们不但要你的手,还要你的脑袋。你只好改变你的作息时间,下了班便蒙头大睡,来拒绝那险恶的“关心”。要等到半夜,你才能起来做自己的事情。但精明的小领导(他也曾是个文学爱好者)依然不放心,第二天总能从你的眼角看出蛛丝马迹,然后提醒你对工作的责任心。有好几次,你几乎就要提着行李拂袖而去了,回到那个乡下小镇。因为这段时间受到的折磨更加认证了你对文学的感情。你的脚要永远朝着对心灵有益的方向。你并不在乎人们说你是一个失败者。后来你在省城继续淹留下来的原因是,有一天你猛然醒悟:你是不是过于强调外在的东西了?某种东西能在那里生存却不能在这里生存是否就说明了它本身的脆弱呢?一个过分依赖于外界的人只能说明你的信心和能力出了问题,或者说你的内功修炼得还不够。你有必要调整自己的气路和脉息。你应该适应城市,正如你曾经适应了乡村。
你换了一家单位。虽然屈辱的境况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你已经平静多了。做自己该做和想做的事情吧,有些事情,是值得用一生去做的,比如文学。你从文学里体验到的不仅有痛苦,还有欢乐。靠近心灵,远离其他,艺术的目的是抵达狂欢。当玛格丽特骑着扫帚把飞越城市上空的时候,你也扫除了所有时间和空间的障碍。
现在,你每天有一小部分的时间用来写作。写你想写的。在写作的间隙,你会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想想朋友,想想大师。大师们都在你的床上。你的那位写诗的朋友,已经远在北京,从事电脑软件的编写工作,他立志要把国外的软件部分地赶出中国去。他还是一个诗人并且将永远是一个诗人。谁说有这样的朋友不是人生一大幸福呢?记得几年前,你在怀念你们县城里的一位年老的文学工作者时写道,假如一个人因善良而爱好了文学,或因爱好文学而变得善良,你都对其表示尊敬。
至于对自己,你也作好了最坏结局的准备。也许,在垂垂老矣行将就木之时,你会猛然发觉自己并不合适于文学。因为你没为她增添什么光辉。但又有谁会拒绝在你的墓碑上刻下“文学爱好者”五个字呢?
或许,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