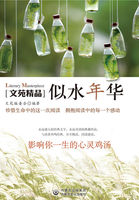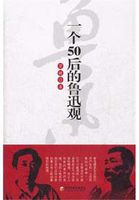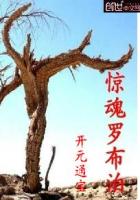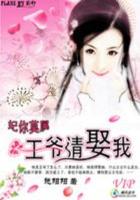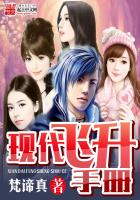之比较:同与不同
说到中西女性主义“像”与“不像”,我们是把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摹本”看待,从表层对双方进行比较,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如果拘泥于“像”与“不像”就容易裹足不前。实际上话语是平等的,分析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同”与“不同”是把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个主体,是要看中国的语境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生长的根基和取向。
有人从中西历史背景的差异、学术背景的差异质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中国文学的适用性。其实,换个角度看,女性主义立场不是自我封闭式的,而是一种面对本土经验、面对外来资源、面对当下女性群体真实境遇的不断敞开。中西历史背景的差异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寻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新增长点的源头,可以展现中国的视角和标准;而中西学术背景的差异形成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特定风格,也造成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些方面特定的劣势。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从西方引入的理论,它产生与发展的背景与中国的文化环境确实存在不小的差异。常被提及的差异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权运动有密切关系,中国缺乏女权运动的需要。西方的家庭模式是“男外女内”,女权运动提出妇女解放、妇女独立,妇女从厨房、从对男人的依附地位中解放出来,改变妇女对于自己命运无能为力的被动地位,追求法律上、人格上的平等,其核心是批判性别歧视,还女性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也就是要求“男女都一样”。而中国家庭结构传统上就是夫妻共同劳动,所谓“一男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此语出自《汉书·食货志》,参见《性别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这里的妻之“织”并非仅为家庭事务,而是一种上交国税的劳动,近现代和当代中国妇女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就“解放”道路而言,西方妇女是靠女权运动从男人那里夺来权利,而中国的妇女解放是通过民族国家主体的建立而获得的,男人倒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朋友,妇女解放首先就是由梁启超、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这些男性大师提出来的。
这些给中国女性主义者出了难题:用“性别”视角观照中国问题的时候,该以什么立场来看待中国特定的男女性别关系,怎样看待妇女解放和家国的关系。若是从西方女性主义的世界性和普遍性来看待中国问题,那么需要对两性和谐的“虚伪性”和“男女都一样的妇女解放”状态的缺陷加以分析,否则就不能展现“女性受到压抑”的基本主题。然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目标就是达到“两性和谐”,初期的任务就是促成妇女权利的获得,达到“男女都一样”,这样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内容和西方女性主义的目标有所抵触。若是只把对“性别”的关注引入分析,仍然认可中国两性的和谐、中国妇女解放的胜利,那么中国批评家就会被认为与西方女性主义者不同,不是在进行女性主义的批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这两种情况都有,都是与西方女性既‘同’又‘不同’,都有一定的创见在里面。
一、两性关系
对中国两性和谐的“虚伪性”的解说最典型的莫过于《浮出历史地表》中的一些说法。作者把“家庭”当成是第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元素,看起来最天经地义也因此最充满意识形态欺骗性,女人“只有在家庭里,她才是一种职能、工具而非主体,她才是女、母、妻、妇、媳、而非女性。这样她才纳入在秩序中,成为秩序所规定的一枚螺丝钉。”虽然有人说,家庭中“妻子”的意思是“与己齐”,但孟、戴则说“‘妻与己齐’短短四个字已包含了男性说话主体、女性对话主体与所谈客体(女性)的两大分野,包含了这两大分野的清楚无误的主客、己他的对峙。”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还有批评家对男性作家笔下女性的优美形象与和谐关系,比如《浮生六记》中的夫妻关系,也认为是男性的潦倒和女性的迎合所造就,并非有真正的平等与尊重。
认可中国两性和谐观的人则侧重对搜寻男性尤其是杰出男性对女性的宽厚恩宠,诸如《袁枚的男女关系及妇女观》(《百花洲》双月刊2001年第3期)、《日本文化对周作人女性思想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季刊2001年第2期)等文章就是这样。黄乔生著的《西方文化与现代中国妇女观》(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并行梳理了“受了西方进步思想影响的”胡适、鲁迅、周作人、张竞生、聂绀弩的妇女观,认为其“不但在理论上有主张,而且实际上对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贡献”。黄乔生著:《西方文化与现代中国妇女观》,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研究男性对妇女的关爱的不止男性和理论家评论家,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包括致力于女性主义研究的女性,也在有意无意地做这方面的工作。
由于观点歧异,双方阵营中人时有相互攻击。比如,第一类人批评第二类人并没有进入真正女性的世界,一切都是以男性为参照和中心,从所谓关爱女性的种种具体行为和现实表象中,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男权社会里女性工具性的实质。《谁在搅女性主义的浑水》一文的作者说从“伟大思想家关爱女性”这一视角进行“女性文学批评”的人,“那些自诩的女性主义者,并不真正在意什么立场,也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女性主义的责任和权利。她们还没有准备好承担使命,还在下意识地四处寻求援助、荫蔽,借他人之功壮自己的行色。看来,应该强调女性研究特别是女性主义研究的起点,在于摆脱那似乎无法摆脱的被动心理——女性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作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女性研究与其痴迷于过去女性曾有过的特别的荣幸,不如坚持男女两性现在仍然处在相同的困境中,同样的不自由,这可以让女性重拾、更重要的是检验男女并肩作战共同解放的神话,去发现、体会现实的男性,谁是真正的伙伴,谁仍然是他们所适应的男性中心的一部分,谁仍然是男性权威的自觉不自觉的维护者。”魏天真:《谁在搅女性主义的浑水》,原载《中华读书报》,见http://www。cReader。com 2002-03-14.
第二阵营的女性主义者则说揭示两性和谐“虚伪性”的批评家对现实的过度忽视和对妇女的生存境遇缺乏理性思考。比如,《中国女权主义的现实出路》一文说,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家和万事兴,男女平等和男女和解是家庭及社会稳定与发展最重要的保证,而“一些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和女权主义思想宣传的女学者,由于无法处理好‘女权主义理想’与现实中国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中都明显存在男权思想的生存境遇的矛盾,婚恋不顺心,常常生活在与男性的对抗而不是与男性的和解中。学术性理性化研究常常变味为对男性带有抵触情绪甚至报复心理的情绪化研究。这种情绪化行为又造成男性学者的情绪化抵制行为,如此恶性循环导致女权主义学术界非学术性的男女学者的对抗,极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健康发展。”于是,作者以关心的姿态说,“如果女权主义者首先当好了女人(这里的‘女人’既非男性文化中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乖乖女’概念,也非霸权的女权主义的女子有才就有一切的概念),现实中国便会少了许多哀叹‘好女难嫁’的女才子,少了许多在家里时时进行‘两个人的战争’的女学者,少了许多因为事业至上而放弃女人的为人妻、为人母等天伦之乐却又时时感叹活着真累的女强人。”王珂:《平权优于霸权:中国女权主义的现实出路——夏洛蒂·勃朗特与弗吉利亚·伍尔芙的女权思想比较研究》,http://www。alleyeshot。com/woman/ke。htm。
对男女性别关系的看法附带出一个“姐妹情谊”的观点的分歧。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姐妹情谊”(sisterhood)是个相当重要的概念,激进女性主义者所倡导“女同性恋”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姐妹情谊”的一个变种。西方女性主义者把“姐妹情谊”当成两性斗争中女性的避风港或者是女性取得胜利的一个保证。当这个词“平移”到中国的语境中,批评家对它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有不少人欣赏这个词附带的政治含义,在中国文学中找到不少女性友谊的例子,来证明“姐妹情谊”给妇女带来的力量。戴锦华的一篇评论《陈染:个人与女性的书写》非常关注所讨论文本中“女性情谊”的问题,而陈染本人则希望用“同性爱”来说明问题,并表示“像戴锦华这样的一位著名批评家,使用‘同性爱’这个字眼,会太刺眼了。也许是,她担心让我太刺眼。我特别理解她。”引自陈染著:《不可言说》,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http://culture.netbig.com/reading/r1/809/20000718/43440.htm.的确,在中国的语境中,很多批评家质疑“姐妹情谊”的存在,说,“主体性的追寻成为女性个体觉醒的重要表征,却极少有女人能联合成战斗壁垒,相反,自我个性的自觉往往是以对同性主体性的忽视、压抑与戕害为前提的,争取男性与打击同性往往是一石二鸟的自觉行动。”丹妤:《邂逅枕边人》,http://culture.163.com/editor/021105/021105_67205.html.
二、女性与国家
20世纪初,中国人生活在被革命的理想煽动起来的激情中,众多女性“被解放出来”或者寻求“解放自身”。20世纪60~70年代,当美国中产阶级妇女不满于“回归家庭”,反对男性社会对于妇女的歧视而发起女权运动时,中国正值社会主义时期,女性早已走出家庭,与男人同工同酬,而此时的社会意识是男女平等。一些来中国访问的西方女性主义者都吃惊于中国女性解放的成就,并认为在这一方面西方人没有资格自居导师。
面对必须解说的女性与家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女性主义者的解释也有两种。一种是家国意识往往会形成对女性意识的遮盖,必须要寻求女性意识与家国意识到区隔。《浮出历史地表》是奠定这个论点的开山之作和代表作。书中认为,自从母系社会为父系社会取代之后,中国男权制集权社会便以政治、经济、伦理价值等方面的强制性手段,对女性实行强制性策略,将之压入社会最底层。家庭是实施这一压制的关键场所,“受命于家”将女性逐出社会,而“夫者妻之天”将女性变成男性的附庸。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的妇女解放运动使中国女性浮出了历史地表,“我是我自己的”,子君的这短短的六个字“结束了女性绵延两千年的物化、客体的历史,开始了中国女性们主体生成阶段。”但“五四”所开创的女性解放,后来却迷失于男性化的民族国家主体的追求中,由此20年代末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丁玲只能倍感孤独,而被迫转入《水》、《田家冲》这种民族解放的集体话语的表达之中,女性意识遭到了放逐。到了解放区及至新中国成立后,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方面都获得了与男性的平等的法律权利,但在作者看来,这一切虽然堪称自豪,但以从属民族主体为代价的女性独立,其实是女性意识更为根本的丧失。作者的结论是,世纪初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意识,一向就未能成长起来,而终于在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泯灭。“这样,问世不久的女性的历史,在与民族群体历史进程的歧异、摩擦乃至冲撞中,走完了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循环,那就是以反抗男性社会性别角色始,而以认同中性社会角色终。在这一个终点上,女性必须消灭自己以换取允诺给女性的平等权利。”
这种分析的影响是巨大的。应该说,对于中国古代女性压迫思想的批判自“五四”时期就开始了,但这里的批判与“五四”以来的批判却存在着视角上的差异。“五四”视角是自个性主义角度反封建,而这本书的视角是从女性意识角度反对男权中心主义。女性的角度不但使作者发现了诸多出自于男权中心的性别压迫形式,而且还直接衍发了对于自近代、“五四”直至当代的社会文化的尖锐批判,这才是真正石破天惊的。从此,严格意义上“女性文学”的开端就被认为是“五四”时期,“关于我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批评者普遍认为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五四’时期,二是1920年代末到40年代,三是新时期文学。”谢永新:《译介·批评·建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我国的发展》,载《东方丛刊》1996年第3期,第238页。而且,不少人把远离政治当成了衡量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标准。这里是“个人化写作”等“小我”写作后来在批评界被推崇的源头。
强调女性意识与家国意识密不可分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也有一批。在1992年哈佛大学的“用性别看中国:国家、文化、妇女”国际研讨会上,李小江力陈中西女性主义的区别应该在于中国妇女解放与男性、与国家的关系密切。李小江等著,《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崔卫平在《我是女性,但不主义》中宣称,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强调女性本质的被消解,并不显得特别有意义。“无性化”的历史命运不但发生在女性身上,同样也发生在男性身上。她怀疑中国是否有“菲勒斯中心”这种东西,同样“阉割”这种隐喻并不适于描述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其实男性被“阉割”的情形并不比女性轻,“当一些男人的肉体被‘阉割’时,另一些男人的精神灵魂能完好无损地幸存否?他们是‘主体’还是‘客体’?”她反对从本质论意义上给人(无论男女)下定义,“实际上我对女人有没有本质并不很在意,我关心的是女人有没有现实性。她们有没有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有没有自己实实在在的生活,基于同样的考虑,我也十分关心我们的男同志有没有他们的现实性。没有根据说我们生活中的男性公民已经解决了上述诸问题,他们已经像传说中的那样,既掌握了支配自己的主动权也掌握了支配女人的主动权。”崔卫平:《我是女性,但不主义》,载《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同样,赵稀方说,把民族意识和女性意识对立起来使得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在论述中国女性文学时陷入了非历史主义的境地。主体不过是历史文化建构的结果,没有脱离于特定历史文化的纯粹女性自我。如果说既然是女性,就应该有女性意识,那么既是社会人,也就应该有社会意识。《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性意识固然出自于作家的主体,《田家冲》、《水》中对于民族国家的追求何尝不是作家主体意识的产物。一味夸大这种女性意识、并以此压抑其民族国家意识会陷入偏颇。《生死场》中的人物金枝说:“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鬼子。”按照女性主义的分法,这里的“恨男人”属于女性意识,而“恨小鬼子”属于民族国家叙述。很显然,“恨男人”与“恨小鬼子”同样都是作为女性的金枝的主体意识的构成部分,而且“恨小鬼子”甚至在“恨男人”之上,因为在“小鬼子”来了之后,连男人也受了小鬼子的侵害,这显然更为严重。金枝这一句简单的话,形象地表明了女性意识的社会制约,它决非如一些批评者想象得那么简单。赵稀方:《中国女性主义的困境》www。cc。org。cn/zhoukan/guanchayusikao/0105/-3k。
以上从性别视角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可以说各有道理,都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流派,不过是侧重点有所差异而已。
第三世界的妇女和本种族的男性一样面临着强势民族的可能欺侮,有着与男性共同的利益,有着与男性合作的必要。这是不同于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权主义者的一个显著的特征。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曾就此有过成功的论述:对黑人妇女而言,她们“个人的”问题与种族、阶级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并不单单是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黑人妇女在意识到黑人男子对自己的性别压迫时还要为其辩解,相信她们困境的根源在于种族压迫:敌人不是黑人男子,而是社会上的压迫性力量。Robin Morgan ed,Sisterhood is Powerful: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New York:Vintage Books,1970),p。393.许多黑人妇女表示,与参加白人女权运动相比,她们更愿意帮助黑人男子得到“他们很久以来被剥夺的权利。”她们的想法是:黑人男子的权利得到保证时,她们才能拥有作为黑人妇女的权利。因此,与白人女权主义者对男子的敌视态度截然不同,黑人妇女不敌视黑人男子权利的增多。而黑人男子在争取种族斗争胜利的特定阶段也往往团结黑人妇女,甚至把黑人妇女尊为“皇后”,要保护她们,解放她们。中国妇女和男子的关系有一定的相似性。19世纪末起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旋风中,中国开始有妇女(比如秋瑾)投身在民族主义的斗争中,与此同时,相对于殖民宗主国或列强的优势与压迫,沦为受压迫、弱势与“去阳性化”的殖民地男性知识分子,基于对阶级、种族、民族压迫的反思,妇女这个千百年来备受压迫的范畴,在男性对家国神话的重构中,被置换于家国痛遭蹂躏与摧残的象征与借喻的话语中,妇女的压迫问题因此得以与救国、建国大业并置。所以,如果如崔卫平所说中国男女都被“阉割”了,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解释为:古代的男性和女性的“阉割”可以说是屈从于拉康所谓的“象征秩序”,而现代的男女受到“阉割”则是因为“殖民”压迫的存在。
再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与国家话语的重建使相生相依的,小说与政治在现代中国文学里一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女性文学而言,二三十年代庐隐、白薇、丁玲等女性作品起发展趋向是对女性和民族作出具有启蒙性的思考;此后,抗战时期,萧红、罗洪等则是更多于作品中关注社会现实与充满革命色彩的新女性现象;新中国成立后,菡子、茹志鹃、黄宗英等女作家却是体现了那个大时代的烙印。这些存在于文学中的现实因素也使当代女性主义者采取认可男性的努力、家国对女性意识的必要性。
不可否认,中国女性主义者在反对“欧洲中心的女性主义”可以得到些许教益,然而,第三世界/边缘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又必须警惕民族问题对女性问题的压抑。伍尔夫曾言,“作为女人没有国家。作为女人,我不要国家。作为女人,我的国家是全世界。”Andrienne Rich,Blood,Bread and Poetry:Selected Prose 1979-1985(New York:W。W。Norton,1986),p。183.这个说法虽然偏激,但揭示了一个真相:妇女与国家话语的关系要比男人与国家话语的关系更复杂暧昧。从现实层面上说,国家话语对妇女问题的控制与吸纳,基本上是其权力话语建构过程重要的一环,革命时期“改变传统上对妇女的掌控势力,是把这权力从亲族转移到国家的步骤的一部分”。Laura Nader,“Orientalism,Occidentalism and the Control of Women,”in Cultural Dynamics2:3,1989),p。337.问题是,打完民族战争以后,妇女的问题往往再次被延宕。周蕾曾举中国妇女的处境为例,说明第三世界妇女问题总是与家国话语纠缠不休,“中国妇女,如同其他父权‘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同胞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要求为了更远大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牺牲、延宕她们的需求与权益……每当有政治危机时,她们就不再是女人;当危机过去、文化重建之际,她们又恢复了较传统的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同心协力致力于秩序的重建。”Rey Chow,“Violence in the Other Country:China as Crisis,Spectacle,and Women,”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eds。Chandra T。Mohanty et al(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p。88.女性身体与乡土、家国的换喻关系,在文学上、民族话语上更是屡见不鲜。伊瑞格瑞说,女人作为一个场域,却失去了自己在这场域之上的占领权、话语权,女人“被指定为一个场域,却不占有一个位置,经由她,场域得以建立,但是为男人所用而非她所用。”Luce Irigaray,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trans。Carolyn Burke&Gillian Gill(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52.也就是说,女性可以作为男性寻求身份与巩固认同的中介,可以作为民族的象征,作为民族的“肉身具化”,她是“民族话语”所欲的对象,但在民族话语历史上却“拥有”极有限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女性作家的作品,如果成了国家话语的载体,那么就可能遮盖住女性的真实经验。所以当一些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提出,丁玲向国家话语靠拢的过程就是女性意识越来越淡漠的过程,我们应能体会到她们立场的源头,并予以理解。
谈论中国男女的性别关系,谈论中国女性和民族话语的关系时候,不管持什么观点,只要涉及“性别”对女性生活的影响,我们就可以得到相当的启示。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所有的支配权都是相对的,人生和社会也是复杂的,但不能因为“男人”自己在境遇上的不完善性就否定他们对女性的压迫,共同的进步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决不能让一方凌驾在另一方头上,我们要不完善中追求最大可能的完善。用西方话语谈论中国现实,其中必然要涉及“转化”和解说的问题,不少时候就是在用“双重语意、双重声音”在讨论。
三、学术背景与特定风格
中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学术背景存在差异是个不争的事实。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反“新批评”的背景下产生的,新批评重客观、重技术、特别是它试图切断文本与现实联系的特性,使它与女性主义重政治、重主观倾向的批评理念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然而,新批评所超导的“文本细读”的方法,使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往往能做到对文本的内外兼顾。
本土的学术土壤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受到两种滋养:一是“文以载道”的文学理念,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化文学象征符号为“社会实践”是文学里不能相忘的一个使命,“新时期以来文学在主题与手法创新上标志了大陆文学的一个多元丰富面貌的开展,但写实/原道精神在文化深层仍是不可触犯的底线。”宋素凤著:《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我国女性主义批评主潮也受到作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原则的指引和暗示,“以真实性为基础,以典型人物为归结。”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这样的批评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以社会上的妇女问题来阐释文学中的性别问题,或者从文学中的社会性别视角来审视男性中心社会,批评思路比较单一。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学习始于译介。然而,译介者早期的目的恐怕亦不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一些译介者对中国文化只停留在感性体验阶段,缺乏理性认识,甚至对中国文学很陌生。他们将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新现象、新思潮引进中国,功用是要与西方妇女文学的翻译和评论结合在一起,这类论文多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等刊物上。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家(部分从事西方研究或外语水平较高的研究者除外)大部分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接受是被动的,接受影响的方式也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接受的材料、理论和方法不是全面的、全景式的,而是局部的,或者是通过一些概念、概观及综述类的评论获得的。因此,虽然女性主义批评的译介热潮正值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德里达、巴特等的译介高潮,虽然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叙述学、神话原形等注重文本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译介,但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可操作性不强。结果,本土学术背景在大多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那里呈现强势,屈雅君说,“本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几乎不存在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工具和方法的问题,而更像是批评视点的转移。”屈雅君:《女性文学批评的本土化》,载《文艺报》2003年3月4日。
学术背景差异引发的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有几个方面。其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进程是从“立”到“破”,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历程是先“破”后“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西方女性富于颠覆性的文学批评通过译介迅速在我国传播开来时,中国学界才真正从建构妇女文学世界进入到以质疑的、批判的眼光审视整个文学世界的阶段。上述原因使得“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出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姿态,它在总体风格上较为冷静温和。”相应地,清理文学史上男权文化传统的工作,虽然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初期工作,但在中国这方面的工作远未达到应有的深度,而在“女性阅读”的研究方面,中国批评家更容易关注“作为作者的妇女”,而对于“作为读者的妇女”很少触及。
其二,“互文性”的不同。“互文性”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概念,“任何作品的本文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47页。“互文性”不仅指明显借用前人的词句和典故,而且指构成本文的每个语言符号都与本文之外的其他符号相关联,在形成差异时显出自己的价值。这一概念本身具有相互联系、“吸收和转化”等特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通过“互文性”与当代大师对话,改动、修正和运用他们的话语,据说“女性主义批评不存在非女性主义批评家未采用或不可采用的方法或理论。”Syoney Janet Kanlan,“Varieties of Feminist Criticism,”in Gayle Green and Coppelia Kahn eds.Making a Difference:Feminist Criticism(London:Methen,1985),p54.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总结女性的创作规律,界说女性的思维风格时,多以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说法为前提,似乎在它开始正文之前,总是需要一个开场白,它必须在一定的前提下,在比较、对照中才能进入操作。也就是说,在对中国女性及其文学进行界说时,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了中国女性研究者无法摆脱、纠缠不休的“前文本”。文本的互文性就是佐证,互文性借助和引用他者,表明了自身的不足,而他者恰恰可以弥补自我的不足,解决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20世纪各种时尚理论血脉理论相连,那么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西方各种理论流派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双重借鉴。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中所表现出的方法上的多样甚至驳杂,也就毫不奇怪了。
第三,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侧重对概念的清理,断言“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反理论的行动,一种对现存准则和判断地抵制”Syoney Janet Kanlan,“Varieties of Feminist Criticism,”in Gayle Green and Coppelia Kahn eds。Making a Difference:Feminist Criticism(London:Methen,1985),p。55.;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表现出一种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的灵活性和功利性”转自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比如,林丹娅、王绯都用了“空白之页”的说法,但有所不同:前者认为“空白之页”说明了女性无声的反抗,而后者则认为它说明了女性在历史和文化中的地位是“匿名与残缺”。两者对这个概念的运用是各取所需。大致看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常见体例是将西方各种批评方法综合在一起,批评家还停留在中国不偏不倚和大而全的哲学思维上。后现代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发展,也许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西方哲学在中国不能生根,作为其派生物的文学批评何以成为可能呢?”
学术背景的差异必定造成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相对而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有不少在学术上需要改进的地方,这种进步需要时日,也需要女性主义的投入和学习的态度。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双方历史背景、学术背景不同,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相当大,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内部也有差异。看来,中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都是有“众声喧哗”的特征,“不同的声音各自不同地唱着同一个题目”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上是对西方文本作深层的改动,并把它移到一个新的环境中,继而载入自己的文本与之相连。除了有关术语的简单问题外,人们还要考虑、借用和重提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转述别人的语言,还在于转述所产生的结果。再加上历史背景、学术背景的差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在进行文本的联系和转换的同时,必定是“求同存异”,必定要组合、再现、歪曲、改头换面西方文本的一些东西。我们读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本时候,实际上可以体会到“双重语意、双重声音”。
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内部的“差异”并不会造成多大的问题,也不是不可弥合,它们毕竟有“一个建立在政治上,而非生物上或文化上的联盟基础”宋素凤著:《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父权制对于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是母系社会之后人类历史上具有普遍性的历史事件,就此意义上说,西方女性主义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观察事物的崭新视角,中国女性主义由此出发对于中国历史文本中男权意识的揭示确发人深省。因为有相同的政治基础,在女性主义阵营里所有的歧异将是互补的力量,而不是对立与离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