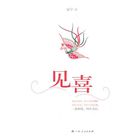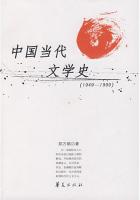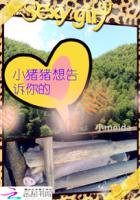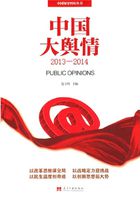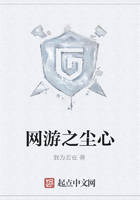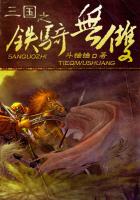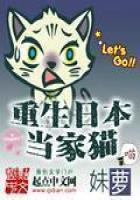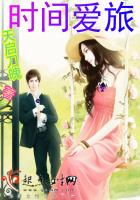一
奈保尔(V. S. Napaul)的《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 1972)是一面政治之镜,映出了后殖民时代非洲的处境。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没有看到“解放”一词所允诺的光明前景,相反却陷入混乱、动荡以及相伴而生的独裁政治的怪圈。有一种观点认为,非洲新的独裁政权甚至比前殖民地的主人更邪恶。是什么导致后殖民时代的新独裁?《河湾》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知道,《河湾》是奈保尔的代表作,非常有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它所触及的两大题材——流亡和非洲——相关。流亡引起共鸣;非洲引起争议。共鸣和争议都是赚取眼球的成功法门。奈保尔写作《河湾》的时代,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流亡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对许多人来说,流亡甚至就是生活本身。流亡的伤痛和屈辱,很容易使他们在《河湾》里找到同感。奈保尔对流亡的成功书写,既博得文名,又赚到钱财。聪明的他堪比《河湾》中的人物纳扎努丁;不同的是,纳扎努丁只是一个商人,而奈保尔在骨子里虽与全球化时代的商人精神认同,却是以知识分子来自我定位的。他在英国牛津求学的经历和最初几年的迷茫和困惑,自然能够在《河湾》流亡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因达尔身上找到程度不小的对应。但最能充当奈保尔化身的,还是他所厚爱的主人公萨林姆。共同的族裔身份、共同的中非经历、共同的信念——即对家园、宗教、记忆、祖国、过去、未来等的放弃——无不表明,萨林姆的精神与奈保尔合而为一;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奈保尔才给萨林姆披上一件落难小商人的外衣。对于作家的这种“分身术”,奈保尔坦言,是为了“无意识地建立一种和谐共存,给予其主题一种封闭的紧凑感”,以便自己藏身其中,不为人知。
如果说,《河湾》针对流亡者个体所下“世道依旧”之判断很大程度上能得到读者的认可,甚至能引起他们无限的感慨,那么针对非洲而言的“世道依旧”说——独立后的非洲仍充满了独裁、压迫、腐败、动乱和战争,仍是一个弱肉强食之地——必引起轩然大波。奈保尔对此似乎心知肚明。随着殖民势力的解体和非洲新兴独立国家的出现,有关他的非洲书写的争议一直不断。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独立后这些国家的命运是更好还是更坏?在《河湾》中,奈保尔通过笔下人物斩钉截铁的回答是更坏: 殖民时期“尚有和平的奇迹”,还有“法律”和“秩序”,现在却“一无所有”。他把非洲的现状断然归咎于非洲人自己,甚至咒骂他们“咎由自取”;在他看来,非洲历史在前殖民时代就很糟,殖民者撤离后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正如萨义德所说,《河湾》的思想要点是,非洲民族主义的胜利不仅没有真正解决历史问题,反而扑灭了“它的最后希望和西方文明最后的一点影响”。
二
奈保尔的非洲观与非洲和欧美知识左派关于非洲的乐观主义的观点格格不入。事实上,在非洲各国获得独立的最初年代,知识左派中一度流行着这样的乐观论调,即古老的非洲进入了新纪元,从此非洲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将开创伟大的事业。奈保尔认为,这种乐观主义论调十分可疑:
我的确对那些事业抱有极大的不信任,正因为它们是事业,它们就不得不简化,不得不忽略许多东西……比如在非洲,你能深刻地体会到他们对现实彻底地拒绝;人们避开了真正的问题,似乎这些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似乎有缺陷的人类的全部历史完全是因为压迫和偏见造成,现在,压迫和偏见都已经被铲除了,剩余的批评只是偏见的偶尔发作,因此可以不予考虑。最近在东非,我一直听到各方都在说这是非洲的时代,似乎非洲突然间就科技发达了,教育进步了,文化先进了,政治强大了。我惊骇地发现,那些只具备很少技能、头脑简单的人民如此地确信他们正携带着所有文明、文化、文学和技术的种子。这些都是无稽之谈……非洲拥有一切的理念某种程度上已经被非洲人接受和挪用,这是最恶毒的骗局。这可能是心知肚明的骗局,你情我愿,但它终究是骗局。
奈保尔对欧洲知识左派和非洲当权者里应外合、“你情我愿”地得出的非洲乐观论进行了批评。一方面,故事中那个无名国家的领袖——“伟人”——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为独裁的需要,大力宣扬“新非洲和非洲新人”的理念,绕过“真实的非洲”,画饼充饥地建立起所谓的“新园区”。另一方面,欧洲知识左派由于对非洲真实情况的隔膜,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独裁者“伟人”的帮凶。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说,盲目热爱黑人之人和一味嫌恶黑人之人没有区别,都是“有病”之人。奈保尔的观点多少是相似的。在他看来,持非洲乐观论的西方知识左派基本上都“病”得不轻。《河湾》通过叙述者萨林姆的眼光,在多处对这些有“病”的西方左派进行了批判和嘲讽,如揭露在非洲东部的解放过程中,一些欧美左倾报纸对那里发生的屠杀视而不见,多是“溢美之词”,盛赞非洲“封建社会的终结”、“新时代曙光”的到来; 国家独立后,西方知识左派成为新兴国家的“座上宾”,充斥在各级教育机构,向费尔迪南这样的“非洲新人”灌输“非洲外面的世界都在沉沦,唯独非洲正在冉冉上升”这种荒谬的看法;他们住在“伟人”专门为他们建造的“新园区”里,整天高谈阔论,为“浪漫的新非洲”大唱赞歌,却对“新园区”外面的非洲生活一无所知。
奈保尔还借助深受西方左派影响并接受其资助的小说人物因达尔的眼光,来洞察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真相。因达尔一直以为,这些为“新非洲”共同努力的西方左派同志一定和他一样,有着共同的理想、目标和追求;因而他向他们敞开心扉,无所顾忌地与之谈论非洲和非洲人的命运。然而,当他试图真正走近他们的生活时,却猛然发现不同种族间的所谓“平等”,所谓左派同志的“志同道合”,一切都是幻觉:“在那公寓里,在那晚宴上,丝毫没有非洲的气息。”他终于明白,这些西方知识左派,非洲的同情人士,其实缺乏真诚的革命者潘恩和格瓦拉那样的实践精神;他们不可能与非洲人同命运、共进退,成为非洲未来的担当者;所谓非洲革命,所谓非洲“新生”,只是他们在富裕生活的间歇所进行的精神意淫而已。正如萨林姆所言,“反正他们又不对非洲真感兴趣,反正他们又不在非洲生活”。
三
在奈保尔深入非洲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非洲各国获得独立已有一二十来年,然而现实状况不容乐观。举目望去,处处经济萧条、政局动荡,冲突、政变、屠杀、战争此起彼伏,似无止境。古老的大陆风雨飘摇,前景未卜。面对这种比殖民时代更糟糕的局面,即便最初对非洲持乐观看法的西方知识左派,现在也大幅度修正先前的立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见仁见智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很大程度是欧洲殖民主义造成的恶果。
不妨以与《河湾》中那个无名小国对应紧密的中非国家刚果为例。比利时在1960年结束殖民统治时留下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四分五裂、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刚果宣布独立的时候政党林立,达120个之多,每个政党背后都与某个族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16个刚果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仅136人受过中等教育。在1400个政府职位中,仅2个职位由刚果人担任。在其他职业中,没有刚果人是医生、中学教师和军官。”在这片近乎白纸的大地上,想要画出一幅美丽的图画,在短时期内实现民族融合、国家振兴,无异于痴人说梦;同样,要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和民主、自由,也不啻是天方夜谭。事实上,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后的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宗主国在殖民时期的残酷掠夺和统治。
与此相类似的一种解释是,非洲的国家仅仅在政治上宣布了独立,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却远未独立,而是继续依赖、受制于原来的宗主国;甚至它们所谓的政治独立也只是在名义上如此,而在实质上却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宗主国的势力无孔不入,继续操纵这些国家,甚至有意挑起部落矛盾和国家间冲突。欧洲殖民国家从未放弃对这些新兴国家的控制。它们只是以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方式行使着帝国的特权。这主要表现在对非洲的经济垄断和文化霸权上,而非直接诉诸赤裸的经济掠夺和武装干涉。《河湾》中“伟人”建立的“新园区”便集中体现了“前殖民主义者企图维持在非洲的乐园和延续殖民主义的美梦”。
还有一种从反思民族—国家的建立入手的解释。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在大肆进行殖民扩张的同时,广泛散布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民族自决论;正是这种民族自决论为后来殖民地无休止的冲突和战争埋下了伏笔。在20世纪的前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者一般以共同的文化、语言或历史进行动员,以推翻宗主国的统治。他们的策略,是将殖民者强加给他们的负面属性转化为一种积极的自我形象。具体说来,就是在文化上利用殖民宗主国对他们的“他者化”: 凡是被蹂躏的,他们加以美化;凡是索然无味的俗套,就重新赋予精神活力。但民族主义这种反其道而用之的策略有着内在缺陷,因为一切民族主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民族属性的概念,而民族主义的政治是属性的政治。因此,这种民族主义的生命力是“模糊、可疑”的,“不仅通过国民教育造成了关于一种不完全,受到压制、又最终恢复了的属性的说法,同时也造成了新的权威”;因而,如果在民族主义者成功的时刻,民族意识不以某种方式转变为社会意识,则前途将不是解放,而是帝国主义的扩张;一旦独立后的国家堕入西方人的叙述话语模式,希望就将变成模拟,人们也将沦为帝国主义者的应声虫。
因此非洲人“发现”,在“粉碎殖民主义压迫的同时,他们正在不自觉地建立起另一个剥削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依旧,只是主人换了副“黑面具”。《河湾》中那个无名非洲小国就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取得独立的国家;但是,其“社会意识”意义上的革命还没有真正进行,因此才产生了“伟人”这样新的独裁者;也就是说,非洲人赶走了旧时的“白”主子,却迎来了新时代的“黑”主人;这个“黑”主人在许多人看来比前任更邪恶。
如果站在前殖民宗主国的立场,对非洲解殖民化的历程更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可能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给了他们进步和现代化,这难道不是真的吗?难道我们没有向他们提供一种秩序与稳定,而这样的秩序与稳定是他们以后未能自己提供的?难道相信他们取得独立的能力是错的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保住殖民地,约束臣民和低等民族,忠于我们的文明职责吗?”在这种思维中,非洲人的悲惨命运自然是咎由自取;唯一的出路是欢迎欧洲人再次君临非洲,再次对这片土地实施殖民和“拯救”计划。萨义德认为,奈保尔成功地说明了上述思想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就能够批评殖民地国家无条件的独立。他对后殖民世界的宗教狂热、政治堕落和本性低劣所进行的抨击,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人对第三世界幻想破灭的一部分……一度指向典型的英法帝国的权力与权威问题,现在指向了替代它们的独裁政权,指向了主张亚非国家仍然应当处于被奴役和依附地位的思想。”
在某些论者看来,作为来自前殖民的知识分子,奈保尔在《河湾》中通过笔下人物所表达的看法受到了西方新殖民主义势力的追捧。因为“假如你坐在牛津、巴黎或纽约,你告诉阿拉伯人或非洲人,他们属于一种基本上有病的或不可救药的文化,你很难说服他们。即使你能说服他们,他们也不会承认你根本的优越性和你统治他们的权力,尽管显然你很有财富和权力”。现在,从前殖民地杀出一个“无情的、诚实的奈保尔”,断然声称他们的苦难是“咎由自取”,当然比宗主国的白人费尽口舌的论证更为动听,也更具说服力。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奈保尔挑选了萨林姆作叙事代言人。他尽力让萨林姆做出貌似客观公正的判断;只有这样,关于“一无是处”的非洲和非洲人“在此世界无处立身”的结论,才更具效力。摆脱了种族、宗教、历史、记忆、家园、国族等一切羁绊的萨林姆,当然最有资格站在客观的立场讲话。更何况他在这个无名小国有丰富的流亡经历,甚至能从西方的他者的角度来反思自己,试问还有谁比他更适合传递奈保尔“世道依旧”的断言?
四
问题是,在宣布非洲人“一无是处”的时候,奈保尔是不是径直在为欧洲新殖民主义铺路搭桥?有论者指出,奈保尔是“新殖民主义的代言人”。新殖民主义作为西方残留下来的影响,已无孔不入地渗入前殖民地的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中,渗入与西方国家纠缠在一起的经济网络中,因而与殖民主义一样,也是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同帝国主义和旧时代殖民主义一样,新殖民主义也有这种预设: 西方/白人殖民者地位高于黑人/本土被殖民者,前者有权利压迫后者,后者的作用只在于凸显和强调前者的优越性。充斥着《河湾》的对“一无是处”的非洲人的大量描述,似乎验证了奈保尔是新殖民主义帮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