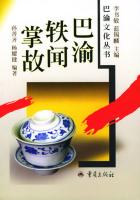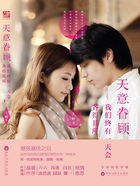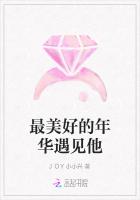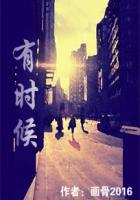六十年代的革命,不只是对一般的文化的革命,也是对文化的细胞――中国人传统的日常生活及其常识的革命。不仅小家庭成了革命的对象,旧时代的家具、烹调、家常话、住房、人和人的交往的基本原则都成了革命的对象。例如,为了某派的主义就告密、大义灭亲、把所有四合院及其家具都视为封建地主的遗产、在家庭邻里之间划分阶级、把城市生活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我以为,我们还在体验着这种革命的后果。最近,我到昆明那些新建成的街道上去走,发现,这些街道不是为中国传统的日常生活建设的。它是为汽车、银行、超级市场和一种陌生的生活方式而建造的。它没有为裁缝铺、老字号的酒店、茶馆、纸烟铺、补鞋匠、咸菜铺、酱油铺、卤菜店……这些“小市民生活方式”留下位置。它的建筑语言像我们在革命时期早已熟悉的那样,高大、全面、宽阔、明亮、崭新、统一、标准化、高度集中、康庄大道以及来自“别处的”……我应该已经可以像学习尼采、海德格尔那样学习中国过去历史中那些伟大的圣哲。我以为,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对他们的疏远、否定之后,在“子日诗云”已经普遍地为某某斯基、某某马斯或某某主义说……全盘替代了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可以真正明白他们的一成不变是在说些什么了。我指的是我自己应该把他们当做指引世界历史方向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经典来学习。
写作(诗以及其他)为什么先验地一定要表现出所谓的“美”,众所周知的、经典的或先锋派的;或者如果与此相反,反抗的写作就一定要以丑的面目出现,同样的众所周知的、经典性或先锋的。我宁愿我的写作仅仅是一种语言的记录,而与什么美或丑无关。但仅仅是记录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表现美或丑已经被世界规定为写作本身的存在的惟一理由、惟一方式。所以,写作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它不单单是灵感、生活经验和写作中的技巧问题。写作本身是一种回到真理的斗争。
在下面,想起了位于世界最高处的西藏。那里的人们没有我们这些住在下面的人所谓的远方和更美好的,在那边时间并不是指向未来的,也不跟着所谓时代前进。在那边时间是原在的。在拉萨,我从未遇到一个对下面的富裕津津乐道而准备投奔的人。相反,我经常遇见那些一贫如洗或者脖子上挂着其价值可以买一座庄园的宝石的人,一步一叩朝高处走去。人们只到神所在的地方去,到拉萨去、到定日去……神的寓所在高处,没有谁要到下面去。照理说,西藏应该是生存条件比四川湖南都更恶劣的地方,他们完全可以像内地民工一样跑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去,但在内地和沿海,你很难遇见到一个西藏人。对他们来说,人生的终点在上面,在神的周围。西藏人是有家的人,原在和守成的人。我回忆着他们的面孔,像岩石一样坚硬,被高原阳光和风塑造过,宁静,守候和憧憬着。
许多诗人对乌托邦话语津津乐道,因为谈论这种东西总是可以在群众中获得某种优越感,在人群中处于“比你较为神圣”的地位。但如果回忆一下本世纪尤其是六十年代的历史,乌托邦话语不正是一种最常见最庸俗也最霸道的话语么?今天的诗歌中的乌托邦话语与六十年代不同之处是,“生活在别处”中的这个别处在六十年代指的是时间上的别处(将来、总有一天),在九十年代这个别处现在转移到了空间上(与西方的接轨,语言资源、玫瑰的嫁接、欧洲的诗歌节)。
二十世纪是一个崇尚升华的时代。任何常识性的事物,都要拔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去看,这是意识形态。但日常生活又何尝不受到这种拔高的影响。今天,你看报纸,还常常会看到什么“某某领导冒雨视察……亲临灾区……”(难道这不是他拿这份工资应该做的工作,难道要在大晴天、世界太平的时候去才是正常?)在学校里,老师经常表扬学生什么“上课专心听讲、不讲小话……”并据此评比优秀,这难道不是一个学生最基本的要求么?在诗人中,这种升华甚至以为诗人比诗歌更崇高,诗歌写作不如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所以出现许多诗歌平庸,但敢于自杀当诗歌烈士、敢于危言耸听的人。诗人不以为他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写诗,而热衷于什么“知识分子写作”,试图让某种“救世主”的形象来取代诗人的位置。“升华”其实许多时候并不高尚,它有着诗外功夫,诗写得味同嚼蜡,却通过在别的方面来升华,以获利。
今天在中国有一种怀旧的情绪。怀旧是由于人们发现他们已经无旧可守,对旧的不断革命,大致中国人终于丧失了“旧”。人们会发现,旧并不仅仅如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那样,只是余孽、幽灵、鬼魂。它其实也是中国人日积月累的生活经验。旧时代的生活其实是有一套方法的。它并不是空洞的东西。昆明建城之始,不仅有风水上的讲究,并且它是依据中国式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来建造的。昆明的各种小吃、茶馆、酒楼、药铺、裁缝铺、纸烟铺、咸菜铺,都是与日常生活相呼应的。这些并不是鬼魂,而是一个人的日常经验。昆明人冬天做咸菜、大年初一不能动刀、春天要吃阳春米线、“三月三、荠菜花儿串牡丹”等等的旧都是庸常,但事关人的阴阳平衡。封建主义之类的旧,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恐怕过于抽象。真正与他生命休戚相关的旧,恐怕还是那些相当具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当这些“旧”丧失掉的时候,人会有无家可归的感觉。精神的断裂人们恐怕觉得过于抽象,人们最可以切身体会的乃是“经验的断裂”。昆明现在流行超级市场,方便倒是方便,但人们会发现他们再也找不到的是从前在杂货铺与老板娘聊天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确实是过于腐朽,但它已经被记载在中国的文学中,也是人们的所谓故乡世界的一部分。找不着这种感觉的后果是,当我们从超级市场出来,一个西方人也许可以顺便到教堂里去听牧师布道,以缓释这种方便然而也孤独、乏味、千篇一律的购物所引起的空虚,但一个中国人就发现他无处可去,他的经验是在购物中应该有一个通晓各种人情世故的老板娘与他聊聊,但这个新世界并不是为这种庸俗的生活设计的,他只有郁闷不乐,他只有在一派全新中怀旧,他必须要有极好的记性与想象力。
二十世纪的知识给我们介绍来自西方的各种图纸,它从不说中国过去也有一份图纸,关于世界乐园的图纸。而且这份图纸其实并没有在世界上施工过。例如,这份图纸关于“原天地之美”的设计。正是依据这份图纸,中国人得以在建立了一个伟大无比的文明的同时,也保持着一个没有被污染的大地,这种状态是在不久前才结束的。
云南民俗文化和自然风光素有美丽神奇之称,但许多写作往往对美丽神奇,仅仅停留在“美丽神奇式”的泛泛捕猎上。组成云南文化的最基本的日常性的方面,注意很少。我们不能总是把云南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例外或对象来观察,对于云南土地上出生的写作者,云南是我们的存在的现实,是生产我们生命和文化的基本元素的大地。因此,那种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和写作实际上往往导致的只是对云南文化的遮蔽,甚至毁灭。“今天许多城里人(比如那些个滑雪者)在村子里,在农民家里,行事往往就跟他们在城市娱乐区‘找乐子’一样。这种行为一夜之间所破坏的东西比几百年来关于民俗民风的博学炫耀所能破坏的还要多。(海德格尔)在云南,我一直试图从在者或居民的立场写作,而不是在通常的强调某种特殊性的那种解放者”“救星”的心态上来写作,我试图关注的是云南作为一种生活样式的日常性。云南在某些论者的单向度文化比较中,往往被视为封闭、懒散、落后。并且这是具有贬义的,或者有待“解放”“改造”“升华”的。这种流行的云南文化视角对云南那些原在的文化的毁灭性打击我们还见得少吗?这种流行于云南的民族风情写作,导致的不是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自信,而是对自身文化的异质性的盲目自卑和毁灭性扬弃。我一直试图通过我个人的写作扭转这种风气,但这种写作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对云南生活――它的异质性、它的时间观、信仰、审美风尚、它的日常生活方式(包括它相对于全球一体化的生活方式和时间观的所谓“落后”、“懒散”)的――认同甚至崇拜(在我看来,在某种角度上,云南世界决不是什么“落后”地区,对于已经可以预见的那个将要“克隆”的世界,它恰恰是一个可以使我们保持住对大地和人类童年时代的丰富生活之记忆和想象力的拯救之地)。因此一种对故乡云南大地是认同,而不是解放的写作态度需要的是云南式的懒散的时间、是平庸的感受、是对千篇一律然而组成了云南生命世界最基本的元素的日常生活的激情。这种写作需要的是对某个特定的地区的日子和生活状态的日常性观察而不是猎奇式的追逐各种民俗节日或风光。我试图把生活的“日常性”、把这种日常性所蕴含的所谓“懒散”作为一种写作方式来实践。我的写作强调的是方法,这方法就是要深入到云南生活的日常性中,与它认同,我是云南人,而不是它的解放者。
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内心宁静如古瓶的人不多。先锋派,主义,如走马灯般充斥艺术。许多人相信,只要掌握了某种主义,也就掌握了艺术的命运。偶然走进画展,汗牛充栋的皆是生活之恶,阴暗、压抑、变态、玩世不恭……但同时看见艺术家们穿着高级时装,交换着行情,及时行乐,体验着大厅外阳光明媚的春天。这个时代,许多画家们是太聪明了,既钻研配制通过行画“先富起来”的秘方,又要扮演愤世嫉俗的“亚文化”艺术家形象。因此,在此时代风尚中,一个以保守自命,依然坚信经典美学的那些老掉牙的普遍原则的画家,要么是由于迂腐而不谙时事,要么是由于固执所以一意孤行。
穿越时间的道路首先并非某种先验的概念,诗歌的灵感来自词。
诗歌是否会跟着时代前进?在八十年代就有八十年代的诗歌,在九十年代就有九十年代的诗歌,从资料的角度或历史顺序的角度可能是如此,但真正的诗歌在任何时代都是诗歌,这个真理的确也是不跟着时代前进的。
不会由于时代前进,那些应时而作的东西就会自动成为诗歌。他们在八十年代不是诗歌,在九十年代也不会由于发生了什么划时代的事件而成为诗歌。有的人以为把他们的东西用知识、精神、灵魂、深度之类的东西包裹起来,就会瞒过读者,有人正在这么做。这种手法我们是很熟悉的,用普泛的概念,例如用人民、我们来瞒天过海的见得少么?把诗歌降到知识的水平,与把诗歌降到意识形态工具的水平同样拙劣。
大海,它传递到所有耳朵中的声音都是一样的。但从汉语、印第安语、希腊语、法语、德语……说出的大海却完全不同。这就是所谓永恒与当下。
二十世纪崇尚的是“升华”,用解放者的眼光看待旧世界,看待大地。把日常生活、传统、大地统统视为解放的对象。以抽象的“终极关怀”否定具体的存在,否定“日常关怀”。
在我印象中,中国今天大谈女权主义的人们都是些知识分子。女权主义的客厅充斥着拉丁字母和干瘪的乳房。这种女权主义究竟何年何月可以解放妇女,恐怕只有天知道。我以为在中国讲女权主义,毛泽东恐怕是先驱,“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华儿女多奇志”“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倒是真的解放了妇女,把中国男人都搞怕了,告密、斗争、开会、批判、武斗……这些历史上只是男人干的事,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不也大干特干么?我这一代人印象中的妇女,其实和男人差不多。比起一百年前在闺房里绣花的娇小姐来,六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恐怕更像男性。比男人更革命的是,妇女们连装束都革命化、男性化了,以至男人们连惜香怜玉都不敢了。倒是男人保守,幸亏没有把男性革掉。毛泽东恐怕也没有读过什么女权理论,但他这一套确实使中国妇女改变了,是否获得了一些女权?当年投奔延安的丁玲而不是沙菲女士恐怕是有些女权的。但获得了女权的丁玲女士何以对他的旧日情人沈从文那么坚硬,到死都要从路线斗争的高度看问题,而不愿意从一个女人的角度看沈从文一眼,也是我难以理解的。女权主义是否就是要使女士们都变成钢铁炼成的?“飒爽英姿五尺枪”以及“江水英”一直是妇女们的标准形象,很可怕的。现在柔软多了,最近几年,这种形象被年轻一代的靓女们用香水和脂粉瓦解掉了。“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光景重现于世,我现在最喜欢三八节,在春天的阳光中,看满世界飘着如云的美女,心旷神怡啊。永恒的女性,指引我们上升!我以为女性的意义在于,她们总是使一个坚硬的世界变得柔软,变得富有人性。女性很少为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主义所迷惑,她们本能地指引世界从理性的迷惘中返回家园。柔软的女性啊,我们的生命之光!据我所知,新一代青春靓女一般是不谈什么女权主义的。大谈特谈的,似乎是害怕别人意识到她们的性别,要把注意力转移到主义上去。
但我还是以为,女权主义是应该讲的,但不是讲那些枯燥至极的、进口的女权理论。在经历了形而上的革命之后,女权恐怕先要从腰部以下恢复。恐怕要到了女性们潜意识里,不再把床视为意志、立场、银行、户口、靠山、地位什么的,仅仅把床视为床,视为柔软,视为乐园。如男人一般具有主动性,具有纯感官的爱好,而不是什么主义,女权主义才会有质量。
我认识一位女权主义者,她拒绝成为一位母亲。她拒绝造物主赋予她的天赋女权,所以,一听到她讲起女权主义,我就起鸡皮疙瘩。
我非常喜欢音乐,这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你怎么可能一天不吃盐?就是如此,但强调得太多,就有做作之嫌,在这个国家,音乐并不是日常生活,而是修养、风度、文化程度、经济状况。我认识许多由于热衷于买原版CD,就自视甚高,也被诗人们肃然起敬的诗人。我害怕音乐被搞成“仪式”。有一年在荷兰,我对一位荷兰人说,我很喜欢教堂的钟声,他说,我恨死了教堂钟声,它每天八点就要响,影响我睡懒觉。其实我是平生第一次听见真的教堂的钟声,我是从知识上来喜欢它的,因为知识总是把这种声音与崇高庄严联系起来。后来,日子长了,我才发现这钟声日常得很,并不只是崇高、庄严,更多时候是听而不闻。在着,如此而已。它在我的知识中被升华了,割断了它的日常性,在这种知识中的所谓音乐生活,只不过是知识的炫耀。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罗曼?罗兰说,莱茵河一条河都是风琴的声音。这就是音乐生活。我年轻时从文学的角度崇拜过贝多芬。我通过约翰?克利斯朵夫认识了他。但我只是在后来――1975年,在一个阴暗的小阁楼上听到了他的音乐。我永远难忘的一日,我的第一次音乐生活,在黄昏穿过响彻高音喇叭的城市,怀着堕落犯罪的心情,当时,所有西方音乐都是被禁止的。关着窗帘,漆黑的小屋内,有裂缝的黑色唱片,音质低劣的留声机,几个热血青年。我其实根本没有听见,我处于与时代对抗的紧张和亢奋中,我们随时可能被邻居告发。但今天当我有时间,用德国制造的“意力”音箱,把音量放大再听贝多芬的时候,我并不十分接受他的风格。我更喜欢那种“无声”的东西,也许是我在一个充满喧嚣的时代呆得太长了。中国古典音乐在今天,我听起来,常常有神曲的感觉。听崔健的东西必须要有时代背景,中国其他搞摇滚的人也一样,但伟大的音乐是可以超越时代的。时代死去了,音乐永恒。但在这个时代,崔健肯定是最有力的。
长诗是一种策略。问题是,诗人离混沌有多远。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混沌消解策略。
在诗歌中,知识永远是次要的。诗歌的活力来自诗人与混沌状态的关系。但仅仅是混沌是不够的,它可以成就天才,但对大诗人来说,重要的却是控制混沌的能力。
诗人从来都是有两种,读者而来的和天才,但在这个时代,读者在诗歌中占了上风。这个时代的知识太强大了,互联网,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强大。创造者的空间非常小。到处都是炒冷饭的人。
这个时代人们用意识形态的、经济的、技术主义的概念来谈论诗歌。接轨,这是一个经济概念,诗歌成了外贸经济。“走向世界”,这是一个技术的、政治的、经济的概念。
导弹的射程可以有世界先进水平,1000公里的肯定和3000公里的射程不同。后者肯定是更先进的技术。但诗歌的“世界先进水平”是什么?难道英语的诗歌就比没有导弹的印第安人的诗歌先进?那年在鹿特丹诗歌节,有位法国诗人念了一首印第安人的诗歌“云,改变了”。我永远难忘。这肯定是第一流的诗歌。
在此时代,我不得不去澄清那些常识性的、不言自明的东西。“诗歌在世界中”我从来都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多少年,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我存在于这种常识之中。忽然,被批评家们告知,要走向世界,我们原来是在世界之外!要像外贸委员会,依据某个订货单去接轨,干依据中国人的身材把波音飞机的座位改小之类的事情。于是,我不得不出来把常识再说上一遍,“诗歌在世界中”几乎成了箴言。
拉金、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艾略特、奥顿等等,如果离开了具体的诗歌,离开了那些诗歌给我们带来的感动,把他们挂在酒吧间的墙上,写在文字里作为自己诗歌来历的证明,作为权威,那么他们就成了与他们的诗歌相反的东西,令人作呕的话语权力,造成这个权力的不是大师们,而是那些企图“借光”的读者。在今日中国诗歌界的“知识分子写作”中,西方大师其实是被作为一种话语权力来作用的。“某的语言资源是来自某茨基”与“某的语言资源是来自他母亲”难道不是一样的么,为什么前者就视为莫大的光荣?因为前者是一种权力,暗示着一个背景,一种权威,向它靠拢,肯定会有好处,至少会使你成为一位看起来似曾相识的“诗人”吧,在迷信权威的读者那里,离“大师”就是几步之遥了。我认识一位西班牙的业余诗人,我们谈到诗歌,谈到西班牙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门尼斯,这个人的诗译成中文很好,我记得有一首是白色的水井,我告诉西班牙人我很喜欢这位诗人。他说,我恨死了这个诗人。为什么?他的诗是我们的课文,我们天天要背诵,我非常痛恨他的诗。
棕皮手记·1999~2000
我始终坚持的是诗人写作。
世界在诗歌中,诗歌在世界中。因为诗歌来自大地,而不是来自知识。写作的“在世界中”乃是一种常识,乃是诗歌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从杜甫到曹雪芹,汉语从不以为它是在世界之外写作,是为了“被翻译”与某种知识的“接轨”而写作,但这一常识今天已成了少数智者在坚持的真理。诗歌本身就是在世界中的。诗歌不是经济体制,不是外贸,它指向的是世界的本真,它是智慧和心灵之光。在诗歌中,中国人、印第安人、老挝人、澳洲土著与英语世界的智慧并没有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发达或不发达的高下之分,不存在所谓“接轨”的问题。今天,普天下,都是渴望着接轨的人群与他们的知识分子。就像云南森林中的黑豹那样,“在世界中写作”的人已经几乎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