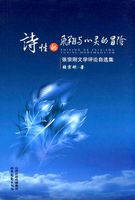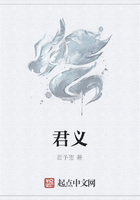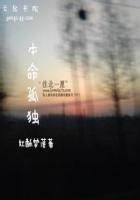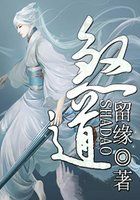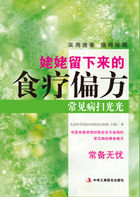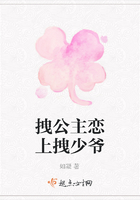作为一个在古典和现代中国学研究中受过训练且有幸经历其中的人,我常有机会在不同领域的学者们所作的研究中进行比较。在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中,有许多人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偏见。但在现代中国学领域,我常遇到一些固执于一端的学者:他们有的明显是在自我指责,有的则或明或暗地从事抨击与攻伐。前者是一些欧洲汉学家,他们不断指责欧洲自身;后者是一些美国和中国学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欧洲,白人,男性。因此,无论这两个阵营发表什么言论或申明什么事情,细心的读者们或多或少都能发现一层或显或隐的意思:对于所谓的被扭曲的中国形象及其近两百年的不幸历史,有一个罪人需要为之负责。在现代中国学领域,我们往往听说“西方”是有罪的,而这个“西方”,差不多就是欧洲。
我并不认为欧洲没有做任何损害中国的事。但我希望表明,我们通常所说的“欧洲”甚至“西方”,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因而需要进行澄清,还历史以公正,并使中国学重获真正的学术性。我并不认为百分之百的客观研究是可能的或必须的,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男女—但是,当一小部分很有影响力的人声称所有“东方主义者”都是罪犯、所有汉语译者都是帝国主义者的时候,那种私人的憎恨已不同于寻常的偏见。
一
1974年11月,我与中国有了第一次真正的会面(之前的接触则都是经由书本)。那时,我与另外9名同学得到机会去北京学习一年现代汉语。临行前,我们在波恩受到了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的邀请。当时,波恩是联邦德国的首都,而我在大使馆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西方摧毁了中国最美的宫殿之一,圆明园。我顿生负罪之感,突然间觉得,不是西方,而是我在1860年做出了如此野蛮的行径,烧毁了那座“光明之园”。从那以后,这种侵略者角色在我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去做这个角色所做的事情,甚至从未主张去做。怎么会这样?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二战结束之后,当时,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很久,我们也接受了美国人的再教育:我们必须去观看关于集中营之残忍行径的纪录片,去听纳粹所有骇人听闻的故事和罪行。当时我们年纪太小,很难真正理解那些事,但我们很快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错误都和我们有关。例如,当得知日本人歧视朝鲜族国民,我们也立即陷入负罪感—但是,这种不公与(我们的)历史有什么关系呢?
直到40年后的今天,我才敢说,不是西方毁了圆明园,而是不列颠帝国和法国。不是德国,不是意大利,不是奥地利、不是芬兰……这些国家在当时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学者们早就应该对真实的历史予以重视,但他们为什么没有这么做,甚至时至今日还在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是“西方”侵略了中国?那不是西方人所为!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在当时根本不存在—当时只有不列颠帝国!但真的是不列颠帝国所为吗?不,是东印度公司(1600—1858)!“东印度公司”不是一个国家,它只是一个受到英国皇室支持,得到皇家海军协助的贸易公司。它拥有的12万士兵是否都是英国人呢?不是的,几乎所有的战士都来自亚洲,因为英国和荷兰公司经常利用当地人。如此看来,与中国人交战的大多数都是亚洲人!另外,鸦片战争后的数十年间,法国、美国、俄国、日本这样的国家相继入侵中国,但是,当时的日本不属于“西方”,而俄国到现在还算不上是一个西方国家!
为什么我们还在简化历史?而且在某些方面,我们的行为与近东地区焚烧德国大使馆(2012年9月1日)的人没有太大区别—那次事件的起因,仅仅是一个埃及人在美国拍摄的视频显露出了反穆斯林倾向!事实上,德国与美国相隔千里,且与此事毫无关系!为什么会这样?我担心,由于历史太过沉重,即使是严肃的学者,有时也需要一只替罪羊,需要用一种简化的方式来让所有的事情容易为人理解—但这种方式已经不再能让历史清楚明白了。
二
所以,一种普遍的看法存在于中国学领域,即无论欧洲的白人做了什么,大概或多或少都是错的。如果我们不译介中国文化,就会被指责为欧洲中心主义;但是,如果回顾近400年来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和对中华文明的引介,我们又会被指责垄断了这一领域。因此,由中国人自己为“西方”读者提供英文翻译,似乎成了必须的、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而大约从2009年开始,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这方面给予了观念上的鼓励和财政上的支持。我非常钦佩他们的工作,但他们能够保质保量,把杜甫(712—770)和李白(701—762)的全部作品成功译成英文吗?在此,我想提醒一言:这两位诗人作品的德语全译本早在大约70年前就已完成,而英语世界尚没有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成果。我还要提醒的是,不应当指责诸如美国这样的国家垄断了翻译,因为他们并不致力于(过多的)翻译。
在我成长的年代,甚至连地名、人名也会成为政治事件。中国的地名人名译成德语或英语,便被指责是一种帝国主义行为。的确,在德语中有Peking,Konfuzius,Nanking这样的词汇,但也仅此而已—几乎所有其他名称的拼写和发音,依照的都是汉语拼音的转写规则。相形之下,也几乎从来没有中国人会使用München,Marx或者Berlin这些德文词,而只会使用其中文译名和发音,甚至在官方报纸中也是如此。
“我们”被指责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充分地了解、或错误地表现了中国—但是,为什么遭到指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虽然其汉学领域仅有初步的工作,却不曾招致批评或非议。2007年,我在印度马德拉斯大学(金奈)时,曾问及他们的中国学研究为何没有充分发展,他们坦率地回答说,印度学生认为,学习中文并不值得。从那以后,我时常对中国的同事们说起此事,但他们并无激烈的反应。但是,曾有一次,他们中有一个人偶然得知一部美国的中国诗选没有收录这位或那位同代的诗人,便对我说:“你看这就是西方,总是把我们排除在外。”不是的,事实上这不是西方,而是美国—那里的译著只占全部出版书籍的5%,但德国则多达70%,其中几乎囊括了迄今为止所有的重要中国作家。这一事实并不为人所知。为什么会这样?非常矛盾的是,这一事实与马克思主义或后殖民理论的观点相左—两者都认为,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永远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因而永远具有排外性,即使其帝国主义历史非常短暂而且并不成功,比如德国。在激进的批评家眼中,我们对中国的错误和不充分的阐释,已经取代了曾经的军事侵略。
这种持续不断的指控始于何时?我认为是在法国1968年学生运动之后。当时,后殖民主义正在逐渐取代左翼理论。然而与此同时,第三世界作为解放力量的幻想、亚非地区在殖民时代结束之后的和平发展之希望,都已经破灭:印度教徒蔑视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内部互相攻伐,非洲的种族杀戮也接连不断,而且,大陆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之间亦有存有敌意。奇怪的是,那些事件似乎还没有被学者们提升到理论的高度,相反,“我们”还在被告知,“西方”过去和现在都怎样地误解了其他文化,特别是亚洲和非洲—可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奴隶制在亚非国家中还十分普遍。
这时候,后殖民理论给现代中国学研究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尽管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从未在其《东方学》(Orientalism,1978)中提及汉学家,但他那种常常以文艺作品作为例证的理论,经常被人们援引,用以讨论欧洲主要思想家和作家如何表现中国。我不认为有什么办法能够简单地解决关于理解和再现的复杂问题。比如,按照一种哲学观点,任何理解都是一种“长距理解”(far understanding),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永远达不到完全的、一劳永逸的理解,总会有一些东西隐匿难见,或迫使我们反思自己的看法。对于一场关于中国的讨论,如果一个中国人仅仅因为他或她是中国人就可以成为评判对错的标准,那么,我们可能还会屈从于盲目的观点,比如,我们可能会从五四运动甚或“文革”时期的角度来把孔子看作一个“吃人者”或封建主义反动派—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并未完成,仍有人在支持它,正如近年来还有人在支持“文革”。然而,我们当真要屈从于这些人的观点吗?
学术并无独一的终点,而是永远开放的。没有人拥有独占绝对真理的特权。任何形式的研究都是一种尝试,而其他尝试途径往往随之而生。但如果研究对象不够丰富、无法提供更为深入的思考,人们终有一天会因其乏味而将之丢弃。不过,对中国历史和哲学的阐释则永远不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对于《易经》和《红楼梦》这样的文本,人们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宣称自己已经臻达完全透彻的理解。
三
自从萨义德开始,有人声称我们“西方人”在研究中国时有一个宏大的计划。2011年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总结:甚至中国领导人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认为整个西方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意图控制中国。不过,我在此并不是要讨论政治,我的主这是为什么?因为人们对他们的预期就是如此—他们是欧洲人、白种人、男性。
四
在传统看来,学者治学应该“不掺杂私愤和偏爱”(sine ira et studio)。我觉得,在现当代学术研究中,情形已经不再如此;与此同时,现代汉学或许已经变成了一门为集团利益服务的附属性学科。我们可以看到汉学的几种发展趋向,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非历史(unhistorical)与普遍化(universalistic)倾向。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就明确地把自己看作西方的受害者,并且发起了一场爱国主义教育浪潮:所有人都不应该忘记鸦片战争之后的种种屈辱。至于如今广受热议的民族、群体或个人之受害者等话题,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讨论,因为我和其他学者都曾有所论及。在此,我建议重新思考另一个通常的见解。根据德国学者的研究,清朝(1644—1911)是一个帝国主义王朝,与俄国、不列颠帝国一样;因此,19世纪的那场战争是对亚洲(中心)支配地位的争夺,而中国、俄国、东印度公司所代表的不列颠帝国以及后来加入的日本都是其参与者—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场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战争。最终,它导致了一些强势国家侵入中国,随后占据着中国的地盘,直到1941年日本控制了所有外来国领地。而一些较小的、如今也被称为“西方”的国家,则根本没有力量、也没有兴趣去中国。
德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其形成也较晚。由于受到不列颠帝国的阻挠,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同中国发展贸易。最终,德国“成功地”在青岛建起了“保护领地”(protectorate)(1898—1914),但实际上,它极为弱小,以至于没有力量用军队来进行管制,因为那里的中题是学术,或人文科学。
我不否认,在19世纪或冷战时期,有一些学者将其学术事业当作武器,但最近以来或1979年之后,中国和中国之外的研究者们一直在进行合作。如今,固执于“你们和我们”相对峙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用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方”来谈论中国,中国肯定不高兴。但是,为什么在谈及“西方”时,德国总是被包括进去,即使事情与德国毫无关系?中国学者由于语言不通,常常凭借美国而非德国的出版物来评判德国。然而德国和美国差别很大,有着她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如果我们仅仅因为语言能力不足而无法阅读中文资料,就转而借助韩国或日本的出版物来评判中国,中国会同意吗?中国人对德国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好莱坞的影响。真要感谢美国电影,它让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了德国人是什么样的—他/她就应该像一个纳粹!就这点而言,我可以举出很多具体的例子,但这样做会引起不快,所以我们还是换一个话题。
我想说的是,尽管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必要性,然而,理论从来不足以解释历史的复杂性。1895年,是日本打败了清朝,而非西方。1905年,是日本打败了俄国,而非西方。1941年,是日本完全控制了上海并使许多欧洲人蒙羞,而非西方。我们必须使用非常具体的词语来再现历史,并认识各个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否则,或许冰岛这样的国家也会连带地被指责曾侵略中国。
更成问题的则是中国学研究中的“普遍化”倾向。我们都听说过一句俗语:“古已有之”,即,某些事情从古代起就已经存在。如今,在现代与古典中国学领域,美国人和德国人都加入了这一潮流,而这种趋势大概始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这些声音在美国和德语国家非常流行,中国学—以及中国本土的相应学科—已被它们占领。相比之下,法国学派(弗朗索瓦·于连[Fran?ois Jullien])和波恩学派(陶德文[Rolf Trauzettel])则是这一潮流不太成功的反对者。
这种普遍化倾向的问题何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许多不想再“羞辱”中国的学者们都发现,欧洲在非常晚近的历史中所“钟爱”的所有东西,其实都包含在中国古典作品之中,比如民主、公民权利、人性、主体性、个人主义、爱国主义、现代性等等。但是,诸如此类的西方术语自有其历史,有时是久远而复杂的历史,而那些主张中国从古至今都具有“进步性”的人,则很少考虑到这些。
在我看来,美国的现代中国学研究如今已经或多或少被中国大陆学者所占领,他们殚精竭虑地去证明,中国从来没有“落后”过,而是一直都很“现代”。但是,“现代性”对于一个德国的思想者而言则是最不好的东西。“落后”有时候更具吸引力。个人主义等现代现象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像哲学家奥多·马尔夸特(Odo Marquard,1928—)这样的德国学者会回答说:个人主义有其局限,应该让位于对传统的重新思考。
所以,应该怎么办呢?学者必须自行回到源头本身—不仅是中国,欧洲也一样,学者们必须去阅读原著而不是译著。但是,美国学术经常是“教科书学术”(textbook scholarship),他们谈到关于中国的话题时,每个人读的都是译著;甚至对于思想极为复杂的作家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也仅通过译本来了解中国。在中国,很多学者只能熟练运用一门语言(汉语),美国的学者则可能掌握至少两种语言(如英语和汉语)。然而,中欧的学者必须精通十多种语言,但遗憾的是,他们无法用这些语言与欧洲以外的同行们进行沟通。他们来自小国家,来自“古老”的欧洲,其帝国主义可以说已是陈年旧事。然而,他们仍被归入帝国主义的“西方”—但是,从古至今,波兰哪有什么帝国主义呢?
如果我们细心阅读史料,就不会如此这般地进行概括。例如,鸦片从16世纪就进入了中国市场。我们总是被一遍又一遍地告知,鸦片与《圣经》一同进入中国,于是,我们仿佛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鸦片和《圣经》是一回事,西方过去是甚至现在也是邪恶的化身。但有时,中国的鸦片事件并不像听上去那样简单:比如,这些贩卖鸦片的人并不一定都是西方人或英国人,他们有时也来自亚洲国家;他们依靠中国官员的帮助,也通过中国海员来销售商品;最终,皇室还从鸦片贸易的税款中取得收益。因而可以说,其中有许多不同的力量在共同起作用,包括美国,否则,这笔赚钱的生意不会将中国削弱。
最后,请让我引述黑格尔(1770—1831)的话来结束我的反思。他曾说,在任何既定的文本中,都有一个友好的词语等待着我们和我们的阐释。在我们阅读一些欧洲学者的著作时,遵循这一建议,寻求对中国进行更为开放的理解,而非时刻警惕于其中的错咎,难道是不可能的么?这种非常普遍的、甚至非常流行的“怀疑的解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难道没有尽头吗?2006年11月,一家中文报纸错误地引用了我的言论,而一位英国的出版商随即就在香港的《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指责我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者!然而,要知道,不列颠帝国至今还有殖民地,而德国自1914年后就再也没有了!
虽然我曾接连不断地对当代中国文学进行严厉批评,但在这背后,对于支持我的这个国家和人民,我仍系之以深情—否则,我也不会每天劳于译事,去担任中国作家和德国读者的仆人。
(郭雅然译,时霄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