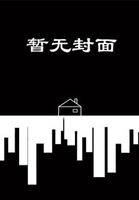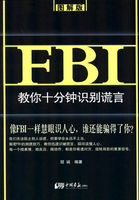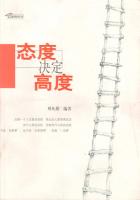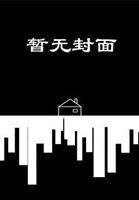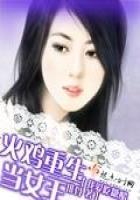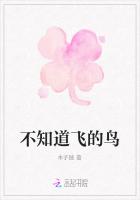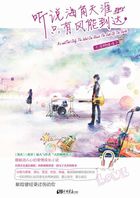宽容大度是一种美德,是一种良好的个人魅力。古来有所成就者,多有不计前嫌的博大心胸,事实上,这是目光远大的表现,既是给别人机会,同时也是给自己机会。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与臣属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经过密谋后,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当天,高祖下诏书大赦天下,并下令“国家军国庶事,皆由秦王处分。”
三天后,高祖又下诏立秦王为太子,诏书称:“自今军国庶事,事无大小,悉委皇太子断决,然后闻奏。”八月,高祖又下诏,正式传位给太子世民,自己退居太上皇。从此李世民当上了大唐帝国的第二位皇帝,是为唐太宗,次年正月改元“贞观”,开始迎来“贞观之治”的新时期。
李世民执政之初,局势并不容乐观。虽然建成、元吉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但是他们经营筹划多年,在朝廷内外和地方上都有相当强大的势力。因此他们死后,原东宫、齐王的势力仍然存在,他们处于与新皇帝敌对的位置。如何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些不安定因素,成为玄武门之变后摆在李世民面前的首要问题。
对于东宫和齐王府的敌对势力,李世民的态度有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
起初,李世民对这两大敌对势力实行高压政策,在玄武门之变的当天,就令部将把建成的四个儿子、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杀死,斩草除根,消除后患;又下令绝其属籍,家产全部抄没。为了迎合李世民仇恨建成、元吉的心理,一些部将甚至打算将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全部斩杀,李世民没有反对,而是以默许来表示赞同。
对李世民这种株连政策,大将尉迟敬德坚决反对,他力排众议,大声对李世民说:“罪在二凶(即建成、元吉二人),他们既伏其诛,如果再连及支党,不是求得安定的良策!大王如果想得到人心,千万不可株连过多过广!”
尉迟敬德主张不扩大打击面,这对安定当时局面来说,确实是一条良策,因此李世民很快就醒悟过来,立即制止了部将滥杀无辜的建议,同时向高祖请求下诏天下,称“凶逆之罪,只止于建成、元吉二人,其余党徒,一概不问其罪。”可见李世民很快就改变了策略,对原东宫、齐王府的势力转而采取宽大政策。
这一政策的改变果然立即收到成效。就在六月五日,也就是玄武门之变的第二天,曾率领东宫、府卫兵进攻玄武门秦王势力的建成心腹将领冯立和谢叔方就来向李世民自首请罪。
在招降东宫、齐王府余党的同时,李世民对其中的一些才干出众者更是另眼相看,将他们和秦王府臣僚同样重用,有的甚至引以为心腹。如被流放到崔州的原东宫属官韦挺,在召回之后,李世民授以谏议大夫之职,留在身边当自己的顾问,而对原太子洗马魏征,李世民更是倾心相交,在对待原东宫属宫中尤为突出。
在对原东宫、齐王府党徒实行宽容政策的基础上,李世民终于化解了敌对势力,还为自己网罗了一批文臣武将,为“贞观之治”的繁荣强盛奠定了人才基础。
李世民礼葬太子建成,又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他的“宽心”谋略。李世民杀建成,毕竟有违封建伦理道德。
为了消除这方面的不良影响,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冬十月刚即位不久,就下旨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元吉为海陵王,谥曰“剌”,借此表明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和李世民的仁爱之心。然后,李世民又下令以礼安葬隐太子建成,以皇子、赵王李福为建成的后嗣,亲自送建成棺柩到千秋殿西门,痛哭志哀。
与此同时,李世民又接受魏征等东宫旧属的上表,允许原东宫和齐王府的属官前往送葬。李世民这一招运用得非常巧妙,因为魏征等人的上表一方面肯定了建成的被杀是罪有应得,玄武门之变是正义之举;另一方面又从封建礼仪上论述了送葬的道理,认为这样做既不背人臣之礼,又有利于消除原东宫、齐王府臣属的仇恨情绪。
对此李世民当然乐意接受,于是原来十分激烈的秦王府与原东宫、齐王府之间的矛盾也借此机会得以消除,李世民也进一步取得了各位臣僚的忠心支持和拥护。
正是依靠这种宽心策略,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之内,就迅速缓解了原东宫、齐王府臣属对自己的仇视情绪,并对他们委以重任,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和原秦王府臣属共同辅佐自己,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由此可见,真正胸怀全局、欲谋大事之人从来都不是激进之徒。宽容是人们立身立德之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