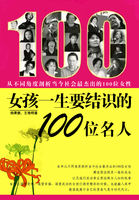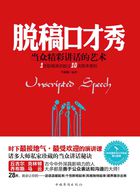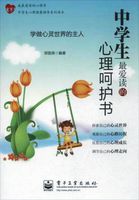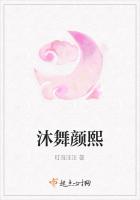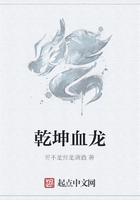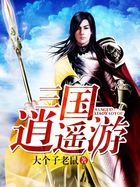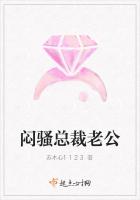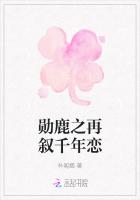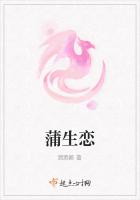越是动乱时期,人才越显得重要,天下之争,实际上就是人才之争。三国时期,曹操、刘备、孙权在用人上各有独到之处,因此能形成鼎立之势。而曹操是其中最杰出的,他手下的能人最多,实力也最强。
袁绍和曹操一起兴兵讨伐董卓的时候:袁绍问曹操:
“如果这次兴兵不能胜利,我们以后将依靠什么来完成大业呢?”
曹操反问道:“您认为该怎么办呢?”
袁绍说:“我将南面依据黄河,北面凭靠燕、代,合并少数民族的兵力,然后向南去争夺天下,差不多会成功吧?”
曹操没有正面回答袁绍,而是说:“我不像你这样依靠地理环境和外族势力。我只任用天下有智力的人,用道义去统御他们。如果这样,就会无往不胜。”
这句话充分体现出曹操对人才的重视。“任天下之智力”就是曹操聪明和老练的地方。
曹操在颁布的《封功臣令》中指出:“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
曹操用人,被公认为是唯才是举、重才不重德的典型。其依据便是他为求贤而下的著名三令:
建安十五年下《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何)尝不得贤人君子与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建安十九年下《有可取士勿废偏短叙》: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止矣。”
建安二十二年下《举贤勿拘品行令》
“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综合分析曹操的三次求贤令归结起来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我干事,不管你是什么人!然而在此之前,从他初举义兵到平定北方鼎足三分,他已用了许多人,谋士如郭嘉、许攸、荀戚、荀攸等等;降将有张辽、张绣、张鲁;
隐士有田畴、邴原;文士有王粲、陈琳等等。他们众星捧月般围绕在曹操的周围,或运筹帷幄,或决胜千里,或文或武,或隐或仕,都能不失时机地为曹操的事业添砖加瓦。
毛介曾为曹操出了最有决定意义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掌握政治主动权的策略;许攸、荀彧为官渡之战的最后胜利立下了大功。当曹操准备从官渡退兵时,荀或制止了他的行动,让他坚持下去,以奇兵攻袁绍。后来许攸从袁绍处投奔曹操,出了火烧鸟巢粮草之计,从而一举破绍;而在曹操北征乌桓、扫平袁绍残余势力之时,郭嘉抱病随行,临病终之时还为曹操留下了锦囊妙计,使曹操不费一兵一卒,就得了袁绍两个儿子的首级。隐士田畴本是幽州牧刘虞的从事,后刘虞被公孙瓒所杀,他因不能替刘虞报仇便逃到山中。在曹操征乌桓时,田畴毅然出山为曹操做向导,开山引路,出其不意地打败了乌桓。
至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虽然“一言不发”,但作为曹操礼贤下士的幌子,毕竟也算一用吧?并且徐庶既不能为刘备出谋划策,便等于刘备少了一个助手,曹操便有比刘备多用一人的可能,这也算是一种用人的方式了。
而所有这些人,都与令上的标准有差异。从令上标准看,曹操用人也拘品行!
假若关羽不义,也来个陈平那样的盗嫂受金,曹操是否会让他杀人不偿命地过关斩将千里走单骑,就很难说了。
还有毕谌,本为曹操别驾。张邈叛变后,劫持了他的母亲兄弟和妻子。曹操对他说:“你的亲人都在张邈那里,你可以到他那里去。”毕谌当时叩头表示忠于曹操誓无二心。可从曹操那里一出来,就偷跑到张邈那里。等到叛变被平定,毕湛被活捉,大家都替他担心。可曹操却说:“一个人如果孝顺父母,难道不也同样会忠于他的君王么?这样的人,正是我所要任用的!”于是曹操不但没杀他,还把他任为鲁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