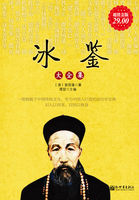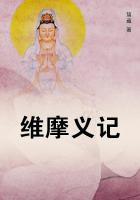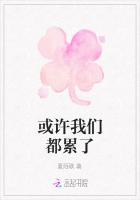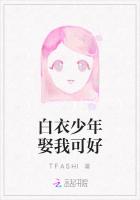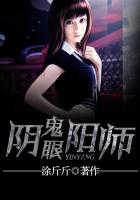精明强干的人,长于随机应变,短在缺乏深思熟虑。
深思熟虑的人,深谙静默安处的道理,短在行动迟缓,缺乏机变。这两种情况正是阴阳两性的区别。汉代李广和程不识就是这两种类型的人。
聪明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种:聪明外向和沉思内秀。
聪明外向的人说了就做,办事干脆利落,迅速果断,手段娴熟老辣,绝不拖泥带水。这类人的缺点是较少进行深入细致周密的思考,凭直觉、经验和性情办事的成分稍重,因本人有力量,也聪明,算得上是有勇有谋,但总的来说勇多于谋,深思熟虑较少。这样办事难免有顾及不到之处,也有可能会因忽略了某些细节而埋下隐患。
沉思内秀的人长于思考,出谋划策兼顾方方面面,给人行事细密周全的感觉。他们做事不像聪明外向的人那样轰轰烈烈,但能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他们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身手不够敏捷,还有可能会因过于求稳而丧失机会。他们知道轻重缓急,虽比较小心,但大事情上不糊涂,能把握方向。
这两种人都有开疆拓土、锐意进取的能力,前者以勇敢闻名,后者以稳重著称,做事风格虽不尽相同,但都是独当一面、办事稳妥的将才。
李广与程不识都是两汉名将。李广的祖上李信是泰国大将,曾率数千人攻逐燕太子丹(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是他一手策划的),并生擒之,后因夸口用二十万人可灭楚国,失败而归。李广生得一双猿臂,精于骑射。一次率百骑突击于大漠之中,追杀三个匈奴射手。大漠沙盛雪,旷野驰骋,李广一马当先,独弓射杀二人,生擒一人,返回途中与数千匈奴兵不期而遇。汉兵一时大惊,立时想在大敌广漠前逃奔。李广急忙拦住说:“大漠旷野,如何逃脱得了性命?不如留在这里,他们反而会起疑,不敢贸然进攻。”
李广率百骑大模大样地进到离匈奴兵二里处,命兵士下马休息。匈奴兵素闻李广勇名,疑惧未定,不敢出击,有白马将走出匈奴阵列,李广飞身上马射杀之,归队后命兵士们歇马解鞍,卧地而息。
由日暮相峙到半夜,燕山月似钩,旷野静默,匈奴兵终不敢击,又怕中埋伏,竟悄悄撤退了,李广将士全身而还。
李广勇猛善战,又会用兵,而且体爱下属,所得赏赐全部分赠部下,领兵四十余年,家无余资。行军打仗没有严格的命令约束,宿营时人人自便,不设哨岗,但从未遭到袭击。兵士部属们都愿意为他效死命。
与李广同时代的程不识,也是边关名将,以治军严厉著称。行军打仗纪律严明,号令整齐,宿营时多设岗哨,兵士不得乱走,因而也不曾遭到袭击。程不识说:“李广治军很简单,但如果敌兵突然发难,恐难以自保。但军士却能因其宽松仁爱而死命以效。我军虽然严肃紧张,少了活泼气,兵士也不自由,但能团结凝聚,从不懈怠,听令而动,因此敌人也不敢侵。”但相比之下,匈奴兵更怕李广,兵士们也以随李广为乐,而苦从程不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论道:
治军以严为首,如无制度约束,就太凶险。李广让士兵自由活动,以他的才能胆识,可以这样,但其他人则不可这样。效法程不识,虽然无功,但不会失败;效法李广,又无李广之才,则祸患暗生,不被敌人击败,就会因内讧而败。
看他们的行动风格可以判断,李广称得上是聪明外向的人才,程不识属于沉思内秀之人。他们都是当时名将,都能建功杀敌。但二人结局并不一样,士卒苦于程不识。
但程不识因严谨自律,最后官至太中大夫。李广骁勇善战,立功无数,名震天下,因不服老,随大将军卫青出战匈奴,迷失道路,没能按预定计划与卫青合围匈奴,致使单于夜遁逃。按军法,失期当斩。回京途中,李广喟然长叹:“广年60余年岁,终不能复对刀笔吏。”于是拔刀自刎而死。士卒百姓皆为之涕泪。到李广的孙子李陵投降匈奴,李氏一族名败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