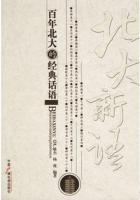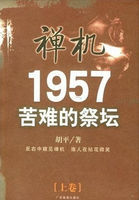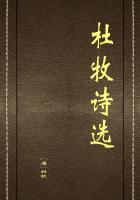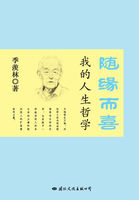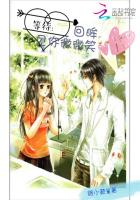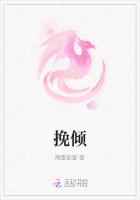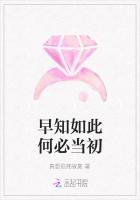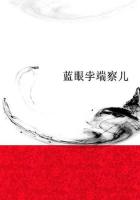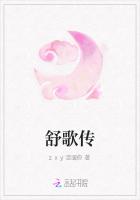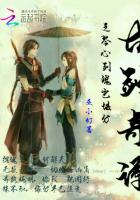而且,诗中用这些材料;并不是用它的实质,只是用它这一点点提炼过的味儿,拿来暗示,形容,比况。譬如雎鸠原不见得像文王后妃,而斑鸠儿是可以引起下文“窈窕淑女”的。桃花与新娘子的关合更是“其妙不可酱油”,却并不曾有谁说,她的脸不含胡地有如桃花瓣。除非你直接经验过,再不然你与作者的经验至少有一两点的类似,又能够“以心会意以意会心”地体会得作者甘苦,这方才可以说你熟悉这些材料。若说考证,非但既不清而又难信;即使考定了,所得的结果多半是呆的,死的,不中用。所以把捉这些名物的氛围,难于考证它们的实质。
譬如灯,我们有电灯,汽灯,洋油灯,通都大邑里已少看见“油盏”。古代的灯是何形式,我原也弄不清楚,但毕竟有点像我小时候夜夜可以看见的油盏火。所以我对于古代的形容,什么“灯花报喜”哩,“残灯明灭”哩,“青灯黄卷”哩,都还有点了解。小孩子却不然了,我的儿女看见《忆》中的插图,他们就不识,讲而后识。夫讲而知,则所知微哉!文学中所要的只是真切的见。
若从历史博物馆看“灯”去,那又是另一回事,或者是看希希罕儿,或者是好古董,或者是专门研究;但决不是读诗的方便。想起来也会失笑,灯与诗又何干呢?那么,它的形式功用等等原该不在话下。我们要知道的是灯前的生活,这才是诗的材料,值得一晌的沉吟与一霎的低徊。──这话或者说得“溜”了(吾友莫须有先生最不喜此)。你去寻检书籍,考订实物,未始不可多增一点了解,反正总比什么不理会的好。但增加多少,实在是个疑问。增加太少,那也不值得提起了。上边的话,未为“溜”也。
和名物典章有关连的,这也不过诗的一部分,有些自然是无关。但无关的不见得就好懂。另有一种说不出,画不出的个性之别,古今情味之异。(我想,中西之异亦然。)这一种隔阂是生于作者读者的关系上,述说尚易,确指则难。我们读五言诗的兴味胜于读四言,读近体胜于读古体,读词曲胜于读诗;这不一定因为古代作品中实质的隔阂多,一半因为作品离我们近的,则无形中之隔阂少也。又如我们喜观陶诗胜于谢灵运,表面上的理由,谢雕琢难懂,陶平易好懂,其实不尽然的。世上也正有喜欢温李比元白更多的人,足证上说之无根。这无非性分的同异罢了。读者与作者近,他们的时代环境相近,一近则无不近;反之,一远则无不远。所以我说,读者的了知,除媒介的故障外,更受一种我与彼的限制,远近亲疏的限制。这也是天生的,没有法子改变增减的一种命定耳。
现在完全转到读者方面来了。我们读一首诗,好像自己完全是旁观,是被动;换句话说,与那久已写定刊行的诗的成就,毫无关系。析言之,则又不然。一首诗写定刊行以后,实在只做了一大半,还有那一小半等着咱们读者去补呢。虽同是读者,而你我不同,所以那补成的半首当然各式各奇,差别得很小,不容注意的也有,差别得很大,不容不注意的也有。
这个道理实在很容易明白的。假如我身完全是个被动的机械,则归斯受之,似别无问题,却还不能算旁观。如无线电机,发是动,收是被动,但也没有谁肯要这有发无收的无线电。况且,我身即使至陋,我敢武断,决不是无线电可比,虽然机械的人生观我也有点赞成。生命情思之交流是何等的微妙呢,读者的地位,完全不是旁观,不完全是被动。他时时给一件作品以新的生命──解释。
为什么不完全是被动?上节的譬喻似乎还不够。在“初见”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被动;刺激由外而来,作品总是作者给的。我读诗和我做诗确是不同,在这一点上。但是,注意,仅仅在这一点上!初见以后诗已融合于我,即胡思乱想,头痛脑涨,废寝忘餐,都是自己干的事了,不和人家再有什么相干,也没有人肯负责任的。再用个薪尽火燃的比方,作者好比一蓬野烧久已烧过了,却藉一种因缘留下星星的火种,──真是一星耳,不知历几何尘劫,这一星火种齐巧不巧,会钻进一池煤油里去,自然又蓬蓬勃勃起来骇人听闻了。只要想一想第二次大火与第一次大火的关系,则于吾言无庸疑矣。
读者的地位既已诠明,更得析言情思交流的状况。假如作者是鹿豕,读者是木石,鹿豕有感,木石无灵,其精诚等于面壁。假如作者是鱼而读者是鸟,作者是渔而读者是樵;那么,跃渊者不知戾天之高,斫柴的不知垂钓之乐,这也完了。又假如作者是形而读者是影,作者是音而读者是响,那就是庄周所谓“莫逆”,片言只语无所用之,更何有于文字,更何有于文学哉!这另是一种完了。自然,这“假如”真是假的,无绝对的同与异,等于木石的人则径谓之木石,何妨。
我们都是平平常常的。我敢说,人永远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作者有他的喜怒哀乐,一个读者有他的喜怒哀乐,不尽同也非尽不同,不尽异也非尽不异,可通却也非尽可通,不可通却也非尽不可通;这是一种错综。作者有了一个,读者可遍大千,宇宙之内,作者们与亿万的读者们吸引排抵,亿万的读者们互相吸引排抵;这是一种广大的错综。作者未作以前对他人的作品是个读者,既作以后对自己的作品也是个读者;读者在未读以前许也是个作者(也许不是),既读以后也可以算是个作者(理由见上);这也是一种广大的错综。创作与诵读二者互为因缘,无有穷尽;这是不思议广大的错综。在这种光景下,得一种电信收发式的了解是否可能,原也不消说得。有人问我,“诗可以懂得吗?”我先要反问他,“何谓懂得?”若说,“譬如电信。”径曰“否!”
离开了解,诗是不存在的,不寓了解,则读者的重要并不亚于作者。依续成未完的诗这个观点说,不妨说误解也是正解。说得激烈一点,简直不妨说误解以外无正解,至少也可以说离开误解则得不着正解。《易传》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此非正见,是名正见。论道之根柢非知亦非仁,特从仁人知士所见的,确也是道之一种形相。说仁知非道,则无一非道,而道竟亡矣,乌乎可!故曰“非正见是名正见”。
深言之,有这么一种玄学的说法;浅言之,凡误解之甚者,通常不名为正解。这又把它们分成两橛了,似乎真有点矛盾。我试以和解之说进。
性分之特异者为偏见,偏见生执著,执著生烦恼。本来我见只是宇宙间的一种见,故虽误而不误,知误而后不误也;后来却认我见为宇宙间的一切见,不误而误,不知误而竟大误特误也。申言之,同异是自然的形状不为累,缘同异所生之是非,足为累耳。自来说诗者,各名有见而所见异,谓己独是而人皆非,察及他人,情有同我;于是谨饬之士转生迷罔,狂放之徒肆为轻诋,门户初严,习染愈深,如此循环,良堪悲悯。冥合作意既不可知,自圆其说亦属良苦,徒以尘点篇籍,灾祸梨枣。其尤甚者,则敢于大言,以一己之硗确,为来学之康衢,贻误贻惭,盖皆难免。凡斯之流俱不得引用圆融之说,为遮羞之具也。
总括上文:诗的本身,一座没藤萝的峭壁,诗人的睥气,胡里胡涂,七扭八捏,读者又是个陌生的客人,在风沙里戴着有色的眼镜,找不着路,互相咒骂。几重的障,几重的网啊!这么说起来,诗总是尽够复杂,微妙,幽沉,几乎神秘的了,还不能证明它不是一句普通话。为什么不是呢?
以上云云,皆属戏论,魔障者何,譬之空花,善读诗者不当泥此。致力于形迹之内,得力于形迹之外,音训粗通,大义斯畅。“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是风景不殊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斯情思可通也。无言悬释,宁待烦言;俯抬即是,何烦冥索哉。五柳先生之“不求甚解”,意在斯乎。视诗为咒,不知所语云何而终身诵之,固失之陋;视诗为谜,以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耳”,亦贤者之过矣。吾之说诗,仿徨歧路,无所适从,欲求陶公所谓“偶有会意”渺不可得,欲仿陶公之赋“归去来兮“,吾将安归乎!属稿既毕,真不知所语云何,自叹有如梦呓,上节讥弹之词即为此文他日之定论矣。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