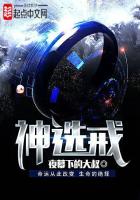“阮总裁开什么玩笑,你现在的身边可有一位漂亮的女主角。我记得,你的规矩是从不同时脚踏两船。因为这点,叫许多女人趋之若鹜。”
阮维东眸光一戾,像利刃般地划过她的脸庞,那声音却是问得漫不经心,“这么说,你已经见过她了。”
任雪晨身体微僵,明明餐厅的中央空调系统好得很,握着酒杯的手心里,却是汗渍漫出。强压下慌乱,苍白一笑。
“紫鑫酒店,不是与安小姐有过一面之缘吗?”
“我有说过是她吗?”
轻描淡写一句,叫任雪晨心里却是陡地一凉。
自始至终,从分手到后来她也小心翼翼地去找过他,或者制造偶然的机会相遇,他都不曾提过,那个女人具体是谁。
她的这一语,无异于不打自招,告诉他她找过安槿的麻烦。
那种凉至骨髓的冰冷,迅速在全身里漫延开来。她怎么可以如此愚蠢,犯下这般低级的错误。
六月的天,像飘过十二月的雪。
任雪晨低着头,不断地与自己说,镇定,镇定,不要慌,不许慌。然后,在唇角边绽放一抹巧笑嫣然,看着他。
“你和她一起吃饭,我碰见过,当时,我和我的朋友就在那个餐厅里。”
彼时所见,他对安槿的照顾,无微不至,小到伸手替那女人拭去唇角边的残汁酱液。
那女人明明不领情,甚至对他呵斥,他却乐在其中,看似霸道的动作却是温柔无比。
那种眼神,是她陌生的,也是她渴望而不可求的。
原来,他喜欢的并不是温顺无比的女人,亦非妆容精致的女子。
那日她所见的安槿,脚踏拖鞋,一条发旧的牛仔裤,上身套一件宽大的T恤,毫无形象可言。
他却紧执了那人的手,十指交缠的姿势。向来注重仪容的他,却容忍了那个女人的随意。
嫉恨就像疯长的藤蔓,缠绕住了她的心脏,勒得生疼。
“是吗?”阮维东淡淡地,眸子里的黝暗叫人深不可测,看不出是相信还是不信。
任雪晨凄迷一笑,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如果可以醉掉那便好了,可惜跟着他这么些年,为他挡的酒无数,那酒量也就不知觉间练了出来。
区区一杯,又怎能叫她醉倒。所以,继续给自己倒,也满上他的杯。
若是能将他灌醉也好,可惜,她从来不知他酒量的深浅。
“跟了你这么几年,你的规矩与脾气我还能不了解吗?纵有不甘,想问问她好过自己哪里,凭什么抢走了你,到底是缺了份勇气。我怕一找她,你就会将我碎尸万断了去。”她微吐舌,俏意生花。
阮维东却是视而不见,眸子一冷,“你有这份自知之明最好。”
任雪晨低低地笑了,心有不甘,“倒不知这位安小姐,可让你逗留多久。
阮维东斜眸一睇,冷漠着声音,“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
任雪晨硬了头皮扯着笑,“女人向来虚荣,请原谅我的攀比,我只是在想,她是否会是你下一个三年或者更长的人选。”
男人的脸色,本就冷沉得叫人心悸,这会却是眉角轻扬。
“她将是我的妻子,够了吗?”
阮维东优雅地啜上一口酒,眸角瞟向她时,又是一副一目了然的表情。
一句话,生生地断断了她的念想。那个女人,浑然天成的自信,源于这一句吗?
任雪晨搁在桌底下的手指,紧紧地握成了拳,指甲掐在掌心里,深深地陷进肉里。
怎么可能,那个女人怎么能成为他的妻子,那是她心心相念了多年的位置啊。
为此,她倾尽所能。怎么可以,被人捷足先登了呢?
却是,只能端了酒杯向他举起,想学着那个女人的云淡风轻,却是满脸酸涩,“看来我该道一声恭喜。”
男人端杯把玩,眸里忽现凌厉光芒,“所以,任小姐,最好别让我知道你找过她的麻烦。”
任雪晨心神一悸,惧意顿涌,手指微微抖着,荡出些酒液,落在盘碟里,溅上了桌布。
尴尬地收回,一饮而尽,又低了头轻声道,“怎么会呢,我又不是不知你的习性。”
不敢对视他的眸子,怕被他一眼看穿。男人若无情,原来竟是这般可怖,哪怕她曾经与他同床共枕。
女人如衣的感觉,终于尝到。
却还是鼓了勇气相问,“你爱她吗?”
如果不是爱上,像他这样的不喜束缚的男人,又怎会甘愿附上婚姻。
闭上眼睛,静等他一句答案。
“若不爱,怎会结婚。”
男人的声音,很轻,像和风拂过耳畔,落在耳膜里,却是刺得生疼。
安槿,到底比她幸运,得他垂青。
心里的恨意,浓上几分,却感觉无力。
如果他已沦落于那个女人的柔情,那么,她还有什么机会呢。
安槿原来是个不简单的人呢,轻轻一句话,便叫自己赴入万劫不覆的地狱。
她都不屑参与这场争夺的戏码,看似所有的主动权掌握在阮维东的手里,其实最后的赢家却是她,不费吹灰之力。
不必争,已输。
任雪晨怔怔地坐在那里,看男人从皮夹里掏出几张钞票,搁在桌面上,起身,不看她。
“以后,你就安心在大丰上班吧。”
说完,便离去。一语,将她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