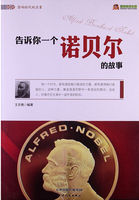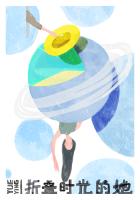她点了一杯冷饮,溜到大厅尽头的门那里,探头去看酒吧里的场景。她看见一个摆满桌子的大厅,尽头有一台点唱机,正在播放里尔乐团的《人生之路》。整家酒吧最奇特的地方在于,这个时段,每张桌子旁只有一位客人,桌上也只有一瓶啤酒。就是那样,每张桌子坐一个人。几乎所有的客人看起来都有一定年纪,或更老些,不是戴着棕榈叶帽就是棒球鸭舌帽,全是一样的棕肤、黑色或是掺杂白色的大胡子,每个人都一语不发地喝着酒,神情专注,彼此间都没有交谈,像是那种沉思中的奇特哲学家。有些啤酒瓶上面还插着餐巾纸,从剩下半瓶酒的瓶口插入,看起来仿佛桌上同时放着白色康乃馨和啤酒。大家都默不做声,只是喝着酒,听着偶尔有人站起来到点唱机投币点播的歌曲。格罗就坐在其中一张桌子旁,飞行员夹克披在肩膀上。他那金色的脑袋一动也不动,独自凝神沉思。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若是他动了一下,也只是为了把餐巾纸从售价七比索的太平洋啤酒瓶里抽出来,然后继续喝酒。里尔乐团的歌曲播完了,换上荷西•阿尔弗雷德的《当这些年随风而逝》。
特蕾莎慢慢离开门口,回到大街上去。在回家的路上,她无法抑止地泪流满面,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为了格罗和她自己,为了那些一去不回的时光。
她有过一夜情,只有两次,都是在她待在梅利利亚的那段时间里。格罗说得有道理,她也没期待过自己有什么大成就。
第一次是受好奇心驱使:她想知道过了那么久之后,会有什么感觉。曾经与自己男人温存的遥远回忆,以及最后一次遭到加多侵犯的痛苦回忆,加多残酷的笑容和粗暴的举止,至今仍深深地烙在脑海里。她小心选择对象,这样就不会有麻烦。对象是个年轻的男孩,一个在国民戏院门口上前和她搭讪的军人。那天她放假,去看了一部罗伯特•德尼罗的电影,内容是描述战争与友情,结局曲折离奇,最后以俄罗斯轮盘来决定命运。她曾经亲眼目睹格罗与他堂弟喝龙舌兰酒喝到烂醉如泥,像蠢蛋般玩起左轮手枪,直到她大声呵斥并抢走他们手中的武器,然后在他们仍嘻嘻哈哈地胡闹时,命令他们上床睡觉。真是两个讨厌而且没有责任感的醉汉。
电影里的俄罗斯轮盘让她想起往事,她难过起来。也许正因为这样,当她走出戏院门口,那个军人一靠过来搭讪—他穿着锡那罗亚州人惯穿的格子衬衫,高大,个性温和,和格罗一样的金发—她便接受邀请到“安东尼”喝杯冷饮,然后听对方聊毫无意义的琐事。最后,他们来到城市的老城墙边,她紧贴着墙壁,光着下身。一只从土坯墙上经过的猫以玩味的眼神盯着他们,眼睛在月光照射下闪闪发亮。她一点感觉也没有,因为她太专注于观察自己,和从前的感觉与经验作比较;忽然间她仿佛又一分为二,另一个就是在对面观看这一幕的猫,如同影子般不动声色。事后男孩还想和她再见面,她说:“当然没问题,亲爱的,改天约出来见面吧。”但是她心里明白,自己再也不会见到这个人了,甚至如果有一天在某处与他偶遇—梅利利亚是个很小的城市—也几乎不会认出他来,更别提记住他的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