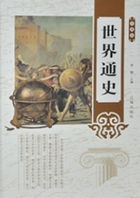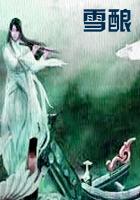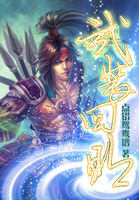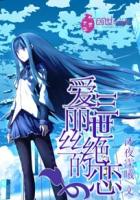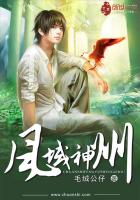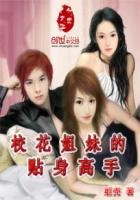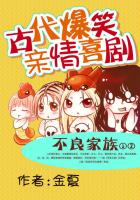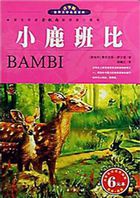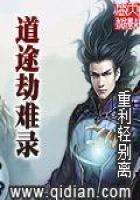第二节 历史评价与实录传统
史料的核实是史家实录的第一步,对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则是史家追求真实的进一步表现。李大钊曾在《史学要论》中说:
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34】
他所谓“解喻”就是史家对过往历史的评论,解喻所能达到的真实程度取决于史家的史识和史观,是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接近真实的。这是李大钊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历史真实和历史评价关系的科学认识。而我们古代的史家在评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时已形成了一些朴素的认识。
“不虚美,不隐恶”,是指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褒善贬恶,都以事实为依据,这是史家所应有的修养。班固此评既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司马迁实录的思想旨趣,也道出了司马迁“实录”与先秦史学“直笔”传统的渊源。
先秦史家已经有“秉笔直书”、“书法不隐”的传统。晋太史董狐因坚持书法不隐,被孔子赞为“古之良史也”。书法是当时史官著史所依循的法则,无隐就是不加隐讳。齐国太史为坚持秉笔直书而不惜生命,南史前仆后继。【35】因此,南朝理论家刘勰在总结史书写作原则时说:“辞宗丘明,直归南董”【36】,即史家直笔而书当以齐太史及董狐为依归。可见,在史学兴起之初,记事不隐的原则就成为史家提倡的一种人格境界,也是良史的一个标准,影响着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在精神上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同时对它又有新的发展。《史记》述秦汉事最详,不仅写出了功臣贤士大夫的事业,也揭露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后来他受到重刑,仍然不忘著述《史记》。他说:“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37】为了写成这部史书就是自己丢了性命,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正是司马迁这种不避强御的正气和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要尽量客观公正地撰写历史、评价历史,形成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特点。但《史记》能成为实录的信史,最重要的还是他不受一般道德褒贬标准的限制去被动地记录史事,而是要自觉地表明自己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态度,使善恶更加鲜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表明自己要以孔子作《春秋》为榜样,用事实说话,不发表空论。即他以保留史事的真相为自己著史的“书法”,从记录史事中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
对司马迁著史的客观态度和《史记》实录的特点,东汉的王充已经给以肯定,他说:“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38】司马迁在《史记》中很少有主观臆断之处,相比于扬雄的好论,司马迁是凭事实表达自己的见解。这是司马迁作为史家区别于文章家的地方。王充还说:“太史公书汉世实事之人”【39】,肯定了司马迁如实记载汉代历史的特点和史学价值。司马迁对秦亡汉兴历史经验的总结,对汉武帝统治时期所面临的新问题的揭示,是通过丰富的历史事件和众多的历史人物活动来展现的,即在如实记录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稽其兴败成坏之理”。这正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的集中体现。王充批评前代学术以疾虚妄、崇真实为最高标准,对前代史书的虚妄失实进行了严格的揭露和批判,对于《史记》,王充也指出其“虚妄”之处,但他却从史家的主观态度和史著的客观真实两方面肯定了司马迁《史记》的实录,使人们对“不虚美,不隐恶”的认识更加清晰,也使后代史家更加推崇《史记》。唐代司马贞为《史记》作注,在《补史记序》中说:“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后之作者咸取则焉。”唐以前《史记》的传播还不广,人们对《史记》的认识还不深,但对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的特点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以之为著史的准则,这表明《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已得到普遍认可。
唐代史家这种认识,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结束,经学对思想界的垄断也被打破,曾一度依附于经学的史学也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出现了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的局面。在这种史风大盛的背景下,《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史学特征得到更多的继承和发扬。当时史臣撰史也以司马迁“实录”为衡量标准。北魏太武帝诏崔浩修国史,令其“务从实录”。东晋时孙盛著《晋阳秋》,也是当时人写当时的史,被称为“辞直而理正”【40】的良史。华峤修成《汉后书》,朝臣“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41】。人们评价陈寿曰:“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辞于东观。自斯以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42】据《晋书》陈寿本传记载,陈寿为人正直,不屈于权贵,他的《三国志》在当时被评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从《三国志》的具体内容来看,陈寿叙事往往能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正是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传统的继承。当时史学评论对这一传统已做到了准确的分析和把握。以文才著称的曹植也说:“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论乎。”【43】他的口气模仿司马迁“继《春秋》”的表白,显然是以司马迁为史家著史的楷模,而“辩得失”、“定仁义”、“成一家之言”就是他所理解的《史记》“实录”所在,表现出对司马迁价值判断标准有较好的理解。
在史学批评领域,实录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评判史家作风的标准,自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观念经历了从个别发展到一般的过程。而这种观念的深入既与史家们追踪司马迁实录的自觉意识分不开,也与史学领域不同史学观念和著史态度的对立斗争紧密关联。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经”,是受到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局限,使人们对《史记》的价值判断标准产生了疑问,以至王允称《史记》为“谤书”。魏明帝与王肃谈到《史记》时也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但这种说法遭到了王肃的断然反对,他指出:“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序事理,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44】王肃认为,汉武帝因《史记》直书而迁怒司马迁,正说明《史记》的直书实录的性质。裴松之注《三国志》,也反对“谤书”说,肯定了司马迁历史评价的客观性,他说:“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世……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45】从裴松之、王肃等人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魏晋人在史学评价上,对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实录精神已渐渐形成普遍的尊崇。这些关于“谤书”的争论是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与现实政治产生矛盾的表现。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这种矛盾愈加尖锐,史家评论也逐渐深入,其标志是:问题提得更加明确,也更带有针对性。魏晋时期,有很多人以批评班固来肯定司马迁的实录态度。如傅玄说:“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救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46】这显然是要与班固批评司马迁的话针锋相对,反过来说,司马迁在价值判断上就没有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堪称良史。张辅也说班固“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47】,不如司马迁。在比较中他们肯定了司马迁的价值判断标准。晋葛洪还试图从马、班思想倾向的不同寻找原因,他说:“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衷。”【48】《史记》的评论以事实为本,褒贬有明确依据,“不雷同于偶俗”就是不同于汉代一般经生儒士的标准。葛洪认为班固从纯儒的角度批评司马迁,与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不合,因此难免偏颇,只有像刘向那样的“通人”才能把握《史记》实录的精神。这样自觉地将马、班进行比较,表现出人们在史学批评上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加强。而这种比较也使《史记》在史学上的地位得以确立,它所具有的“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得到进一步确认,成为良史的一个标准。这为今后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树立了目标。
到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明确提出了“实录无隐”、“按实而书”,“析理居正”和“贵信史”的主张,他所说的信史包含了据事直书和据理直书两方面的内容。不过刘勰所尊的“理”主要还是儒家政治伦理性标准,所以他说司马迁是“爱奇反经”。但刘勰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针对当时史学“腾褒裁贬”、是非无准的具体情况,在圣人之旨外提出了史学新的价值评判标准:“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孔子的尊贤隐讳是圣人之旨,而惩戒的直笔精神也是史家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怎样在这两种标准之间权衡取舍,他只能依凭史家的“素心”,即客观公正的态度。这就为后代史家提出了怎样处理客观事实与史家主体意识的关系问题。
在这种思想线索的指引下,唐宋史家在撰史实践和理论上继续发掘和总结实录精神的内涵,进一步推动了实录传统的形成、发展,有代表性的史家有刘知几、吴缜、郑樵等。
刘知几的《史通》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直书”与“曲笔”的对立。他最强调的优良传统就是“直书”的传统,他提出“史才三长”,于“史识”他特别强调了“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49】以此为标准他赞扬了董狐之书法不隐,马迁之述汉非,称他们“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50】同时,刘知几最反对的就是褒贬任情的曲笔。他指出,自《春秋》的“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以来,形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以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51】他反对为了褒贬而歪曲事实,并指出《春秋》“所未谕者”十二条、“虚美者”五条,以“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的“实录”跟“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52】的偏见相对立。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几在《史通》中特设《申左》篇与《惑经》篇并列,用《左传》的“实录”来批评《春秋》以来的褒贬任情。他说:“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若无左氏立传,其事无由获知。然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两传也,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53】可见,刘知几提倡的是用实录史事来表现善恶真伪的价值判断,有了事实做基础,才有中肯的褒贬。刘知几对《史记》实录的理解与他对《左传》的理解息息相通。在《史通》一书中他多次将司马迁和左丘明相提并论,如《辨职》篇说:“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杂说下》说:“子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然。盖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联系到他在《直书》中所说:“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可见,对《左传》和《史记》实录精神刘知几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史家若做到“不掩恶,不虚美”,在人格修养上可称为君子,撰述成史就可以传之不朽。
刘知几关于直书和曲笔的理论已经涉及到撰史中史家主体意识和客体的关系,他并没有把史家的实录事实与主观评价简单对立起来。一方面,他认识到主观情志和道德观念会影响史事记载的客观性,如他在《疑古》篇中指出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出现这种情况,刘知几认为其根源在于人们“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虽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益亦多矣。”这也是他指责《春秋》拘于礼法,隐讳史实的做法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的原因。因此,他提出史家撰史要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54】的态度。实际上,就是要求史家主体要依据客体进行自觉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要写出信史,还要依靠史家“鉴识”、“探赜”的思想修养,才能做到“铨核得中”【55】。《史通》卷七中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就是刘知几构建的史家主体修养的理论框架。这比刘勰的“素心”要具体得多,表现了刘知几为探讨史学价值判断标准所做的进一步努力。在经学大盛和史书官修的政治、学术背景下,刘知几对曲笔讳饰的揭露和对《春秋》褒贬的质疑,表现了他试图冲破史馆修史和史官制度中的一些限制、使史学能够在宽松的环境中发展的批判精神,是对司马迁以实录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在此精神的影响下,后来史家和史著继续以实录直笔反对曲笔褒贬。《册府元龟·国史部九》有《不实》篇专门列举了史书“不实”的种种表现:
《传》曰“书法不隐”,又曰“不刊之书”。盖圣人垂世立法,惩恶劝善者也。若乃因嫌而沮善,渎货以隐恶,或畏威而曲加文饰,或徇时而蔑纪勋伐,恣笔端而溢美,擅胸臆以厚诬,宜当秽史之名,岂曰传信之实。垂于后世,不其恧欤!
显然,这段话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旨趣,与《史通·曲笔》是一脉相承的,它从大量实例的列举中总结出了种种现象的本质:不实,并把不能传信的史书斥为“秽史”。
宋人吴缜则从理论上提出了史学批评的评价标准:“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56】他认为事实是史书的第一要义,褒贬、文采都以此为基础。他明确地把史学批评的理论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了,这是在史学思想和历史编纂学上明确了“实录”的标准。
宋代史学中有些史家片面强调《春秋》的褒贬之义,理学义理思想的盛行又强化了这种观念,逐渐形成了一股不顾客观事实而空谈褒贬的学风。当时史家撰史,在价值判断标准上往往受主观好恶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出现了“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的混乱局面。郑樵对此进行了批判:
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女不事饔殄,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57】
在这里他彻底否定了褒贬在史书中的价值,认为史家只要写出史事,人物的好坏自然分明,不用再发议论。郑樵把记载国家典章看做撰史的主要任务,而史家对史事的评价似乎用处不大。这涉及到史学中客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也涉及到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在当时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在郑樵心目中,他仍把《史记》、《汉书》的记事写人看做“详文该事”的楷模,说明他是以实录的根本要求,来反对为了维护封建主义统治而专事褒贬的恶劣风气,在当时还是一种进步的史学思想。
唐宋以来,人们对实录评价原则的维护,主要是就史文编撰中具体的史文和记事而言,明代李贽则从历史评价的标准上提出了富有批判精神的认识。他认为汉以来“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58】。这是明确倡导,在历史评价上,史学家应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突破“咸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传统价值评判观念。李贽这个论点是对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的进一步提升,在历史评价的理论发展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在这种进步思想的指导下,李贽反驳了班氏父子对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的评价,他说:“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此迁之史所以为继麟经而作,后有作者,终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笔则笔,削则削,初未尝案古圣人以为是非也。”【59】他认为不管是孔子,还是司马迁都有自己对历史的“是非”标准,只有这样才能言出于吾心,词出于不可遏。这其实可以看做是李贽对史家主体意识独立性的强调。而且李贽还认为迁、固之悬绝,就在于司马迁有旷古只眼的“独见”,而班固只不过是按古圣人是非以为是非的“文儒”。这种认识与李贽进化的历史思想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是有关系的。可以说,正是他与司马迁有这种思想精神上的契合,使他能够更客观地认识史家主体和史学发展的关系。
清代学者钱大昕治史以“实事求是”为旗帜,他对实录之书的认识告诉我们:实录的撰史方法,是贯穿在史料安排、编纂体例和历史评价中的,是统一在一起的。钱大昕说:“史家记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各若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60】他批评那些死守《春秋》“一字褒贬”的做法,认为用这样的方法治史,就失去了据事直书的根本原则,只能是愈弄愈乱。他在这里用《史记》的“不虚美,不隐恶”反对“掉弄一两字以褒贬”的史学方法,还把班固和司马迁的撰史方法相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班氏降陈胜、项羽为传,有意抑项,较史公直笔,则去远矣。”这是从史料安排和编纂体例上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从唐代后期人们过分强调《春秋》褒贬的风气到清代史家和学者彻底否定《春秋》褒贬,学术史的发展表明,司马迁《史记》的实录精神是史家主体意识和客观事实的统一体,代表了先进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这也说明人们已经在史料真实和历史评价的客观性上建立起了统一的、实录的标准。
可以说,由于史学与现实政治的复杂关系,以及儒家经学思想的影响,政治伦理性的价值评判标准,从中国史学产生后就一直存在着,使史学发展的道路艰难而曲折。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标准就成为后代史家的旗帜,用来反对史学批评和历史撰述中存在的专事褒贬之风,逐步确立了史学实录的价值评判标准。可以看到,随着矛盾的激化,正直的史家不再停留于批评曲笔的表面现象,而是要从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上加以批判。在此过程中,以《史记》实录为评价标准的思想始终占据着主流,使人们对史学固有性质的认识更加清楚,坚持了史学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无疑是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在史学发展中所起到的、最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