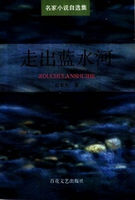我知道上海是怎么回事。我从小就知道。上地理课的时候,老师用竹鞭指着中国地图东边的一个缺口说:这是上海。她的竹鞭顶着四周环水的地方,我问弄丢了那块是怎么回事,她说那是岛,崇明岛。那次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上海把崇明岛扔到河中间去了。
我没想到我在高中毕业之后的岁月里来到了上海。这是历史专门安排的。历史老人调遣了几百万像我一样的外地人来到这里找饭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成了碗厂,做了许多饭碗等着我们去端。我以前在四川的饭碗让一个娇滴滴的川妹子给我抢走了。这年头漂亮女孩子的碗总是又好又大。有她的就没我的。人多碗少。我只有来到上海。我爹把我送上火车时,重重地拍了一把我那有骨无肉的屁股说:龟儿子,好歹也是读了几天书的,在外面好好混去!我爹的话随着那个巴掌贴在我的屁股上了。从成都到上海后,我一直觉得屁股上张了个东西。父亲的谆谆教诲撑起了我外形的圆润。
我知道我是不配到人才市场去的。我有这个自知之明。毕业证是越大越管用,我没有像别人那种大红本本。可这不是丢人的事。蛇有蛇路,鳖有鳖路。我在职业介绍所门前晃荡的时候,就让一位女孩看上了我。她问我会干什么,我说我会做几个川菜,酸菜鱼烧得不错,还会使用四川那种长嘴茶壶。她两片粘连的口红就那么裂开了,说:行,看你还老实,跟我走吧。
我就跟着这位红口红裙子的女孩走了。我尾随在她屁股后面有点兴奋。职业介绍所门前众多的目光都贴在我的衣服上。我知道他们羡慕我。不仅叫人领走了,还是个女的。
她叫王瑛。我叫她王小姐。长相与身高都是一个典型的小女人。就是这个小女人给了我一只在上海的饭碗。我的饭碗在她手上翻云覆雨,折腾出许多花样来。
她把我领到东方路一家叫风满楼的餐馆停下来,我以为她是领我来吃饭的。那时候我真的有点饿。她在门前驻足几秒钟便进去了。通亮的蓝色玻璃门,门面不大但却看得出来里面很豪华。我不敢进去。我害怕这种华丽的地方。觉得自己像垃圾似的。其实上海像这样的门很多很多,但很多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进去。蓝色玻璃映着我紧张而又兴奋的脸。我不知道我怎么居然留意起自己来了。王小姐进去约三分钟后,拉开玻璃就把脸挤出了门外,说:进来呀,你愣在那里干什么?
我眨了一下眼,说:小姐,我不吃饭。谁让你吃饭了?叫你在这里来工作!王小姐一笑,我发现她笑起来真好看,还有酒窝。我噢了一声便进去了。我迈进门时她在我背上推了一下。我的心里因为“工作”两个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甜蜜和幸福。它比“打工”给人的感觉要好些。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说工作而不说打工。我想她上学时一定学过遣词造句,不然一说话怎么就惹人喜欢。
屋里并不像外面那样不显眼。里面的空间很大。摆了两排大圆桌,一共八张。从墙角的台阶拾级而上,便到了二楼,是雅座、收银台和一个可歌而不可舞的卡拉ok 厅,小而精致。我看着这些东西就觉得舒服。
王小姐拍拍凳子,示意我在雅座上坐下来。我坐了。我们面对面。小姐说:小四川,你从现在起就在这里工作。主要是后勤服务,扫地,擦灰,倒茶。扫地擦灰是晚上早上干的事,客人来了,就是倒茶。她用纤细手扯起我衬衣的一角,说:你的工作非常重要,你就是门面,是窗口,要干净卫生体面,不能脏兮兮的。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每个月给你四百块钱,管吃,管住。你有意见没?我没意见。
王小姐起身走到收银台那地方,取出一套青色衣服,说:小四川,你过来!我过去了。
把这套衣服换上,这是工作服,上班穿的。王小姐把衣服递给了我,同时把目光也递给了我。我看见了她眸子里的我有些发虚。我按照她指定的位置,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把衣服换了。这套青色衣服真合体,好像是为我度身定做的,只是那顶绿帽子我不喜欢。绿帽子上镶着红边,总觉得有些不顺眼。大裤子和长袖青衣虽然很合体,可也有些滑稽,像是舞台上的某个角色。我走出去之后,王小姐说,不错嘛,还真像那么回事。
衣服一换,我就成了这里的工作人员了。我知道这个时候的表现是最重要的。我开始学着另外一个女孩子的样子从事沏茶和收拾残汤剩水的工作。沏茶是那种小盖碗茶。古时候文人雅士喝的那种。但真正的茶叶并不多,里面有苹果片、生姜片、红枣、冰糖和枸杞。长嘴茶壶不是我的专业,但我学过。成都那些茶馆就有这种东西。我同学的爹就开了一个茶馆,没客的时候我们就在里面洒冷水闹着玩,莫名其妙地就学会了一门手艺。那时就没想到玩也能玩出这路好处来,居然能在大都市里派上用场。有的读四年本科也找不到职业。比起他们我就幸运多了。我提起长嘴茶壶就得心应手。为了稳妥起见,我在桌上放了个小杯,我站在一米开外的地方往里倒茶。壶停杯满,滴水不漏。看来我技巧还在,基本功还在。王小姐见我出手不凡,连连夸耀说:不错,你真有两下子。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她成了第一个在上海夸耀我的人。
收银台旁边那个穿红工作服,也是戴着绿帽子的女孩子笑眯眯地望着我。我看得出来她跟我是同等身份的人。可我就不明白她的头发为什么染得发黄。我不大喜欢头发发黄的中国女人,给人一种异族的感觉。但她的样子并不叫人讨厌,属于平易近人的那种长相。这种相貌决定了我们以后的来往。
来了一个高个子的黄脸男人。后面还松松垮垮地跟了几个男人。好像是来吃饭的。他们非常熟悉地坐在雅座的位置上。黄脸男人对王小姐说:人找到了?王小姐迎过去,笑盈盈地说:找来了。黄脸男人问:怎么样?王小姐说:刚来,模样还行。王小姐向我招招手:小四川,过来一下!
我过去了。我提着长嘴茶壶。我像他们新买的宠物一样,让黄脸男人把我周身打量了个遍。过目之后,他说:小四川,好好干。干好了要加薪的。王小姐问我,听见了吗?我说听见了。
黄头发女孩子放好茶杯以后,就轮到我表演了。我的长嘴茶壶灌了大半壶滚开的水。我站在圆桌的外围向茶杯注水。我的手稍稍一顿,就飞出一股白色抛物线,稳准狠地冲得杯中浪花翻滚。这个不经意间的动作赢得了黄脸男人的喝彩。他说不错。他说不错,我想肯定就是不错的。能上雅座的人说话都不一般。
黄脸男人他们吃了一些酒,之后就长一声短一声地怪唱。他们吃得少唱得多。他们唱得比狗屎还臭。我在他们伸长脖子的时候就想到了鬼哭狼嚎。这之间我吃了一顿饭,甜不拉叽的,吃得我想吐。我自己添了一些辣椒,好不容易才把它咽下去。
王小姐一晃就不见了。她到楼下张罗去了。我不知道谁是老板,是王小姐还是黄脸男人?他们玩得很久。天擦黑我就想到睡觉的问题。我怕他们只顾自得其乐而忽视了我。晚上十一点了,黄脸男人才把我领到一个拐弯抹角的去处,是一个又破又烂的小房。里面就只有一张床和一些脏兮兮的被褥。黄脸男人很大方地把钥匙递给我,说:这里就归你住了。这像狗窝,你自己好好收拾一下。
我说:怎么这么烂呢?
黄脸男人说:陆家嘴的写字楼不错,你配吗?有个地方能放下你身子就行了,你又不办公!他说毕就走了,把惊叹号丢在了门口。我看着外面的夜光,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寒噤。
黄脸男人姓苏,叫苏老板。是从宁波过来的包工头。这是黄头发的小丫子告诉我的。小丫子在风满楼干了一年多了,知道这里一些重要人物的来龙去脉。她告诉我,解放前上海就有宁波帮,宁波人做生意是在全国出了名的,是出现大款最多的地方。我知道宁波的名气是很响的,清朝政府曾经把它割让出去做外国人的通商口岸,这一割让影响就大了。我们的老师都知道它的底细。正因为苏老板是宁波人,虽然我不喜欢他,但也叫我刮目相看。
我问风满楼的老板是谁,小丫子说她也搞不清。平时管事的是王小姐.。王小姐是西安去的,长安县人。有个叔叔在上海当小官,她就到上海打工。几年下来就打出了名堂。小丫子在说这些话时,充满了对王小姐的羡慕。她说当老板真好,愤怒了可以发火,打人骂人;高兴了就唱歌,手舞足蹈。那该多自由!打工就不行。什么怨气都得忍着。
我问:她敢打人骂人?
小丫子说:其实王小姐是个口恶心善的女人,她骂人是常事,她巴掌细嫩,打人也打不痛的,她火一出,什么都没了。不记恨人。
用不着小丫子介绍,我就知道王小姐是个好人。聪明人一眼就能看出人的好歹来的。话说回来,十几个人的餐馆,要管事,不厉害点怎么行?老板不像老板的样子就没王法了。没了王法就会乱套。
小丫子说:要是你当了老板,肯定厉害。
我说:我这一辈子就不会当老板。只会用长嘴茶壶。小丫子就笑。笑声像铜铃在红衣衫上活蹦乱跳。我看她笑得真有点可爱。我到风满楼的头几天表现还是不错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王小姐每次看我倒茶的样子就情不自禁地发出会意的笑。我看得出来那是她对我表示满意的表现。她当然不能太多地夸我。夸奖使人骄傲,骄傲使人落后。我开始摸出了老板的一点心态。我之所以表现得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很大程度上是初来乍到的缘故。我不敢贪玩的,上海有许多好玩好看的地方,我多么想去,但我都克制了。端着别人的饭碗,受着别人的管,图个优良表现是顶要紧的事情。
我正在谨小慎微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错误正在等着我。那个错误等在情理之中,又出现在预料之外。错误蹲在二楼雅座那个玻璃门的门口。
那个白色透明的玻璃门是一张完整的厚玻璃做成的。四周镶着铝合金。由于每天都把它擦得太干净,一尘不染,几乎就没有了那种门的感觉。原本是一个阻隔的空间,因为玻璃的透明便常常忽视了阻隔的存在。那天是合当有事,苏老板他们几个人来得匆忙,说是吃了饭要去办什么事。小丫子七脚八手把茶碟放好,我就提起长嘴茶壶往里走。我没想到那里有门,更没想到门是关着的,一不小心就撞到了玻璃上。首当其冲的不是我,而是仙鹤细颈一般的长嘴茶壶。随着啪的一声,长嘴一下子折成了两折,出水口卑躬屈膝地弯在了壶体上部。整个过程自然流畅,坚强果断,体现了水到渠成的效果。
穿着高跟鞋的王小姐雄赳赳地走过来,揪住我的耳朵就往外拉。我的耳朵像橡皮一样变了形,火辣辣地痛。她把我揪到墙角放开水桶的地方才松开,松开之前还把我使劲拧了一下。然后虎视眈眈地望着我说:你慌什么慌,鬼追了你是不是?
我怯生生地望着她。我说:客人来了,我一高兴,就不小心……你以前见过玻璃没有?
见过。知道玻璃是透明的吗?知道。
光知道不行。你要记住:玻璃是透明的。记住了,玻璃是透明的。
王小姐笑了笑,用细嫩的手摸了摸我发烧的耳朵。她笑我,是笑我的可怜相。她摸我,是为了安慰我。有她这么一摸,我便突然不恨她了。这个女人真是会教育人的。我在等待进一步发落的时候,她却转身走了。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我手上依然提着那只折了嘴的茶壶。
小丫子在收银台前咯咯地笑。起先她捂着嘴。王小姐走后,她嘴也不捂了,敞着嘴笑,她指了指餐具室说:还有一个好的,快去换了!
我连忙到餐具室换了一个好的。我心旌摇摇,也许是太慌了,我提着空壶就直奔雅座,直走到那该死的玻璃门前,我才想到茶壶是空的。里面的苏老板正对着门,他的眼睛和目光都像涂了口红一样,叫我望而生畏。我丧了胆似的连忙转身回来,灌了开水又往雅座跑。我卷起来的衣袖因为匆忙而全部垮下来,掩住了半边手背。头上的绿帽子也不明不白地歪了。我一走到玻璃门前就提醒自己:玻璃是透明的。借助玻璃映出的模糊的影子,我正了正衣冠,小心翼翼地拉开门,如履薄冰地走了进去。在我给茶碟注水时,苏老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直到顺利地把茶倒毕,我才松了口气。
我没有忘记弥补我的过失,一个人不怕犯错误,就怕不改正错误。以前老师就一直用这种领袖的口气给我们讲。苏老板他们一走,我就连忙进去打扫。我看见桌上的鱼骨鸡骨上残留着许多肉,我觉得真是可惜。到底是有钱人,他们用不着在骨头上下工夫去啃。除了一碗鳖汤所剩无几外,其他的许多菜都残留着。要是旧社会,也够翻身之前的农民吃几顿油水的。我把这些东西看了又看,真舍不得倒它,要不是外面有人盯着,我就要把它吃了。但我还是咬紧牙关倒进了桶里。然后把盘碟收拾起来,把桌子擦得油光锃亮。我在提着半桶残汤剩饭走出雅座时,突然想到酒店里喂头猪多好。正好可以把这些利用起来。王小姐眼睛很尖,见我在纳闷,就走过来,问我想什么,我说:我想喂猪。
王小姐哈哈大笑了。她几乎是笑弯了腰。笑毕了,站起来擦着笑泪说:你想喂猪?
我想喂猪。我说。这些东西倒了多可惜。王小姐抖抖裙子,笑着走过去对小丫子说:他想喂猪。小四川想喂猪!小丫子也咧嘴一笑。望着我说:看你那么瘦,先把自己喂肥点,喂什么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