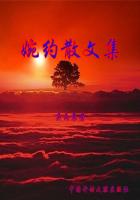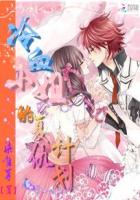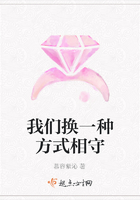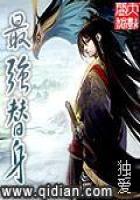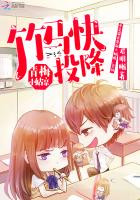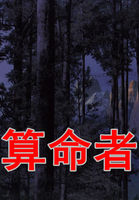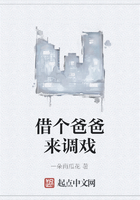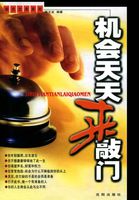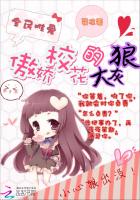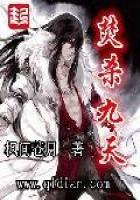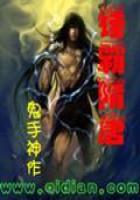袁琳有点不解,她说,那时候就没有人同情你们的遭遇吗?不会是所有人都那么恶毒吧。我说,或许有,可能我没感觉到吧。但有一个人对我的同情我真切地感觉到了。她就是我的数学老师刘老师,名字叫刘敏。她是一个刚结婚不久的漂亮少妇,丈夫是军人,她原来在城里的初中做老师,后来随下放的父亲来到我们乡里做小学教师。我第一次与那个朝我脸上吐唾沫的学生大打出手被带到办公室的时候,几个男老师轮流过来弹着我的脑壳骂我恶毒,只有刘老师没有说什么。后来她给我倒了一杯水递给我,说,喝了吧。
然后叹了一口气,说,这孩子也够可怜的……我大口喝水的时候眼圈发热,几乎哭出来。对于别的老师的责骂我毫无感觉,一句温暖心窝子的话却差点把我的眼泪挤出来。我当时心里暖暖的。后来我长到粗通男女之事的年龄之后,多次没心没肺地想,要是刘老师离了婚多好,最好也曾经被别人打成“狗崽子”,那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不管她比我大多少岁,我都愿意娶她和保护她。正是因此,我才一度迷恋她,甚至要求她向我敞开心怀。那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比我大十几岁的刘老师被我的举动惊呆了,我一边燃烧一边绝望,渴望用自己的近乎野蛮的拥抱拉近与她的距离,我感觉到了来自她内心深处的战栗和挣扎……
那已经是后话了。
我在学校挥舞链子锁的时候,哥哥已经在矿山机械厂上班了。他初中毕业的时候十五岁,在父亲还没有被赶回农村的那年就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扔掉书包就跑到了远离市区几百里外的一个山村做下乡知青,直到“文革”结束后矿山机械厂招工,父亲找了关系把他弄回来进厂做了工人。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比我大十三岁的哥哥很高大很强壮,但今天看来,他其实只有一米七二,比我矮了九公分,实在不算高大强壮。再看他那张做知青时光着脊梁与同学们在田间劳动的照片,就发现他瘦得像麻杆,模糊不清的照片上却能清晰地看到他一根根凸起的肋骨。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只有四十岁,但他却像老头子一样驼了背,扛着锄头到田间劳作的时候脚步踉跄。我甚至担心他是否能继续承受生活的重压。我总是给他惹麻烦,校长不厌其烦地把他一次次叫到学校,当着我的面控诉我的罪行,父亲除了鸡啄米一样点着头唯唯诺诺别无他法。当时我们刚学了一篇鲁迅的文章《少年闰土》,我发现他确乎已经是那个像木头一样的中年闰土了。
母亲同样身体孱弱,但也不得不参加生产队的各种沉重的田间劳动。在父亲到外县参加修筑大坝的集体“大会战”的时候,母亲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点着油灯纳鞋底,后半夜她熄灯躺下了,但我仍然时不时会被她的叹息声和压抑着的抽泣声惊醒。我知道她在担心我父亲的身体,父亲早年得过肺结核,治好后就干不动重活了,但修大坝是重体力活,利用原始的木制推车搬运沉重的泥土和砖石,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父亲不累到吐血就算上天保佑了。那种数千人一起夜以继日地战天斗地的宏大场面恐怕现在很难再见到了。
在揪心的牵挂和惊恐里过了两个月之后,父亲终于回来了,他的头发像乱草,胡子拉碴,面孔黢黑,耳朵和眼窝沾满灰尘,老旧的灰色中山装包裹着的身体瘦得脱了形……我们几乎认不出他了,好在他还能活着回来,而且从麻布袋子里拿出十几个像石头一样硬的黑乎乎的黍子面馒头,这是他从每日定量的伙食里省下来的。母亲看着我父亲满脸欣慰地低着头从口袋里往外一个个掏那些黑馒头的时候,再也忍不住了,搂住父亲肮脏的身子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骂:你个死鬼,一走就是俩月,纯粹想折磨死我们娘俩啊……父亲揉搓了一下浑浊的眼睛,抽了两下鼻子,腼腆地念叨着说,守着孩子,别这么搂搂抱抱的,我这不是活着回来了嘛!
当时的我一句话也不说,说实话,我那时很看不起他们俩拉拉扯扯的样子,但我又着实想不出他们应该怎么做才更合理一些。那时的我还太小,总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老是怯懦地对待所有铺天盖地倾轧过来厄运。我很早就听说过这样一句俗语:树挪死,人挪活。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去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生活?不认识我们当然也就不会知道我爷爷是地主,不知道我们的地主出身也就不会对我们另眼相看。我其实从骨子里羡慕那些贫农阶级的子弟,我没有朋友,来去都是孤零零的,而他们则拉帮结派,呼朋唤友。他们在学校里填表的时候可以趾高气扬地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大模大样地填上“贫农”,而我则要屈辱地像堆砌坟墓一样艰难地歪歪扭扭地写上“地主”两个字。那时我的耳朵和眼睛都极其敏感,任何一声“嗤嗤”的窃笑和一个不屑的充满优越感的眼神都会深深刺伤我的自尊心,把我的心情搞得灰不溜秋,我心底懊恼万分,但又不知道该怨恨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