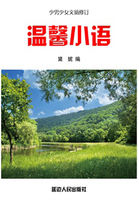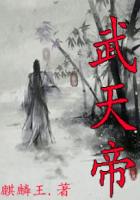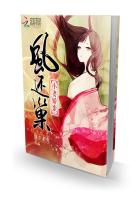二 苏联文艺理论影响下的《文学读本》及其续编
抗日战争中,王任叔在上海租界坚持文艺斗争,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重新评价的。孤岛时期,王任叔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方面走向了成熟,这与他此前经过左联的锻炼,在政治上已趋成熟有关。特别是他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用以指导自己的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这是其文学观念走向成熟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同志自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至1942年《讲话》以前发表的政治论著,如《五四运动》(1939年5月)、《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给了王任叔结合文艺运动实际进行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的思想钥匙。他此时关于“大众文学”、“民族形式”、“遗产的批判继承”的认识,在总体上是正确的,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发展和完善有一定的思想贡献。
除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之外,苏联文艺理论的深刻影响也是王任叔能够在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重要原因。孤岛时期,王任叔出版的重要论著主要有以下几部:《文艺短论》,1939年由上海珠林书店出版;《论鲁迅的杂文》,1940年由上海远东书店出版;《文学读本》和《文学读本续编》,分别于1940年5月和11月由上海珠林书店出版。其中《文艺短论》是他1936年出版的《常识以下》的再版,《论鲁迅的杂文》属于文学批评著作,只有《文学读本》及其续编作为专门的理论著作,是王任叔文艺观念的集中展示,也是他此时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而这两部理论著作的写作又受到了苏联文学理论的深刻影响。王任叔在《文学初步续编》后记中曾有过这样的表白:“全书的纲要,大致取之于苏联维诺格拉多的《新文学教程》。因为在他提出的各项问题,确是最基本的问题。然而我或者把它扩大,或者把它缩小,而充实以‘中国的’内容。”这说明王任叔在基本的理论框架上接受了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
应该特别指出,《文学读本》及其续编是我国第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比较系统地研究和阐述文学问题的理论专著,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应该有其重要的位置。虽然他受到苏联文艺理论的重要影响,但我们仍应该承认王任叔在接受苏联文艺理论时的创造性劳动,即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的“中国化”改造。
具体到书中的具体内容来看,通读全部著作,不仅满眼是这样的章节:“中国文学观念史的发展”;“鲁迅是怎样描写人物的”;“中国文学的流派”;“中国文学的种类”;“民族形式的检讨”;“新文学的诸问题”;“抗战文艺理论的清算”;“新民主主义文学的特质”,而且在一些文学基本问题的章节里,也以中国文学论点和中国文学作品为主要例证。这确是一部显示作者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融会贯通到中国文学里来的有分量有质量的文学理论著作。特别因为它写成和出版于上海“孤岛”时期那么一种艰苦的环境中,更使我们对作者这种大无畏的坚持真理的精神发出由衷的钦敬。
认真阅读《文学读本》及其续编,可以发现它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中,有如下一些理论努力应该给以关注。
1.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作者在《后记》里说:“写这一书时,我就有一个企图:既要比较广泛的涉及于文学上的诸问题;又要把我认为比较正确的文艺理论,组织在中国文学的作品分析与叙述上,而归结于中国气派中国作风文学创造的提示。”这里所谓“比较正确的文艺理论”,是在当时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比较隐晦的提法。通观全书,我们的确看到作者在这一方面的一以贯之的努力。他不仅大量引证了鲁迅、高尔基、茅盾、郭沫若、A·托尔斯泰、法捷耶夫、普列汉诺夫、米丁、藏原惟人等人的有关论述,而且有的地方直接引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序言》,以及恩格斯的关于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论述。特别难能可贵的是,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他“从领导同志中首先看到其断片的收录”(1949年《再版后记》)以后,立刻在《读本续编》里大量加以引用和阐述。在第五篇第一节阐述新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风格问题时,引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切实地否定了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不得不走上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论断。在第七篇第一节《新文学的产生的原因》里,大段地引用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划分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论述。在同篇第三节《抗战文艺理论的清算》里,阐述了中国革命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理论。在第四节《新民主主义文学的特质》里,则又引述了关于中国革命政权形式的论述。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王任叔在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下,综合中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建构我国马克思文艺理论体系的努力。在具体分析论述上,王任叔也是积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有些看法虽然可以看出明显的时代局限,但那种理论研究的勇气和开拓精神是让人敬仰的。
比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在这篇著作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作者运用此观点进行文艺研究的努力。他不仅始终把我国文学的发展同阶级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观察,而且对引证的每一个文学作品、每一个文艺论点,都试图从阶级意识方面加以分析,哪个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哪个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哪个属于封建阶级的思想,哪个属于“农民的自然发生的现实主义文学”,都一一加以标出。典型的例子如在第五篇第一节《文学的风格》里,他引用了《诗经·国风》里的《将仲子》一首诗:“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书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作者在分析这首诗所刻画的少女虽然贪恋情人,但又畏人言的矛盾心情后指出:这是“由于封建社会的建立,男女的原始性的恋爱已被禁止了。礼教男女的防范渐渐确立起来了”。这种分析虽然不免机械生硬,比较简单,也不尽恰切,但任何初创的东西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可贵的是这种披荆斩棘的开创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观点是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王任叔在本书里也坚持了这个观点。例如在考察中国文学民族的形式时,他把它分为四个阶段:A、初期封建社会的文学形式(西周—春秋、战国);B、专制封建政治的确立与衰落时期的文学形式(秦汉—两晋、南北朝);C、地主阶级经济复兴期及衰落时期的文学形式(唐—元);D、专制封建制崩溃时期的文学形式(明—清)。又如在考察新文学的发展阶段时,他大胆地把它划分成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五四新文化的特质是“民主”与“科学”??
第二阶段——1927年大革命以后的文化的特质是“阶级论”和“唯物论”??
第三阶段——自“一二·九”而来??它完成了将要完成第一阶段的否定之否定之任务,它保留第一阶段“民主的”特质,然而否定了它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以阶级论贯彻它,成为“大众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部分。它又否定第二阶段,那种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论性质。它保留了第一阶段的科学的特质,然而它否定了科学之形式逻辑之思维法则,和科学生产技术的资产阶级专有的意义,而充实以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法则和科学生产技术之国家管理形式,而造成民族之大众的幸福的社会基础。但它又否定了第二阶段唯物论之非中国化的适用,那种生吞活剥的搬运方式。
这里我们看到的,既是原则上依据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又大量加入了他自己的考察观点。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估计客观上是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很可能王任叔还没有正式看到《新民主主义论》的全文,正如他后来自己说的:仅仅“从领导同志中首先看到其断片的收录”;主观上也反映了当时的党员学者在研究问题上是毫无思想顾虑的,敢于根据客观历史事实,独立大胆地做出自己认为是科学的结论。作者在《后记》里说:“这书如其有可取的地方:那就是我的立论,是大胆的。不管自己意见成熟不成熟,拿出去供别人讨论,也还有益的吧。”对这种治学态度,可能见仁见智,有人未必同意。然而,从上面的引证中,我们也可看到:王任叔的“大胆”并非信口开河,哗众取宠,不过是把他学到的毛泽东思想,努力融会到他体会到的客观现实中去,这样的治学态度不能认为不是严谨的;而在学术空气上,则是一派朝气,生机勃勃。
2.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启发式的论辩
王任叔是有丰富创作经验和阅读、批评经验的文学理论家,他的《文学读本》和续编中处处迸发着独到的见解,不落窠臼。原因就在于他不是先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观点来生套客观现实,削客观现实之足,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导的履,而是首先从总结客观现实着手,由此验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正确,从而尽可能地丰富它,发展它。在《怎样写一个人物》的章节里,他把描写人物性格归纳为五种方式;又把描写人的形象归纳为“间接的形容”——“中国旧小说多用这种方法”和“直接的形容”两种,而在直接形容里,又分为“静态的写法”和“动态的写法”两种。对创作和描写上的“类型化”(即今天所讲的“公式化概念化”),他指出问题所在是:“人物不是生活的人物,而仅是某一种道德的象征,抽象概念的堆积。‘他’仅具有某一社会群的一般的东西,而没有特征的东西。或者是‘他’仅作为一个‘他’存在,而‘他’不活在他所居住的社会里似的。”在《文字的风格》一节里,他分析常见戏剧性的各种表现,有四种样式:“一种是‘化妆演讲’的样式??一种是‘双簧’的样式,表现和说唱者是分离的。??一种是‘舞蹈’的样式。??一种是戏剧本身。”在《中国文学的流派》的章节里,他把中国古典文学总结为五种派别。在《民族形式的探讨》一节里,他又把中国文学民族形式的发展总结为五个特点。??类此种种,都表现了作者是把客观存在的历史现实放在第一位,努力从客观历史现实中总结出规律性的理论的东西。这种精神无疑是科学客观的研究精神。即使在今天,这种科学的文艺理论研究精神都是应该继续肯定和提倡的。
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和错误的东西不断地作对照、作斗争的过程中被确认和发展的。这部著作的另一特色就是:作者在把每一个自认为是正确的论点交给读者之前,并不回避提出不正确的论点,相反是先把形形色色的不同观点都提出来,启发读者自己去思考。这种先进的对话意识也是应该肯定的。这方面的例子在书中举不胜举,几乎每一章节都用的是这样的方式。比如第二篇第二节,《艺术是起源于游戏吗》,他首先引用了“游戏”说的朱光潜的观点,又引了相同观点的席勒的论述,然后引用了不同意这一观点的普列汉诺夫的论点??然后在对照和分析不同观点的进程中,引出必然的同时也是作者自己的观点。再如第二篇第一节,关于什么是文学的定义,他也首先把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不同界说统统摊开来,问:“在这样众多的界说中,我们将何去何从呢?”当读者开始思索的时候,他便一个个地分析产生这种不同的关于文学的界说的历史背景和阶级根源??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以理服人。
著作中还有一个特色,即:针对论点,不针对人;对一个人的许多论点,也不是“褒则全褒,贬则全贬”。第六篇第一节,在谈到诗的特征的时候,他举了两个相反的例子,第一个是朱维基的诗《我们不要忍耐》,肯定了诗人的抒写和悲愤之情,但同时指出,这首诗“作为诗的表现上,是超过了作为诗的语言的几何学限度”,因为朗诵者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一口气诵出五十几个字的一句诗句来的。第二个是徐志摩的诗《一条金色的光痕》,指出这诗“充满了虚伪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但同时又说,这诗“捉住了语言之自然音律,全都适如语言之几何学限度,而诗的篇幅的长短,也适如其情绪的起落”,内容虽然不好,艺术可以借鉴。在不因人害意的问题上,著作在个别地方甚至引用了周作人和胡适五四时期的某些论点,指出“值得我们注意”。此书编写时,周作人的“落水”已明,胡适则老早在蒋家王朝里“高升”了,王任叔如此引用,在极“左”的人的眼里,一定是“与敌人勾结”的“反革命”行动无疑了。然而这里正可看出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
3.尽可能做到了通俗
王任叔在《后记》里曾有这么一段话:“写作时,有一个别扭,闹得凶:想尽量写得通俗一点,但有时简直无法通俗。于是写下又改,改下又写;把句子倒装、顺装,简直在练习作文了。”的确,一本理论性的著作,特别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初创时期的理论著作,要写得通俗是极不容易的——外来的理论和异质的文学现实要做到恰切的结合比较困难。
但从《文学读本》和续编中,我们感到了尽最大限度的通俗。在第一篇第一节的《谁唱出第一个的歌》里,他首先拿鲁迅写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引出“‘第一个’总是可敬的”,于是引出“这世界是谁第一个创造的”的问题,把读者引向主动要求研究的轨道。在第二篇第一节《文学与定义》里,他从“瞎子摸象”的故事谈到“定义不容易下”,再引出古今中外曾给文学下过的种种不同的定义。在第四篇第七节《故事与结构》里,他从一句俗话“世界如舞台,而人生如戏剧”引向“有些理论家说,艺术家是个谎言大家”,由此引出关于戏剧和生活现实的关系的申述,都起到了启发和引导读者的作用。在第三篇第三节《典型性》里,在谈到恩格斯对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的论述的时候,他用了讲故事的形式来开头:“从前英国有个女作家赫克奈斯,写了一册小说,叫做《城市姑娘》,寄给昂格斯(恩格斯)去看,请他批评。”但特别多的是他在说清一个概念或论点的时候,引用大量的人们所熟悉的作家作品,又解说,又分析,务求读者真正能学懂学通。文学理论著作写作时的通俗化问题,至今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王任叔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文学读本》及其续编问世以后,在文学界和读者中,特别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颇为强烈的反响。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反响绝不是偶然的。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著作,王任叔积极接受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尝试,这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有其特殊的价值。
1941年3月,《文学读本续编》出版不久,王任叔离开“孤岛”去了南洋。1947年10月,他从苏门答腊回到香港,海燕书店向他建议把这本书再版。1950年1月,经作者小作修改,改名《文学初步》,由海燕书店在北京先后出了三版;1951年7月至1952年6月,又由新文艺出版社先后出了三版。然后,经作者作了一次大幅度的修改,再改名《文学论稿》继续出版,直到1954年6月,又出了修订本版。至此,王任叔的这部著作才完成了他的理论使命。但《文学读本》在开创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基地上的功绩是不会磨灭的,我们应该承认它的开拓之功,并总结其接受外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进行“中国化”转化的早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