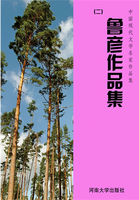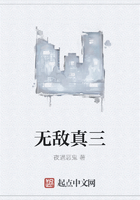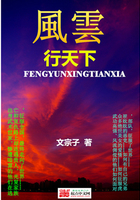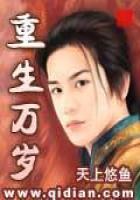王元骧先生(1934—),原名麟祥(亦写作林祥),浙江玉环人,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研究者。作为高校中的学者,王先生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除了为期刊的约稿和相关学术会议的既定命题而展开之外,主要是为了服务教学而进行的。然而,正如王先生自己也多次指出的,他的学术研究虽然有浓厚的学院气息,但大多是针对社会现实向理论提出的具体问题的,并非脱离社会现实的纯理论思辨。所以,既积极关注现实,又讲究学理的严谨就成了王先生文艺理论、美学研究的总体特色。
王元骧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研究文学形象,特别是文学典型开始,踏上了自己的科研探索之路。对自己在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对文学形象相关问题的研究,他因“文革”的影响以及当时学养的欠缺,不是特别满意。但他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成绩其实非常不错。童庆炳先生在谈到新时期三十年以来的文艺理论研究成绩时,曾批评“许多文学理论的基础性问题我们都是浅尝辄止,没有拿出像样的东西来”,而对王先生的典型和典型化问题研究他给予了肯定。他说:“在我们的有限阅读中,只有一个典型和典型化问题这一论题,由于王元骧教授在80年代的《文学评论》上面发表了长文,把典型与典型化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比较清楚,可以说解决了一个问题。”【1】童先生对新时期三十年文艺理论研究的批评过于严厉了些,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他都根本没有提及,这说明这一评价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其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但他对王先生的典型问题研究的肯定,清楚地彰显了王先生当时学术研究的成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是王元骧先生自己认可的学术开端期。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评价自己的学术研究时曾说,80年代中期以来自己发表的一些文章“才是真正具有我自己的个性和特色的东西,是我这些不成熟的东西中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篇什”【2】。自那时迄今,在近三十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王元骧先生一直坚持着具有自己个性的学术研究道路,以极其严肃的学术虔诚面对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认真地思索时代现实向理论提出的各种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受社会现实的影响,文艺领域的急遽变化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文革”结束以后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摆脱了极“左”政治的重负,文艺领域曾出现过短暂繁荣,不同的文艺观念同时并存,各类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人眼花缭乱。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迅速繁荣起来,这使拜金主义开始流行,人文精神走向沉沦,这在文艺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都给文艺理论、美学研究提出了各种尖锐问题。王元骧先生以敏感的问题意识、可贵的探索精神、严谨的学术思考,直面时代现实,针对现实问题给出了自己深刻而富有价值的理论回答。
根据不同时期王先生关注的理论问题的不同,王先生至今的学术探索可以划分为审美反映论、文艺实践论和文艺本体论三个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王先生主要对审美反映进行了充分研究,90年代中期以后他更多地思考了文艺实践论问题,而21世纪以来他论述比较多的是文艺本体论。对这种研究重心的变化,有学者认为王先生的学术研究在转轨,但王先生不认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说:“我是在沿着同一轨道推进的,以后的这些‘论’,其实都是从‘审美反映论’中生发出来的,是‘审美反映论’已经蕴含了的,或者说是由于对‘审美反映论’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所必然导致的理论指向。”【3】王先生的自我分析是准确的,从治学倾向来看,他确实是从社会现实所引发的问题意识出发,对自己的文艺理论、美学观点按原有的思想轨迹进行了自然的延伸,文艺实践论也好,文艺本体论也好,与王先生的审美反映论都有明确的思想联系,这些不同的“论”其实都是社会现实影响下,王先生自己思想逻辑的必然变化所致。
一 王元骧先生治学的总体特色
王元骧先生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非常注重学理——这一特点的形成应该与王先生的理论研究属于“学院研究”密切相关。王先生的论著逻辑严谨、理性色彩鲜明,观点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比如,就他的理论文章来说,即使是他自己不太满意的、早期对文学典型问题的研究,也因为他曾对西方文论中典型理论的发展变化有认真的历史梳理,所以他根据西方典型理论的历史变化趋势,结合自己对文艺的艺术特点的理解而提出的观点,论证严谨、认识深刻,让人无法轻易辩驳。再就王元骧先生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变化来说。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艺理论、美学研究,因为受西方理论的深刻影响与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的制约,它们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的,王先生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也不例外。但与很多学者研究兴趣广泛、论点多变不同,王先生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在变化时,变中有不变,变而有理据——他不是随着学术热点的变更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认识,因而他的研究内容有时看似保守,但却“保守”中有新意,经常可以见到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见提出。比如他早期的文学典型研究受认识论文艺观念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艺观念转向审美反映论,虽然从文艺观念的性质上看,这种转变是比较大的,但这种变化也有其内在的变化逻辑。我们注意到,王先生早期在研究阿Q这一典型人物以及文学典型的相关问题时,虽然在文艺观念上还深受认识论文艺观的束缚,但已经非常重视文学的审美、艺术特性。比如他非常重视文学典型的独特性:“我们在平时阅读文学作品时都会感到,一切优秀的艺术典型都是丰富多彩、不可重复的。”而且,他对典型形象的分析一方面着眼于典型形象的个别性:“文学是通过个别的、具体的感性形象,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生活本身的样式’来反映生活的”;一方面又重视艺术家反映生活时的创造性,即关注典型形象与生活中的“原型”的不同。【4】特别是在后一方面,王先生强调艺术家独特的感觉、思考和审美评价以及富有艺术个性的艺术创造和艺术表达的意义和价值,这说明他的艺术观念与后来的审美反映论,在重视文学的审美、艺术特性方面有一定的思想延续性。更进一步,如果说关注文艺形象(文学典型)意味着关注文艺活动中的想象问题,而研究文艺的情感反映特性,则意味着关注文艺活动中的情感问题。这种变化从文艺心理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只不过是研究重心从想象转移到了情感,这种研究变化的逻辑也就更容易理解了。
王元骧先生对学理的重视,从根本上说来自于他对学术研究的虔诚。以求真为学术研究的最高追求,淡泊名利、心无旁骛,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他对理论研究的学理性的重视。另外,他对学理的重视也得益于他对理论研究方法的有意识关注。自然,他关注理论研究的方法问题与他重视理论研究的学理性是统一的,两方面是互相作用的。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王先生的论著所具有的强烈逻辑理性色彩就形成于他在探讨具体问题时所具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意识。总体上说,王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深刻的掌握,其理论研究对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有娴熟的运用。就思维层次来说,他经常把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不同理论层次的认识有意识地辩证统一起来展开探讨,这就能够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思维具体”的深入把握。就研究角度来说,努力从不同的角度来综合性地把握对象,比如从科学性与人文性、静态与动态、时间性与空间性以及经验与超验等角度的统一中来综合性地把握对象,以达到对研究对象的全面深入认识,也是他习惯采用的研究方式。总之,唯物辩证法的深入掌握和熟练运用,是王先生的理论研究能够走向深刻、准确的重要原因,是他的理论研究具有深刻的学理性,研究结论具有强大的理论说服力的重要原因。
进一步说,研究方法不是抽象的,它并不是可以无限制地到处运用,适用于各类不同研究对象的万能方法;在理论研究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应该适应研究对象的性质。王先生之所以对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青睐有加,这一方面是他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王先生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美学学科的性质有科学的把握。王先生认为,文学活动除了具有认识性内容外,情感、价值是其更为重要的构成要素,所以他主张研究者应该对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人文性有所意识,对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要进行多角度的综合性探讨。这一认识在根本上决定了王先生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科学性和深刻性。
关注社会现实是王元骧先生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另一突出特点。正如上文提到的,王先生的理论研究虽具有浓厚的学院气息,但并不脱离社会现实,而是始终针对社会现实向文艺理论和美学提出的问题的。比如在早期的文学典型研究中,王先生对文学创作概念化的理论批判就是显而易见的。文学创作的概念化和模式化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直至70年代末一直是我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中的顽疾。这主要是因为文艺活动因社会现实的影响,受到了政治活动强有力的束缚限制。王元骧先生早期的文学典型研究就是直接针对这一长期以来的现实问题的。王先生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中的这种理论针对性,在他的许多论文中都有非常明显的表现,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理论研究的现实感。具体地说,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审美反映论主要针对刘再复的主体性文论对文艺反映论的理论挑战,同时也回应了文学研究中“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争。新时期以来,受改革开放要求人们解放思想的影响和西方文论各种新颖文艺观念的启发,人们多强调文艺活动相对于社会现实及历史的审美独立性,因而对长期以来强调文艺反映社会现实及其历史发展的文艺反映论提出了批判。特别是刘再复的主体性文论以及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论争造成了文艺观念的极大混乱,文艺反映论中强调文艺与社会现实的密切联系的科学论断也在泼机械唯物主义的脏水时一块倒掉了。王先生从对文艺的情感特性的把握入手,在积极地探讨文艺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审美性质,从而与钱中文、童庆炳等先生共同推动审美论文艺观念确立的同时,又深入论证了文艺的情感反映特性,这就在吸收主体性文论和“内部研究”的科学观点的同时,捍卫、发展和完善了文艺反映论,提出了自己的情感反映论,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中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王先生9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艺实践性研究和文艺本体论研究,在理论上主要是针对我们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长期以来主要关注文艺的认识性质而忽视文艺的实践属性这一理论失误而展开的。而这一理论研究,同时也回答了在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统治一切的当今时代,文艺对人的生活有何价值意义的问题。总之,王元骧先生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密切联系社会现实,认真地回答了时代向文艺和审美提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发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探讨。自然,王先生的理论研究对时代现实的关注是通过严谨的学理探讨来实现的,关注现实和讲究学理是他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积极探索、综合创造也是王元骧先生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在直面社会现实问题,严肃认真地展开文艺理论、美学研究时,王先生在治学思维上的突出特点就是进行“综合创造”。王先生曾有论文集以“探寻综合创造之路”为名,这就是被列入以集中展示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研究成绩为目的的《新时期文艺建设丛书》中的《探寻综合创造之路》一书,此书的命名并不是偶然的。王先生说:“我一直认为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只有在多种关系和联系中才能认清它的面目,对它做出全面而准确的把握。”“我觉得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造’的口号,不但对于哲学界,就是对于文艺理论界来说,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回顾自己这20年对于文艺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似乎自觉不自觉地也正是在走着这一条道路,用我为自己所确立的目标来说,就是‘融合百家,独创一格’。”【5】所以,综合创造一直是王先生文艺理论、美学研究中自觉的学术追求。
王先生治学上的综合创造如果从研究方法上看,就是上文提到的,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熟练运用——从不同的思维层次和不同的认识角度出发对文艺理论和美学问题进行综合探讨;而如果从理论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这一“综合创造”指的是在探讨具体问题时对各种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的综合运用。王先生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界一直被看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研究者,但他的马克思主义“色彩”除了表现为不脱离现实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外,主要表现为思考问题时的辩证认识;而正是这种辩证认识使王先生的理论研究形成了视野开阔、思维严谨、论证充分的优点——为了充分、深入地展开理论研究,王先生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思维层次来综合性地把握相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有助于具体研究的中西古今思想资源都被积极地吸收借鉴,这极大地增强了王先生观点的理论说服力。概括地说,从接受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影响这一角度来看,王先生在早期的文学典型研究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审美反映论研究中,受苏联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影响比较突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他开始走出苏联认识论文艺理论和美学模式的影响,努力从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实践性思想中吸取理论营养,试图在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这一大方向下进行理论综合。而21世纪以来,他对文艺本体论问题的关注,使其注意到了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中“经验”和“超验”两大思想系统的不同,因此努力尝试“经验”研究与“超验”研究的综合成为其借鉴西方理论思想的主要方向。下文,我们将结合王先生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发展变化,主要对其接受外来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影响进行梳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