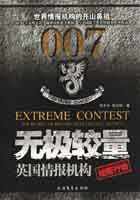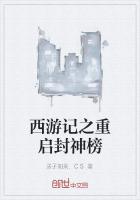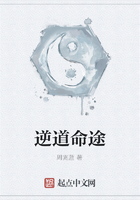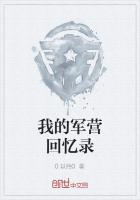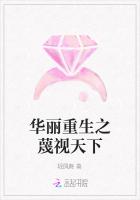口述 陈宗烈 整理 韩斌
一台罗莱福来,一台莱卡F3,闪光灯是灯泡式的,轰一声,闪一下,换个灯泡,被拍的人往往丢了魂似地吓一跳。1956年至1959年的西藏还处于封建农奴社会,贵族、领主、牧民、农奴、乞丐的生活情态都被我收入了镜头
20岁之前,我不知道摄影为何物。我一直生活在江苏老家,带领弟妹种地、做小学教员、参加土改,一心要求进步,却因为有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的父亲,而被主流社会拒之门外。
父亲的故事本来和我们的话题无关,只是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让我再次看到父亲这一辈中国人的缩影。和这部剧里的杨家兄弟相似,我家也是国共两党共存:抗战爆发,我的两个舅舅加入了新四军,我的小姑妈去了延安,当小学教员的父亲投奔了国民党军队,军部组建了个“血花剧团”,父亲担任上校团长,宣传抗日……在那个举国热血的时代,我们家是两种主义,一种情怀。
父亲看不惯国民党贪污腐败,也买不起全家六口人的飞机票,没去台湾,回到老家,在朋友的工厂里当会计。1951年镇压反革命,他被判刑10年,送到青海劳改。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被特赦,回老家没几年就病逝了。而我们,因为家庭问题,入团、参加抗美援朝,都没有份。
在家乡没有前途,生活都有困难,我到北京投奔小姑妈。北京机会多,到处在招工。我参加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考试,竟然被录取了,工作是当摄影师的助手。
我大开眼界。我参加摄制组,拍过西安飞机厂、洛阳拖拉机厂的选址建设,拍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片,拍过乌兰诺娃、米哈伊诺夫等苏联艺术家的来华演出。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用镜头来记录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工作努力,我1954年被保送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新闻纪录电影摄影。
“家庭成分”始终是一座大山。领导劝我改行:“现实是严酷的,搞新闻摄影的很有可能进中南海拍摄,你第一关政审就通不过。”
郁闷中,厂里贴出布告:《西藏日报》社成立了,需要摄影记者。
我看到了希望。我不能搞电影了,还可以去拍“呆照”啊(搞摄影的对拍照片的戏称)。西藏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一定会有我的作为。
1956年,我24岁。7月底,我提着一个铺盖卷、两只纸箱子,坐上一辆美国造军用道奇卡车——那是解放战争时缴获的战利品,历经21天的颠簸,和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一起,豪情万丈地来到了拉萨。
满怀干劲而来,现实与想象却大不相同。领导要求我们树立“长期建藏、边疆为家”志向,一切行动遵照“十七条协议”,适应西藏特殊的社会现状。“门里是社会主义,门外就是封建农奴社会”。上班、生活的圈子,就是报社的大院
我安下心来,参加报社组织的学习班,先过语言关。
藏语是拼音文字,规矩多:上层对下层,或者平民之间交谈,用的是口语,相当于藏语“大白话”,贵族之间交谈、下层对上层人士说话,必须用敬语。敬语是一种非常文雅的书面语,比如“你叫什么名字”,敬语必须说,“请教阁下您尊姓大名?”有点儿像“文言文”。
我们的藏语老师杨化群是四川人,当时是藏文编辑部的副主任。他自编一套教材,深入浅出。我学得很有兴致,进步也快,不到一个月,就掌握了一千多个词汇,日常交流基本没有问题了。
杨化群这人不简单,他曾是拉萨三大寺之一哲蚌寺的喇嘛,是当时少有的汉僧,对古典和现代藏文都很有研究。他的感情生活很传奇,妻子是拉萨的尼姑,名叫益西旺姆,两人相爱后双双还俗。益西旺姆后来成为西藏广播电台第一个藏语播音员。
报社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不少。我们有三位副总编,其中一位擦珠·阿旺洛桑,是个活佛,是西藏历史上最早东渡日本的留学生,他的学问与诗赋,在社会上极负声望。
而每天上午,总有一个身穿澳毛长袍、戴着玳瑁近视眼镜、面容清秀的老人,颤巍巍地走进报社大院。藏族职工见了他,躬腰立于路旁,恭敬地问候他:“公俄,古苏德波银呗?”(公爵,您贵体安康否?)他叫江乐金·索南杰布,是西藏藏文编审委员会委员,报社藏文编辑部的顾问。
江乐金的祖先颇罗鼐被清朝政府封为“郡王”,这个高贵的封号承袭了九代,传到江乐金是第八代。江乐金懂英语和印度语,是个大学者,他还曾是个激进的贵族青年:1939年,他创建“西藏革命党”,想改变西藏的社会制度,按照英国模式,搞议会制。失败后被西藏地方政府抓捕判刑,后来流放到了无人区。他设法逃到印度,成了拉萨当局的通缉犯。直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才回到西藏。
江乐金一生都很前卫。西藏男人当时仍留辫子,他却是一头黑亮的短发。晚年,他创造了很多藏文的现代名词,比如藏文的“报纸”(擦巴)这个词,就是他的原创。照片上他睿智的眼神、清冷的侧影令我动容,我想,像这样的大贵族、大知识分子,一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人都被我摄入镜头,成为一个时代特有的印象。
进藏不到一个月,中央通知,决定在西藏实行“六年不改”(暂不进行民主改革)。人员收缩,原来调进藏的通通撤回去。《西藏日报》从内地引进了三百多人,半年里走了百分之八十。我选择了留下——当时,报社的摄影记者只剩下我一个
尽管争取一切机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但是在拉萨,我还是嫌摄影的机会少。
没想到引路人很快出现了。他就是报社的另一位副总编,噶雪·顿珠。
噶雪是“噶厦”(地方)政府派来的四品官,他是西藏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之一,大贵族,从小在印度长大,英语很好,曾经做过达赖的口语翻译。那时他30多岁,当地人称呼他“噶雪赛”(噶雪少爷),他一出现,人们往往低头伸舌,表示敬畏。
我进入他的视线,是因为我能用敬语和他交流,还会说两句英语来补充——我的英语是新中国成立前学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差,教材是林语堂编的开明课本。这让他觉得我与众不同,很器重我,主动说:“以后我们可以好好合作,有重大报道,我去写文字,你呢,拍照,我们配合。”
太好了,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从这以后我就跟着他四处活动,就此走进了西藏社会更深更丰富的层次——寺院、僧侣、贵族、官吏……
那时西藏还有一些摄影记者,新华社的、军区的,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我的幸运。我拍的有些照片,当时并没机会在报纸上发表。我想,今天不能发表,说不定将来有用,而且我还自己花工资积蓄另买了一台莱卡F3,带在身边。没想到当时这个非常简单的想法,让我现在很庆幸自己有那样的“远见”——所有的惊鸿一瞥,现在都成了永久的历史定格。
西藏的贵族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封闭的,一种是现代、有新思维的。噶雪·顿珠属于后者。他追求进步,思想开放,认为共产党、解放军是为老百姓做好事的,修路、开厂、办医院、建农场,都是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噶雪带我参加的第一个重大活动,是1957年的“莫朗钦波”——每年藏历新年第二天举行的传召大法会。在那些天里,拉萨完全变了样,到处是身着绛袍的喇嘛,如同一片红色的海洋。政府官员和警察都不见了,取代维持秩序的是铁棒喇嘛和朵多喇嘛——后者脸上抹着锅底灰,膀大腰圆,状如凶神恶煞。
1957年的大法会,宗喀巴传人甘丹赤巴·土登衮嘎大活佛要到大昭寺的松曲热广场讲经。宗喀巴是格鲁派(黄教)创始人,他最小的弟子根敦珠巴死后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甘丹赤巴的宗教地位十分崇高,那一年他已经90多岁了,担任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的会长,是一个爱国的高僧。
我和噶雪一同前往。他黄袍马褂,传统装饰,盛装出行,我西装革履,紧随其后。刚走到八廓街,已经人山人海,无法插足。噶雪问我:你带钱了吗?我说有,从身上摸出三个“袁大头”来——那时,人民币在西藏还不流通,当地人只认有袁世凯头像的大洋。
噶雪向一个铁棒喇嘛招招手。那喇嘛满脸涂墨,臂系红布,手执木棍,腰挎大刀。见是个贵族招呼他,便大大咧咧地走过来。噶雪尊称他一声“古秀拉”(先生),希望他为我们带路进广场。一边说,一边塞银元给他。喇嘛收了钱,二话不说,粗声吼着“啪纠纠”(快滚开),用手中的棍子在前挥舞,原本水泄不通的人群竟然像海水被从中分开,闪出一条通道来,我们仿佛捻着避水诀的孙悟空,跟着他长驱直入,一直走到正在讲经说法的大活佛面前,拍到了一幅幅难以重现的场面。
正午时分,烈日下出现了一列色彩斑斓的队伍。开道的是前驱警跸,手执经幡的仪仗队紧紧跟上,之后是贵族、僧侣、地方政要,他们身着盛装,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其中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大“嘎伦”
1958年8月,哲蚌寺、色拉寺举行考“格西”活动。格西是藏传佛教的最高等级学位,相当于“神学博士”。活佛都要前去应试,噶雪跟我说,我们一起去看看,可以多拍点照片。
从拉萨哲蚌寺到色拉寺的长长的土路上,事先用石头铺好了一条警戒线,中间就是所谓的“神路”,只有活佛和仪仗队可以行走。老百姓就在“神路”的两旁烧香、叩拜。
正午时分,烈日下出现了一列色彩斑斓的队伍。开道的是前驱警跸,手执经幡的仪仗队紧紧跟上,之后是贵族、僧侣、地方政要,他们身着盛装,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其中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大“嘎伦”(首脑)。
中间是一顶黄色锦缎包裹的大轿,活佛就在轿中。轿子是清朝顺治皇帝所赐的“金顶黄轿”,后来一直都用这顶轿子——破了,就按原样修好。轿前有“孔雀伞”,轿后有华盖,不停旋转。
贵族和僧侣们的家奴、侍从和护兵牵马徒步前行,簇拥着各自的主人,组成这支浩浩荡荡、排场十足的队伍。
当日我没看到其他的摄影师,只有我一个人跑前跑后,对着这一盛大的场面拍得畅快淋漓。因为噶雪的关系,我跑到轿子跟前拍照,也没有人阻拦。
当时拉萨居民三万余人,乞丐就有四千多。他们嘴里叫着“咕几咕几”(求求你),伸出拇指冲上的双手行乞。有的还高唱乞讨歌:“呀拉嗦——天上的飞鸟,没有比麻雀更小的了,啊啊啊——地上的人哟,没有比我更可怜的了!”
虽说“院子里是社会主义”,农奴社会等级森严的气息却无处不在。报社有个藏族勤杂工阿旺,出身“育布”(佣人),专门为编辑部打扫、送水。每次见到噶雪、江乐金等贵族,立即低头旁立,弯腰吐舌,离开时倒退着走,到门口才敢转身出屋。
我说,阿旺你参加革命了,已经是国家的主人,贵族和平民都是平等的同事,你应该挺起胸来。阿旺说,农奴当久了,见了贵族老爷总是心里害怕,奴性在作怪哩。后来在同事们的鼓励下,他才慢慢打消了顾虑,挺直身板。
那时候我总想找各种机会,跟随工作队下乡,去接触拉萨以外西藏的实际生活。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去拍西藏各个阶层的原始生活状态、地理宗教环境,觉得应该积累这些资料。
工作队下乡,有的给农牧民看病,有的为牲畜防疫,兼带宣传政策。一个工作队十一二号人,队伍却浩浩荡荡,骡子、毛驴就有一二十头,大部分用来驮礼物。礼物送给头人和领主——下乡需要当地人的指引,不然寸步难行。礼物包括茶叶、绸缎、银元。在牧区一块银元买一只羊,六块银元就能买一头牦牛。领主收到礼物,通常都很高兴,就会让管家帮着我们开展工作。
我们和农奴有接触,但都不够深入,因为和农奴打交道多了,领主会以为我们在做农奴的思想工作,势必引起误会甚至反感。既然不能多说多问,拍照就是最好的记录。
1957年,我跟着工作队来到金龙谿卡庄园,借宿在农奴扎西旺堆家。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厉声的训斥声,出去一看,原来是管家强桑前来逼债。管家肥头大耳,恶言恶状。扎西旺堆一脸畏缩,愁苦满面,无助的目光低垂到地面……没有比这更强烈的对比了。我悄悄拿起相机,灯光一闪,把恶管家吓了一跳。
另外一张农奴半夜吃饭的照片,也是抓拍的。
那是在另一个庄园。农奴整个白天一直在地里干活,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半夜,他们回来了,疲惫不堪。牛棚就是他们睡觉的地方。管家提来一桶萝卜汤和一桶糌粑,这就是晚餐:汤是漂着几片萝卜的清水,糌粑是粗糙的豌豆磨成炒面,一般都是给牲口吃的,人吃了肚子会发胀。这样的情景,令人心酸。
那段时间,形势已经很紧张了,经常有消息传来,哪里发生了叛乱,攻击我们的机关和学校,偷袭我们的部队。有一次,我跟着兽疫防治工作组下乡,被一帮武装叛匪跟上了。我们走他们跟,我们停他们也停,他们经常在山顶或高坡驻扎,居高临下地监视我们。晚上我们都要轮流放哨。
他们跟了我们一个月,一直没敢下手,因为我们也不好惹——12个人,个个身强力壮,配有武器。我们的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开第一枪。
这是1959年平叛和民主改革前我亲眼所见的西藏社会情景,我们都有强烈的感受:西藏需要变革。
1980年,我工作调动,离开了西藏,领到了三千元安家费,携妻儿在北京安下了家。今年3月,我把一百张西藏的照片捐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也是国博关于西藏地区的首次专题性收藏
命运是奇妙的,它对你关上了一扇窗,同时又开启了一道门。进藏半年,因为工作出色,我被破格吸收入党。1960年,我被评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就是全国劳模了。如果在内地,我的命运轨迹肯定不一样。
评上劳模的消息,是1960年5月收到的,报社给我发电报,催我到北京开大会,我还很不情愿呢——那会儿我正在珠穆朗玛峰上,准备跟着中国登山探险队第一次从北坡登顶。
“文革”中我也受到了冲击,被发配到林芝的原始森林里劳动。西藏的天很蓝,深邃得望不到尽头,原始森林寂静而迷人。美丽的尼洋河从密林中穿流而过,河水纯净清澈,可以把河底的石头看得清清楚楚。在那里“劳动”,倒别有一番难得的意境。
我利用闲暇时光,动手做了一个红木的板凳,又在凳子底面刻上心里的话,托人带给远在拉萨的妻子,而她给我的回信让难兄难弟们嫉妒不已——那是写在一张张裁得整整齐齐的粉红色的纸上。
1956年进藏,1980年离开,这25年,我亲身经历了西藏从封建农奴社会到平叛、民主改革、“文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几个翻天覆地的转折,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了它从“旧”到“新”的历史全程,这些照片现在被公认为珍贵和有价值。
今年3月,我应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要求,把这批照片中的一百张照片捐赠给了该博物馆。这也是国博关于西藏地区的首次专题性收藏。
前些年我重返西藏,看望了很多老朋友,包括我的“阿嘉拉”(姐姐)次仁拉姆,百感交集。
次仁拉姆从前是农奴,1961年,翻身农奴组织互助组,桑嘎村的11户“朗生”(家奴)因为不会干农活,被排斥在外。次仁拉姆的丈夫强巴叹气:“会跑能飞的都入组了,只有过去住马厩的人剩下了。”次仁拉姆却很有主见,把“朗生”组织起来,学习务农。三年后,他们摆脱了贫困,实现了丰衣足食。这个“朗生互助组”被称为“百万翻身农奴的好榜样”,次仁拉姆当上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我在桑嘎村蹲点采访了三个月,她也成了我的“阿嘉拉”。从此,她每次到拉萨开会都要来看我。
我调回北京10多年后再次见到她,当年的少妇,那时已经70多岁了。她从冰箱里拿出啤酒,爽朗地说:“以前请你喝青稞酒,现在要请你喝啤酒啦!”
我的西藏朋友们,和从前相比,他们的生活早已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