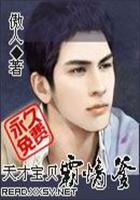因为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所以街上就略显冷清,两排的商业街上的店面门紧闭,除了肯德基依旧傲然挺立在市中心最热闹的繁华大街。
陆予说的认识的人就是眼前这个穿着颇有当年一夜而红的小沈阳穿的苏格兰裙子,头发过腰,用紫色发带束起的男人。
老实说,我一开始还真没敢说眼前这货是男人,只是颤颤巍巍的上前一步,恭敬的说道:“敢问这位对方性别?”他很娇羞的捂嘴一笑,然后直接把我的手放到他胸上,我眉头紧皱,面色极其纠结。
首先,我知道了他是一个纯男人。
其次,我感受到了他强烈的胸肌跳动。
陆予眼光一个凛冽的扫来,他笑呵呵的收回手,冲我抛个媚眼:“我名字叫魏维,你可以叫我维。”魏维是本市唯一登过美国杂志采访的一位理发师,他有两句话说的特别经典:“你说你搞艺术,我说我搞你的头发,那叫深入艺术。”
“无论你官多大,地位多高,来到我地方,我最大,我让你低头你就得低头,我让你抬头你就要抬头。”
我的目光一下子从呆滞变为敬佩,冲他竖起大拇指:“魏大师啊!你看我这头发还有救不?”我揪着我的发尾,前几年烫发过多,发质变得不好,还开叉。魏维靠过来,瞅了会儿,吧唧嘴:“你这头发谁给你烫了,把头发都烫死了,只能给你修修,然后用好一点的护发素洗洗,也就这样了。”
我说:“你就随意来吧,我相信你!”
三十分钟以后,请你们当我没说过上一句话。活了将近快三十年,发现人生中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刚剪完头发后自己的模样。
“你看,多漂亮啊——”魏维在耳边赞叹道。
剪短削薄的头发紧紧的贴在脸两旁,那一头清爽的短发披在脑后,干净极了。一双明亮的杏仁眼闪闪的,微红的脸蛋透着成熟,红润的唇瓣微张。就是头发跟狗毛一样,轻飘飘的,动不动就静电飘在半空中。我的眼神很是怀疑的瞥向那头坐在沙发上的陆予。
他也扭过头,带着调侃的意味说:“是不是啊,陆予,真的很漂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