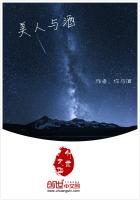母亲一进入庙中,才仿佛恍然大悟,怎么能跑到这个地方呢?她将庙内环视了一番,但实在是跑不动了,她想找个地方暂时躲一下。可是就连那尊依然高坐在供桌上方的菩萨,也是个泥木做的实心菩萨,想如同电影中那样藏进菩萨的肚子里去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躲到菩萨身后,也无法将自己全部拦住。母亲慌忙又往外跑,可那个日本兵已经追进来了。
面对着双手端着长枪的日本兵,母亲大睁着惊恐的双眼,一步一步地往后退,日本兵则一步一步地逼上来。
然而,我母亲那双紧紧盯着日本兵的大眼,虽然有惊恐,但在惊恐之外,更多的却是冷峻——她往后退的脚步,并不是慌乱,每一步提前往后挪动的那只脚,一落到身后,即呈横形脚掌,也就是说,只要她站定不动时,保持弓步或变成马步,就随时都能招架攻击并及时反击。我母亲从我那武秀才叔祖父那里偷学来的武艺,第一次面对着一个异国侵略者,一头无恶不作的野兽,展示出应有的功效。只要这个日本兵不是对着我母亲,将那三八大盖的扳机一扣,那么尽管他有着一杆吓煞人的钢枪,真要拼打起来时,谁胜谁负,尚难以预料。
这个日本兵并不想在这个时候扣动扳机,他如果想扣动的话,早就已经扣了。他从穿在脚上的靴筒子里抽出了刺刀,他用左手提着枪,右手扬起那把刺刀,说出了一句我母亲竟然能够听得懂的话。
我母亲一听懂他说的那句话后,就用手指着自己那涂过锅末灰的脸,再使劲地摆手。我母亲说自己不是日本兵说的那个,绝对地不是。可是我母亲不知道,她那张涂过锅末灰的脸,早已经汗水浸淋、冲刷,不时地用衣袖、围裙擦汗,显现出来了她的本来面目。
日本兵不知是不是能听懂母亲的话,如果他真的听不懂,那么从母亲的手势也能明白,于是他吼叫起来,大概是斥责母亲在说谎,恶狠狠地说母亲就是他说的那个!
我母亲忙用手指一指自己的背上,那意思是告诉对方,她已经是好几个孩子的妈妈,你若不信,背上还正背着一个。可我母亲的这些意思却似乎激怒了这个日本兵,他高扬着刺刀,比划着,越逼越近。
我母亲装作不懂他的意思,一边往后退,一边像害怕不已地转动着她那灵泛的眼珠,寻觅着可以防身的武器。然而,庙里除了那泥塑木雕的菩萨,任何可用来抵挡的东西也没有。菩萨脚下只有一个供桌,供桌上有一只香炉,炉子里残存着不少烟灰。
我母亲一步、一步,慢慢地往供桌移去。
日本兵逼得更近了,我母亲能清楚地看见他脸上布满的疙瘩,那些被称为青春痘的疙瘩,似乎在他狰狞笑着的脸上不停地跳跃;还有那两道浓黑浓黑的眉毛,和浓眉下那双既充满杀气,又浸透着淫欲的眼睛。
他也许不是一个职业的“武士道”狂徒,而是在日本近卫内阁新体制下被征召入伍或自愿入伍的一名年轻士兵。他要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向他们的天皇发誓,不惜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他在入伍前,也许是一个农民,也许是一个工人、小商贩,甚或是一个学生!他在自己的故土,在自己的家乡时,遇见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也是像老街人一样非常礼性地打招呼的,作为一个日本人,他当然不会像老街人那样开口便是“你老人家”,但他和他的同胞们那满口的敬语,每句话最前面的敬称,其实比“你老人家”还要显得尊敬,使用的频率还要更高。而且,他和他的同胞中也有信佛的,对菩萨的虔诚信仰,希冀菩萨保佑的心情,和中国的信徒没有什么不同。他正值青春期,他一定有位可爱的女友,或者已经有了一位温柔漂亮的妻子,可他此刻,却要强奸一个中国的母亲,而且就在有菩萨看着的庙里!他还打算在菩萨的脚下强奸了这位母亲后,将这位母亲杀死,包括母亲背上的婴儿。他会不会将所做的这一切,写信告诉他的女友,或者他的妻子呢?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会告诉他的同伙,会告诉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向天皇发过誓的家乡人,他会以此为炫耀,甚至作为他的战绩,那就是他又强奸了一个中国母亲,又杀死了一个中国女人和一个中国婴儿!
当我成为新中国的大龄中学生后,我曾拿来一篇著名作家写的访问记,念给我父亲听,那篇散文说的是这位作家访问日本,亲眼看到了美国丢原子弹对日本人民造成的巨大的伤害,那篇访问记写得很有感情,厉声谴责美国丢原子弹的罪行,说日本人民是和中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可我还没有念完,我那位实在有点儿蠢的父亲却跳了起来,他说:“这是什么混帐东西,竟然说美国丢原子弹丢得不对?!美国不丢原子弹,日本会在那一年投降?!什么日本人民?什么对中国是世代友好的,把我们老街人几乎全杀光了的(他又说的是老街,他只知道老街!如果他知道全中国有多少人被杀害,那还不知道会怎样呢!),不是日本人?没有日本人,哪来的什么日本人民?人民不是由人组成的,而是由畜生组成的啊!?”父亲对我说:“你不要在老子面前摆知识,老子没有知识,但老子有眼睛,老子的眼睛亲眼看见过,也看得清清楚楚!”父亲甚至还指着我说:“当年那日本人一刀把你给捅死就好了,你就到阴间去说日本人民其实对你是友好的……”
父亲发完这场令我不能不感到害怕的火后,竟不时偷偷地翻我的书包。他从我的书包里找出《新华字典》,专门去找“人民”的释义,可这本字典里却没有“人民”这一条。后来他不知是在谁那里借到一本词典,并请那人为他找到了“人民”的释义。父亲指着那一条对我说:“你看,你看,这上面写着呢!”那本词典上面的原话是:“人民: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然而从父亲口里念出来,却成了“人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父亲自己不会断句,他以为字典上是没断句,便按照他的断句,将一句话念成了七句。但他抓住了要点,他说:“就是劳动群众,就是基本成员哩!那些当日本鬼的人,不是劳动群众啊?他们还会都是些财老板啊?他们不是基本成员啊?!难道还都是高头有钱有势的成员啊?!高头有钱有势的成员会去当兵啊?!”父亲不知道“上层”这个词,他认为“基本”的对立面就是“高头”。
我母亲将我藏在草丛里,日本人自然没对我捅刀,可日本人的刺刀已经比划着我母亲的胸衣,要我母亲将衣服统统脱掉,不然就要用刺刀划开!
这个时候,我那伏在母亲背上的三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这个幼小的、真正完全不谙世事的生灵,大概也觉察到了母亲的危险,他似乎知道,如果母亲没了,他这个幼小的生命也就没了。他的突然大哭,既像是在为母亲着急叫喊,也像是在替母亲求情,求这个日本兵在菩萨面前发一次善心,放过母子二人。
然而,三弟的哭叫,不仅没有感化这位日本“基本成员”中的一员,不仅没有帮上母亲的忙,反而使得日本兵那狰狞的笑都不见了,他一下冲过去,一把就要从我母亲背上将我三弟抓到手上。
母亲本来已经做好了逃脱的准备,可三弟的这一哭,日本兵的这一扑,必须首先保护儿子的本能,使得母亲不能按原定的步骤出手,而只能迅疾地一挪步,离开了供桌,离开了供桌上的香炉,使日本兵没能抓着她的儿子。
与此同时,母亲脸上显露出了乞求不要伤害孩子的表情,这表情是那般的痛苦、无奈、让人心疼。
日本兵却比划着做了个恶狠狠地要母亲把婴儿摔到地上的动作。他将左手抓着的枪往地上狠狠地一顿,接着往地上一掼,再加一脚,踩在上面。他这一顿、一掼、一踩,就是对母亲乞求不要伤害孩子的回答,就预示着对我那才几个月的三弟要付诸的暴行。
就在日本兵那一脚踩下去时,我母亲猛地往供桌旁一跃,伸手抓起一把香灰,准确无误地撒到日本兵的脸上、眼里。
日本兵哎呀一声,忙用手捂住双眼,就连右手上的那把刺刀,也掉在地上。
母亲趁着日本兵捂眼睛的这一瞬间,从庙里飞奔而出……
母亲撒出去的这把香灰,是老街人向日本人的第一次还击。虽说只是一把香灰迷住了日本人的眼,使母亲逃脱了魔爪,但让老街人知道了,日本人的眼睛也是进不得灰的,被灰迷了的日本人也是要用手去擦的,从而推定:日本人的脑壳,也是能被砸烂的!
十
我们终于到了白毛姨妈家里。
白毛姨妈的房子建在一个山坡上,虽说是山坡,但已被整理得相当平整。房子背后是一片葱郁的竹林,竹林中间有一条小道,通到一个池塘,池塘里的水已经干涸。我们就是绕过干涸的池塘,沿着竹林里的这条小道,来到白毛姨妈家后门的。
白毛姨妈的房子虽然是茅草屋,但很大,有好几间,每一间都很宽敞,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用做厨房的大间里,还有一条像小溪样的水道从厨房流过,不知我白毛姨妈是从哪里接水进来的。水道里的水已经很清了,可水道旁边还打有一口水井。白毛姨妈只是在水道里洗菜、洗衣服;煮饭、炒菜、喝水都是用水井里的水,这口水井很深,打上来的水比老街的井水还甜。
白毛姨妈和她的丈夫都很能干,他俩在这深山老林里,本来过着极其平和的日子,几乎所有的生活都能自给自足,每年只需下山换些盐、整理整理农具什么的。但可惜我姨夫年轻轻的就积劳成疾,山里人只能靠采些草药治病,那草药再神奇,使用不善的话也使得许多本可以治好的病,成了不治之症。年轻轻的白毛姨妈没有孩子,孤身一人,我真不知道她一个人是怎么在这深山老林中捱过每一天的。但白毛姨妈生性快活,似乎并不犯愁,还特别爱笑。
白毛姨妈一见着我们,高兴得连蹦带跳。她一把抱起我,将我举到她的肩膀上,要我骑“高马”。她又抱过我三弟,在三弟脸上一顿乱亲,亲得三弟哇哇大叫,她则笑得格格的不停。
当白毛姨妈得知我们是如何遇险,又是如何脱险的事时,一个劲地说搭帮菩萨保佑,搭帮菩萨保佑。
我在一连啃了几根包谷棒棒,吃了两碗糙米饭,喝了一大碗秋丝瓜汤,将饿得瘪瘪的肚子胀起来后,坐到母亲的对面,目不转睛地盯着母亲。
母亲见我这么使劲地盯着她,不由得摸了摸脸,说:
“你这样看什么?我的脸还没洗干净?”
母亲不知道,我这是在用崇拜英雄的眼光注视着她。但我不会说“英雄”,又一时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话来,便突然说:
“妈,你就像是大戏台上的赵子龙!”
我跟着母亲看过大戏,那是从县城下来的戏班子,在老街河对面的沙滩上扎起戏台,天还没黑就响起锣声、鼓声,那锣声鼓声先是零零碎碎地敲几下,打几下,夹杂有几声尖厉的唢呐叫,还有二胡的调弦声。到得天黑下来时,锣声鼓声骤然热烈,时而如疾风暴雨,时而如扶夷江中涨水的大潮,响得老街上吃夜饭的人做手脚不赢,忙忙地扒完几口饭,便吆喝着去看大戏。此时四乡的人也开始来了,且衣服都要穿得整齐些,平时难得有社交活动的姑娘们、小媳妇们也能成群结队而来,各自在头上插一朵花,或在对襟衣服的布扣子处别一条鲜艳的布巾,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也无人干涉。人群中的问候语更是不断,“你老人家,去看大戏哩!”“有大戏看哩,你老人家!”如过节日一样的兴奋。
大戏台下的观众皆是站着,无人坐凳,好自由活动,站累了,走开,到沙地上坐下,讲白话,讲那旦角是如何的漂亮,那武生是如何的威风……戏台上的唱词其实是没听清几句的,也用不着听清,大抵都是晓得戏文的;老树的树杈上则爬满了细把戏,彼此说着与戏文完全无关的事,唧唧喳喳,像喜鹊似的叫个不停。忽听得有人喊:“呵,赵子龙出来了!”细把戏们遂立时缄口,看“赵子龙”的武打。赵子龙出来必是《长坂坡》,无论大人、小孩都爱看。
赵子龙《长坂坡》是单骑救主,大概因为那“主”是一个小孩的缘故,被赵子龙揣在怀里,和细把戏们有着紧密的联系,故都将赵子龙视为心中的英雄。
我母亲从日本兵手里逃出来时,正是将三弟一直背在背上,所以我说母亲是赵子龙。
母亲听我说她是赵子龙时,却说:
“赵子龙一身是胆,我怎么能和他比?当时我还没被吓死?整颗心都是怦怦跳,要蹦出来了。”
我说:
“妈,我才不信你被吓住了呢!不过,你怎么只抓一把香灰呢?你应该抓起那个香炉,把日本鬼砸死!”
母亲说:
“你懂得什么?第一,你不知道香炉的重量,不知道一下能不能够抓起,如果一下没抓起,那就死定了;第二,即使你能抓起香炉,那也要时间,抓香炉要时间,举香炉要时间,就连砸去时,还有个时间,那种时间是连一丝一毫(老街人还没有分秒的概念)都耽误不得的,抢到那一丝丝时间,你就赢了,若是没抢到,那就只有输了,打仗叫兵贵神速,两人交手叫眼明手快……”
母亲说完,叹了一口气,说:“我还是太胆小,太胆小……”旋又像为她自己辩护说,“到底没见过这样的阵势——钢枪、刺刀,我背上还背着一个嫩毛毛……”
母亲似乎有些遗憾,有些后悔。她遗憾、后悔的究竟是什么呢?当时我没弄清。
这时白毛姨妈插话了,白毛姨妈说:
“姐啊,你讲那日本人进庙说的那句话你能听懂,他到底说的是句什么话呢?”
母亲说:
“那有什么好说的,反正他是讲了一句中国话。”
二十多岁的白毛姨妈竟带着撒娇的口气说:
“姐啊,你就讲一下嘛,讲给我听有什么关系?”
母亲仍然不肯说。白毛姨妈就抓着我母亲的手,使劲摇,说:
“姐啊,你讲一下嘛,让我也听听日本人是怎样说话的吗!他说出来的是不是人话?”
母亲这才说:
“他那时讲了一句中国话,我硬是听懂了。他说什么花姑娘,花姑娘……哪里有花姑娘?”
母亲讲到“花姑娘”时打了一下顿。
“那个该死的把你当作花姑娘哪?!哎哟姐,你真还是那么漂亮哩!”白毛姨妈笑起来。她这一笑,倒使得屋里的气氛轻松了许多。
母亲说:
“别乱讲,他是问我哪里有花姑娘?我说我不知道,要他到别处去找,反正我不是花姑娘。”
母亲说这话时竟有点羞涩,脸上还起了一阵红晕。
母亲虽然说的是日本人问她哪里有花姑娘,但我稍微懂事一点后,却断定是母亲将日本兵的话改了一下,其实日本兵说的是:“花姑娘的,大大的干活!”因为后面的一切,都是他要强奸母亲的举动。而母亲之所以把它改了,是因为即使没有被强奸,说出来也不好听。
白毛姨妈又问我;
“老二,你妈妈将你藏在那草丛里,你也吓得该死吧?”
我回答说:
“姨妈,你也藏到那草丛中去啰,去试一下啰,看你怕不怕啰?”
白毛姨妈又笑起来。
对世事似乎完全不知晓、对迫在眉睫的灾难更是毫无所料的白毛姨妈,就像个小孩一样天真。
见白毛姨妈在笑,我却非常认真地对母亲说:
“妈,我幸亏是跟着你,要是跟着父亲,可能就到不了姨妈这里了。”
我这么一说,母亲急了起来,她赶紧走到门口,望着外面,嘴里不停地说:“他们怎么还没到呢?他四爷和老大怎么还没来呢?”
白毛姨妈说:
“我那姐夫走得慢,挨得很,老大又只能陪着他慢慢走,姐你就放心吧,他们等一下就会到,不会有事的。”
白毛姨妈将我母亲拉进屋里,要我母亲坐下,正继续说着要我母亲放心的话时,父亲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