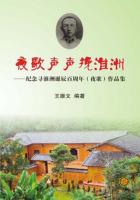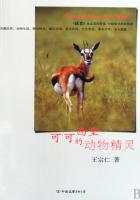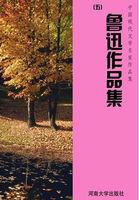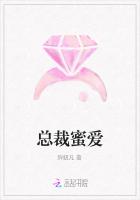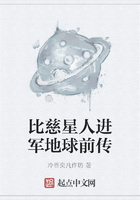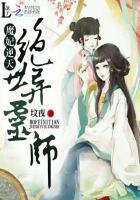再看看这外面的地,她们从上海来穿的都是圆口的方口的布鞋,那沙土已经淹到裤脚了,一踩下去,鞋里面全灌的是沙子。有的女生又说:“这怎么生活呢?”好多人又哭得不行。
另一方面,正因为风沙大,住地窝子倒有地窝子的好处,避风、保温。当然它是最简陋的房子,即使是翻新再建的地窝子,也还是往地下挖两米,上面再搭高一米,把大家自己砍的胡杨做梁和柱,把自己打的茅草、芦苇铺上,然后把泥土敷在屋顶上。放个木框就是天窗,因为很少下雨,也不需要塑料纸什么的糊窗子,就是留个通气采光的洞。
对女青年来说,在大田里劳动,可以和男青年一样承受饥饿和劳累,但是女性遇到的特殊困难却更加难以克服,连必需的卫生用品也是没有的。大概是到准许有人探亲以后,女青年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上海带卫生纸来,比如谁探亲了,大家就请她帮着带上一点。有时候还让家里寄,按印刷品寄过来。一位亲历者说起来,当时所谓的卫生巾用的都是布条条,里面装的草木灰。自己缝这么长的一个长条,两边搞个带子,如果是灰满了,把灰抖掉,灰不是吸水嘛,就这样用。所以每次一有这个情况,干活的时候,大腿都给磨破了,很难走路。
那时候在大田和工地都没厕所,就是到旁边的荒草堆里面,因为草长得高,外面看不见,在草堆里踢一踢,就这样解手。在戈壁滩,有一种小小的虫,叫它“草蜱子”,钻到皮肤下面以后,就会生出无数的小虫,把血都吸掉。曾经有个女青年,在草丛里解手,这个“草蜱子”就爬到她的下身里,她也不知道,忍着疼,到后来检查发现里面都是血,最后人就这样死掉了。
连队的人都跟着放映机走
上海青年在那个年代之所以感觉特别艰苦,也许因为他们要面对的,其实不仅仅是物质的问题,而且精神生活也非常贫乏。在基层连队,报纸杂志看不到,电影一个月放一次就不得了。一放电影,整个连队就沸腾了。
连队里如果通知要放电影或者演出队要来,那就像过节一样。放电影也好,演出队来也好,都是一件大事情。平常大家是看着太阳落山才下班,到这样的日子就会提前一些下班,收工回来洗洗。开演前一两个小时,大大小小的凳子都放好了,孩子们喊着演出队来啦,或者电影来啦,这些喊声会一直到正式演出或放映开始。
都是在露天,场地上本来就竖着两根杆子,然后拉上一块银幕,被风吹得鼓来鼓去,放电影用16毫米的小机子。那些年虽然翻来覆去看的没几部电影,但大家照样兴致高涨。
冬天就更别提了,晚上到零下二三十度,露天冷得厉害,再加上那时候的片子全是阶级斗争,情节又苦,看得大伙鼻涕眼泪都结冰了。
卫生队里头住的重病号也都非要出来看电影,有的看到一半不舒服了,赶快现场急救,或弄回去急救。有一次病号还在打着点滴,瓶子拿在手上来看电影,冻得那家伙差点死掉,马上送回去急救。还好,卫生队离电影场不算远。
在不少连队,最多一个月能放一次电影。到这个连队放过以后,再转到其他连队去放,那么这个连队的人会跟着电影放映机走,再去看第二遍,看第三遍,要走好多路。那时候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最远的连队的人,从五十里地开外提前奔过来。第二天一大早照样要出工,但没有谁因为这个觉得累。
除此之外,其他娱乐活动呢?尽管白天干活很苦很累,但是黄昏下班后,也没有洗澡的条件,就弄点凉水冲一冲,洗一洗,把自己的干净衣服一换,院子里很快就热闹得像上海“大世界”了。唱歌的、跳舞的、下棋的、拉胡琴的、拉手提琴的、吹笛子的都有,反正要把单调的日子想办法过得高兴起来。
沈黎明是1966年从上海进疆支边的,分到了北疆的柴窝堡林场。四十多年后,笔者在乌鲁木齐偶然遇见他,他已经退休,那天下午他正在闹市的街头吹奏笛子,另一位朋友拉琴。悠扬的乐曲传过几条街,一首接一首都是有关边疆或草原的老歌。行人会在他们面前驻足听一会儿,有的人在乐器盒里放下一点钱。沈黎明说:“我这个乐器是十六岁到新疆来了以后学的。那时候我们的文化生活相当朴素,很少有电影,没有电视,我们就自己丰富一下业余生活。因为笛子价格便宜,一块钱一支,所以我就学着吹了。”
连长程均友可以说是个深得上海青年认同的基层干部。他的想法是,得给他上海青年们组织娱乐活动,不能让他们闹情绪,不能让他们悲观,要根据年轻人的特点,把连队生活活跃起来。开篝火晚会时,他为了逗这些青年人,把老羊皮袄翻着穿,毛朝外,找个破毡帽戴上,也跑到人群里面跳,惹得大家哄哄大笑。他知道,一开心,大家就不总想着艰苦了。
帮我老婆也带个那东西来
喜好观察的老职工子弟何立云,后来又有了一些发现,像上海女青年在礼拜天穿着短裤就出门了,有的老职工和家属就捂着鼻子,看都不看,有的还臭骂她们。有个上海姑娘长得蛮漂亮,爱打扮,穿得比较新潮,人家就骂,骂得很难听,她就再也不打扮了。
开始这么一议论,甚至领导再一说,确实没人敢穿从上海带来的一些衣服了。不过说起来,上海青年实际上带去了很多新的东西,尤其是女青年穿着,对当地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后来有的确良了,首先是上海青年先有的确良衬衣。穿的确良衬衣就显得女孩子好看多了,还印了漂亮的小花;再一个呢,不像以前布的,的确良比较薄,合身。但是,一些老职工和家属就看不惯,尤其天热的时候,看见只穿件的确良的,就说是贴肉,透肉。
在农二师34团,和李小女同宿舍的有个女青年,她家庭条件很好,她的好衣服有好多件,但是不能穿出来,都放在纸盒子里,放到铺底下。结果老鼠在下面打洞,从那个箱子衣服中间打洞一直打到上面。等她把衣服打开看时,“哇”地大叫起来,发现每件衣服都不多不少六个洞,干脆没法穿了。她趴在那儿大哭一场。连其他人在旁边看了那些好衣服,也都觉得特别心疼。
李小女穿的第一件的确良衣服,是她父亲给寄来的一件淡米色的确良衬衫。当时她已经调到团部,是给团领导服务的公务员。那天早上起来,她穿着那件新衬衣,到了参谋长的房子里。参谋长看着她问:“姑娘,你穿的是什么?”李小女说:“这是的确良,新出来的。”当时的参谋长是战争年代过来的,算是长辈了,他说:“脱掉,快回去脱掉,不要穿,难看死了。”领导不让穿,她虽然很喜欢,就没穿了。其实,那时候上海的街上已经时兴的确良了,在兵团的上海人听说以后,也都想有这么一件。
有的老职工,由于多少年形成的观念,再加上政治运动那么一搞,特别看不惯上海女青年的衣着打扮,总能把她们的形象和“封资修”或者女特务联系起来。女青年穿裙子,穿短裤,穿个汗衫就出来了,老职工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不过老职工的子女正好相反,他们羡慕上海人,跟着上海人学,学上海话,学穿着打扮。
要说起来,那真是不该成为笑话的笑话了。上海青年慢慢地把的确良穿起来以后,出现了一个情况,天热,衣服比较透,那些上海的姑娘,都戴胸罩,一戴胸罩就很明显地衬出来。那时候老职工的家属还没有这些,老职工就气愤地说:“这叫啥东西嘛!”有的甚至骂这些上海丫头不要脸,骂得一文不值。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往往就是这种骂得凶的人,他听说有人要去上海探家了,又悄悄地找到人家说:“哎,你要回去吧,帮我老婆带一个那东西来。”他想让带的是什么?不单是的确良衬衣,还有那个都不能说出口的东西—胸罩。有的上海青年故意问:“呦,你们也要那个呀?”因为已经很熟悉了,他就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挺好的,让我老婆在家也穿。”总之明着骂是要骂,私下里带还是要带的。
还是何立云讲得实在:“原来我们那个地方的小伙子和姑娘,都很土的,不讲卫生,不注意洗脚洗脸。裤子衣服的话,可以说一两个月不洗,水也少,就是这样。他们上海人来了之后,看到他们搞得干干净净的,出去很好看。好看难看大家还是看得出来的,像我们这些人就跟着上海青年学,人的精神面貌也跟着好多了。”对何立云来说,这样子学习的效果是明显的,他后来娶了一位漂亮的上海姑娘。
生产建设兵团的这块土地,重新改造着上海青年;另一方面,被兵团改造多年的上海青年,也在用他们带来的观念和方式影响着原来的兵团人。若干年后,老职工讲到上海青年给塔里木带来了文明,他们还说过这样的笑话:“你们‘上海鸭子’来的时候,我们擦屁股不用纸的,因为你们擦屁股用纸,后来我们学你们的样子,擦屁股也用纸了;等我们刚学会了擦屁股用纸,你们又用纸擦嘴了。”
关于“上海鸭子”的说法,至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以说是褒义的。一开始是老职工形容上海人很能说,总在一起哇哇地说个不停,后来演变出对上海青年的夸赞,“上海鸭子呱呱叫”,就是好的意思。
趋势是挡不住的,渐渐地,上海那边上半年流行的服装,下半年在新疆的各地团场就流行了。因为后来可以探家了,有那么多人来往于上海与新疆之间,这些东西怎么能不传得很快呢。
那时候,许多团场老职工的孩子没见过城里的东西,甚至都没听说过。大人孩子都没见过火车,更不要说亲身坐一坐火车了。很多老职工一辈子就在农场,到许多年后他们的愿望就是从农场坐一次火车,去乌鲁木齐看一看。
关于这个,何立云又笑着说了一番实话:“上海青年开我们的玩笑,讽刺我们这些老职工的孩子,说我们要是去了上海,看到高楼大厦都会把帽子看掉。意思是傻得光顾仰头看,把帽子都看掉了。我们也相信,人家那里大马路,不停地跑汽车,楼房那么高,上海来的人我们也看到了,都清清爽爽、干干净净。那里不光是汽车了,还有火车、轮船,经济又发达,商店又繁华,你说这个东西,再笨的人,我们好坏还能分得清。”
连长程均友因为参加过征招工作队,是极少数到过上海的老职工。在他眼里,那时候光知道上海的东西好,想象中那就是工业化大城市。像衣服,上海的好;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上海的好;收音机,上海的好,那个年代在农场的职工谁能有个收音机呀。
到1966年,拿农一师来说,职工总数是十万七千多人,而这个师的上海青年最多,有四万六千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这么大的一股新生力量,简直把师部所在地阿克苏变成了一个初显繁华的“小上海”。
到了七八十年代,情况更明显,农一师所在的阿克苏市,不管河南人也好,甘肃人也好,都爱讲上海话,他们的孩子都讲上海话,你都听不出他们原来的老家是哪里。团场一到星期天,集市上好像满街都是上海人,满街全讲上海话,当地年轻人喜欢学上海话。所以在衣食住行方面,上海青年对当地的影响非常大。
从上海带来的各种家具或者家具样式,都成了引导潮流的稀罕物,大家都会跑来看,照样子画尺寸,量好,回去学着做。后来一个阶段,全团就像是木工厂,家家户户门口都在利用空闲时间打家具。这样一来,搞得本来强调艰苦朴素,“先生产、后生活”的兵团,很有点生活的气氛了。
兵团所在的那些地方以前有原始森林,林子里树棍子多,原来都是砍树棍子,回去在屋里栽四个桩子,把树棍子排上,上面铺草,这就是床,大部分家里都这样。后来上海人成家以后开始用家具了,有的是托运来的,有的是自己做,老职工家庭也跟他们学,床也会做了。当然,还是觉得床睡着更好。
包括在团场出现的沙发,刚开始也是上海青年自己做的。没有弹簧怎么办?就用汽车废轮胎,黑色内胎不是有弹性吗?把它截成一定宽度的一条条胶皮带;做个木框子,把胶皮带在两边一钉,上面用棉花一垫,用布一蒙,坐上去软乎乎的,沙发就成了。老职工一看,都说:“你们上海知青咋这么聪明,这洋玩意儿都能做出来!”沙发就这么很快兴起来。不管样子土不土,毕竟家里摆一对沙发,来个客人,请人家坐上去,主人挺有面子。
起初是个人自发地做家具,后来影响到公家也成规模地做了。团场专门成立副业队,把会这个工、那个工的人都集合起来,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有专职木工,开始给公家做家具,包括领导和机关的办公家具都得到升级换代。做多了还往外拉出去卖,变成了给团场带来额外收入的“第三产业”。
尽管有这些发展,但身处那遥远的地方,在上海青年的感觉中,边疆与内地,特别是与心中的上海相比,差距好像很大。那些年,他们的日子都是在盼望着过,盼什么时候吃的能不再紧缺,盼小家庭能添一样好东西。一时间在团场,谁要是骑辆新自行车,就会在土路上到处转转;谁要是戴了块手表,就总爱在人前把袖子撸撸;谁要是穿了双皮鞋,就会在别人面前把两脚跺跺……他们的支边生活就是这样在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