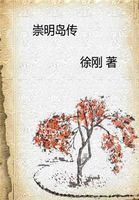五月的晚上,农村比城里忙啊!一出了县城,公路两旁便看不到信步的闲人,也听不到恋人的窃窃私语,甚至连蝈蝈的叫声,也不象在城里那样悠闲自得。一路上,除了拖拉机抢收抢运的轰隆声,就是嚓嚓收小麦的镰刀声。望着这一片繁忙的景象,脑子里又出现了我那粗壮健美的妻子。此刻,她也许在地里收小麦,或是往家运。结婚几年来,她又忙家务又拉孩子,里里外外靠她一个人担当。有时累熊了,趁我回家也埋怨几句:“咳!当初俺不如找个吃农村粮的,忙时有个帮手。”是啊,象我们,既比不上都在农村的夫妇方便,也比不了城里那些双职工。所以,尽快给妻子找个合适的工作,一时成了我思想上的一种压力。今天,这事总算办妥了。
到了家门口。腿还没骗下车子,正碰上妻子往外走。
“怎么,又来家宿旅馆呀!”妻子一手提着张镰,一手拿着块干粮嚼着说。见我往门里搬车子,又故意板起脸:“走走走,俺权当没有你这个人。”
我生气地把她一推说:“人家累得要命,你还开玩笑。”
“这些人整天泥里土里的都没有说个累字呢,夏收这么忙,别人都来家帮帮,你可倒好,一走就是一、两个月。”
没想到这么一句很平常的话,引出她这一套埋怨来。我极力想把这种紧张气氛平静下来,把那桩喜事告诉她。可还没等我开口,她又说:“今天晚上来家,这旅馆不能让你白住。”
我问:“干哈?”
“饭罩里的干粮还热,你先吃点。”她说。
我说我已经吃过饭了
她二话没说,从地上拾起一张镰刀递给我说:“走,跟我去收小麦。”
“天这么晚了,能看见?”我有点打休地说。
“今夜收不完,明天就影响到种。”她指指即将升出东山的月亮说:“有灯哪。”
来到麦地头,她把腰一卡,指着地里的十二行小麦说:“大秘书,来,你五行,我七行,比比谁先割到南头的。”
见她副做慢相,我轻蔑地白了她一眼说:“你前面割吧,这营生,我干过。”
开始几镰,我确实:占了优势,大有甩下她的气势。我直起腰,向妻子一笑说:“忽么样,还可以吧了”
“嘿,还行。不过,可要坚持到底。”
二百五十米长的地,真耐干。割了还不到二分之一,我就与妻子拉开了距离。只觉得膀酸手涨,浑身无力,脸上的汗水一个劲地往下流。手上的两个血泡也被镰柄挤破,痛得我直咬牙。
又坚持着割了一会,妻子已经接了过来。她不慌不忙,还是开始个样。直到割完最后一把,直起腰,望着我狼钡相笑着说:“你啊,别再逞能啦,干这个,你俩也不跟一个。”
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起了母亲和儿子,我问:“哎,咱娘和毛毛呢?”
她忽然咯咯地笑了起来说:“怎么,就才想起你娘和你郑宝贝儿子?不要紧,没有不了,明天他大姑就一起送回来啦。走吧!”
水银似的月光,透过窗I?的玻璃,洒在炕上,洒在妻子的脸上。我说:“素芝,告诉你一一件大喜事。印刷厂郝厂长答应给咱个合同工指标。”
“俺不稀罕,生就一身庄户骨头,进了城还不自在呢。”
“慢慢就习惯了。每月还有四十多元的工资。”
“四十元算什么。我预计着到年底,起码也得拿上二千元,比你这国家干部都强。”她的话语里始终透着一种豪气。
出乎我的意料,现在妻子对这件事的看法会与我不一致。我有点为难地劝说道:“我已经和人家订妥了,你要是不去……”
“那怕什么,咱不去有的是去的。”
“前几年你整天要我给你找临时工,现在叫你去又不去了。”名我埋怨道。
“你这个人,前几年咱村有这个样?现在大包干虽说累点,可干的舒心,收人大。”
我一时语塞,只觉得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却没有更充分的理由来说服她。停了一会,我又以商量的口气劝说道:“素芝,我看你先去干着,以后有机会转成正式的。”
她没有回声。
“行不行你倒说呀!”
仍没有回声。
不知什么时候她早已进入了香甜的梦乡。这时我才意识到,经过一天的劳累,她太疲劳了,实在不该再打扰她。
一觉醒来,阳光已射进玻璃窗。身边的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走了。我下炕去洗了把脸,准备做饭。一掀锅盖,见饭早已做好,正在站着纳闷,妻子提着镰刀走进来。
“你啊,真懒得够呛,就才起来?”
“那你为什么不早叫起我来。”我满有理由地说。
“哼!本想叫你,俺又舍不得。”她一边拾掇着饭一边说。
“吃完饭我帮你去割。”
“俺不用!昨晚上不过是叫你尝尝在家里这个滋味,别忘了。你当俺真叫你干。”说完,她嘻嘻地笑了起来。笑完又说:“出去干临时工这个事,我看就算了吧。你回去和郝厂长道个情,就说你老婆干不了。”
实在不愿意,我也没办法,只得依她。吃完饭,我拿起镰刀,要去割麦子,妻子上前一把夺下来,扔在地上说:“不用你,别干不多点活,城里耽误乡里耽误。只要回去把你的工作干好,别丢了人就行。有空常来家趟。”她说着,把自行车给我推出门去。
“书包里是二十个咸鸡蛋,带回去蒸蒸吃。”她说着,把书包挂在车把上。
我抬起头,深情地望着妻子,心中激起了感情的波涛。此时,我多么想抱住她给她一个甜甜的吻,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妻子是最不喜欢这种时髦的表面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