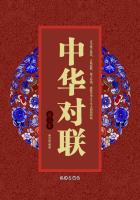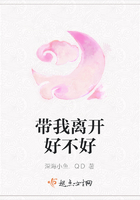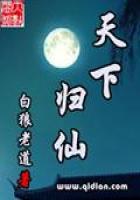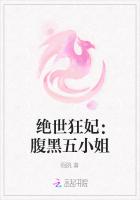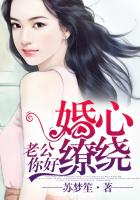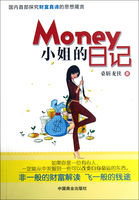不久前,我去交城县,在山中逗留了两天。这是我第一次进入交城山。我看到了清澈的流水,茂密的森林,山间的小路和小小的村庄。这一切幽雅的山林景色,使我流连忘返,激动异常,使我想起了许多如今已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就是三百年前交山农民起义军的故事。并且,说来也很自然,使我想起了傅山。
《山海经》里记载着:“悬瓮之山,晋水出焉。”悬瓮是形容晋水的汹涌之势,有如把水瓮推倒一般。这就是现在的晋祠。传说周成王桐叶封弟,封唐叔虞于晋水之旁,至今晋祠有唐叔虞祠。晋祠的圣母殿传说供奉的就是唐叔虞的母亲,周武王的妻子邑姜。周王朝在晋国制定了适合当地民情的新政策,叫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那时的晋中盆地,南人称之为大原,北人称之为大卤。就在傅山的文章中,依然称太原为大卤城。阎尔梅的诗《访傅青主于松庄》说:“狼孟沟南大卤平,汾川直扫太原城。”“大卤”二字使人想起一种面食的名字来,它就是大卤面。自古以来并州号称民性强悍,出产名马、名刀,还出产慷慨悲歌之士。而交城山就在悬瓮之山的西面百十里路,几乎是紧密相连,简直就是一座山。当年交城山农民起义军所占据的山林,据《交山平寇始末》说,东起太原,西至黄河,南至汾州、交城,北至保德、宁武关和芦芽山。这一片大山,纵横千馀里,万山盘错,莽莽苍苍,森林衔接,郁郁葱葱。《山海经》称之为“管涔之山”。
封建统治者对这一片大山厌恶极了,说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盗贼”的“渊薮”。交山农民起义是在明朝崇祯初年,其领袖名叫王才宏,攻州破县,曾经一度占领临县城,远近震恐。崇祯三年,闯王的起义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太原以西的这一片大山之中,一时树起了许多起义的大旗,犹如雨后春笋,真是风起云涌。如果要写出他们的山头和名姓,则需要一大段文字。
崇祯末年,李自成准备进入晋中,派了将领来同交山军联络。交山军立即同意归顺闯王,接受李自成的指挥。在李自成退出北京向南撤退的时候,交山军的一部分随李自成南下了。但是大部分的交山军没有南下,留在交城山中坚持斗争。这个时间,交山军里有人投降清兵,也有人假投降。清兵一来,强令剃发。于是所有不愿意剃发的农民就逃跑进了山,交山军反而不断扩大起来。人越来越多,仗越打越大。大同总兵姜,“部下多骁勇,久蓄异志,及见交山乱,思逞”①。这年冬天,姜起义,打的是明朝的旗号。姜派姜建雄南来与交山军联络,交山军决定接受姜建雄的指挥。他们四面出击,占领了交城、文水、清源、徐沟、太谷、汾阳、离石、静乐、岢岚等地。当时只有太原和榆次尚未攻占,不过交山军也已经任命了太原知府和榆次知县。后来多尔衮亲自出战,消灭了姜。多尔衮派两位亲王,一个是敬谨亲王博洛,一个是端重亲王尼堪,直驱太原,与正在进军太原的交山军作战。清兵南下,把交山军看做是姜的残部,待姜建雄战死汾阳之后,他们便以为大获全胜。其实,交山军又退入了深山。顺治十六年,石楼曹青山暴动,投奔了交山军,交山军推举曹青山做了交山军的领袖。这中间大小战斗打了许多,有过许多胜利,也有过许多失败。这个时候坚持战斗的乃是交山军的第二代了。父亲战死,儿子接班;爷爷牺牲,孙子上阵。到康熙七年赵吉士做了交城县知县,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到康熙十年才把交山军最后镇压下去。从崇祯初年到康熙十年,交山农民军前仆后继坚持斗争,时间长达四十馀年。其间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啊!
傅山虽然没有参加交山军,但是,要说他同交山军没有关系,却不对。这证据就是傅山的有名的文章《汾二子传》。傅山曾经把这篇文章抄写过许多份,分赠他的朋友。至今山西省博物馆还保存着他的《汾二子传》的手迹。那书法清俊遒劲,大气凛然。文章也好,读之令人肃然起敬。邓散木说傅青主小楷极精,这《汾二子传》就是傅山小楷的精品。汾二子即汾州(今汾阳)的两位先生,一位名叫薛宗周,字伯文;一位名叫王如金,字子坚。他们两位都是傅山在太原三立书院的同学。傅山同薛宗周最要好,崇祯九年他们一起上京,为平反袁继咸的冤案奔走呼号,同阉党爪牙做殊死的斗争。那次斗争终于获得胜利,可以称作古代历史上的一次学生运动。后来马世奇写了一篇《山右二义士传》,歌颂这次运动。二义士就是傅山和薛宗周。薛、王二人在姜起义之后,见交山军打的是明朝的旗号,他们便立刻参加了。他们带领交山军向太原进军,打到晋祠,遇上了博洛带的清兵。博洛在赤桥,薛、王在晋祠堡。一个小小的晋祠堡,堂堂的亲王率领大军竟然攻了五天才把它攻下来。战斗失利,他们两位都牺牲在晋祠城头。傅山在叙完他们的事迹以后写道:“二子果能先我赴义。”“往者不悔,来者不拒,何哉?余乃今愧二子。”这篇文章作于何时,也值得一提。文中傅山写道:“及袁先生三立讲堂,二子咸在,至今盖十五六年矣。”从崇祯九年,数十五年,正是交山军在晋祠作战的那一年,即顺治六年。晋祠战斗发生在顺治六年五月间。傅山的文章大概就是这一年的夏秋之间写成的。当时传说薛宗周没有死,傅山写道:“死耶未也,彼其无论矣。”意思就是:薛子是死是没死,先不要管,我决心写《汾二子传》。可见傅山是急切地要给二子作传,其心情之激动可以想见。又过了十五年,傅山写道:“自袁师倡导,太原晋士咸勉励。文章风节,因时取济。忽忽三十年,风景不殊,师友云亡。忆昔从游之盛,邈不可得。余与枫仲,穷愁著书,沉浮人间。电光泡影,后岁知几何,而谨以诗文自见。吾两人有愧于袁师。”②这里“师友云亡”,师是袁继咸,友里自然就包括薛、王二子。三十年后,傅山依然怀念薛、王二子,言语深沉,感人至深。这就是傅山同交山军的密切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三十年后,傅山依然在怀念交山军的英雄。
当我在交城山里漫步的时候,我想寻找裴家马坊,没有找到。有人告诉我,那可能就是方山县的马坊村。从老方山看东北,相距十来里路,本是古代屯田的处所。我想到那里去寻找“孟楼”的遗址,以便凭吊古代英雄们的遗踪。据说孟楼高十几丈,可望数十里。当年起义者战败自焚的时候,烧掉了“孟楼”。那为首的起义军将领,名叫裴奇芬,是个明朝的武举。当时的举人秀才,不分文武,莫不踊跃投身革命,他们甚至不计成败利钝。傅山的《汾二子传》里说,薛宗周见有人犹豫动摇,严厉地说:“极知事不无利钝,但见我明旗号,尚观望,非夫也!”正是这位“高视迂步,不苟言笑”的薛宗周,在晋祠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战斗。后来战斗失败,当晋祠南城楼起火时,有人看见他投身烈焰中,壮烈牺牲了。这都是一些平时非常骄傲的文人,这就正是他们的所谓“崖岸”。而跟随他们一起战斗,最后一起牺牲的,都是淳朴憨厚、不识字而有觉悟的山村农民。
我来到一个小小的山村。它简直就是一座天然的城堡。古人讲究风水,所居要求背风,向阳,汲水较近而没有水患,不过如此而已。这个村子,高高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咀上,向阳却不背风,没有水患,汲水却远。村后没路,村前唯一进出的路,崎岖难登,就是毛驴,驮着东西向上爬,也是很困难的。我看见毛驴就想起了“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叫”这首民歌,仿佛交城山里只有毛驴似的。然而古书上写着,交城山里出产名马,其马高大善走,古代用作战马。清兵入关以后,严禁山民养马,实际是害怕。据说元朝统治者害怕菜刀,许多家庭共用一把菜刀。而清朝统治者害怕马,严禁养马。没想到这些尚武的民族,一旦成了统治者,心理变化很大,胆子很小,脆弱之极。我脚下的大石块,细雨过后,焕然一新,呈现着各种奇妙的花纹。我抬头望着高处的庐舍,想象着古代的战斗,也许我面前的大石板上,就曾经洒过交山军英雄们的鲜血,他们的妻女被屠杀,他们后来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当他们倒下去的时候,山石也会震恐,发出金石之声。他们为了什么?为了生存,为了自由。他们生活在一个乱世,一个个性正在觉醒的乱世。
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天天都有谣言,处处都有怪事,人心浮动,天下大乱。正是在这时候,个性开始觉醒。傅山在《学解》一文中说:“学本义觉,而学之鄙者无觉。盖觉以见而觉,而世儒之学无见……所谓先觉者,乃孟子称伊尹为先觉。其言曰,予天民之先觉者,将以斯道觉斯民也。乐尧舜之道也,而就汤伐夏以救民,则其觉也。觉桀之当诛,觉汤之可佐。尧舜汤者,杀桀乃所以为尧舜汤也。是觉者,谁能效之。”③
觉就是觉悟,见就是见识。庸人们没有任何见识,甚至害怕别人有一点点见识,怎么能希望他们有觉悟的一天呢?傅山指出,真正的觉悟就是像伊尹那样的觉悟,觉悟到夏桀当诛,以这种革命的道理唤起民众,并以此达到杀桀而救民。在古代社会里,凡识字的人都知道“汤武革命”的典故。傅山这些话,直截了当鼓吹革命,这是再明白易晓也没有了。正是在那个大动荡的时代,先觉者以个性独特相标榜。在《汾二子传》中,傅山说:“余先与薛子游,畏其卓荦,喜西河有斯人。”卓荦特达,用现代语说就是卓越独特。傅山对薛宗周的个性,是又敬畏又喜爱,高兴在汾阳出了特殊的人才。汾阳的缙绅和士人都喜欢做买卖。薛宗周是当年三立书院的高才生,“薛峻崖岸,肩棱棱如削,不苟言笑,高视迂步,而佣奴汾之人”。而王如金“短小负气,行多不掩言,而亦佣奴汾之人”,“二子者独喜交游豁达,耻琐碎盐米计”。傅山有《悼子坚》诗二首:“王子狂而疏,行真不掩言。”“醉眼乜西河,黄茆连青天。”④醉眼二句,狂态可掬,这就是三百年前的革命英雄。人们只知道一定的时代产生了一定的个性,这无疑是对的。但反过来说也一样是对的:独特的个性,形成了独特的时代。傅山的个性也是非常独特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充分理解并且热情歌颂这些具有独特个性的英雄。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当年的战场。这就是米家庄西面的夹谷地带。《交山平寇始末》记载着这次战斗。顺治五年九月底,“右营守备李进忠率兵五百,运粮千石入山。王显明、王国光、张继成、齐三夏等闻之,伏众数千于米家庄西十里野则河山下石锁关侧。进忠兵至,贼断其前后,集鸟枪乘高夹打,自辰至午,进忠死,五百兵无得脱者。报至,举军丧气”。这是一次大胜利,并且是歼灭战。
我站在河边,察看这弯曲狭长的河谷。如今的情形同三百年前大不一样了。修筑了平坦宽阔的汽车路,架起了高压电线,还有一些水泵房之类。汽路上不时有汽车和拖拉机走过。汽车的喇叭像发脾气似地叫着,相比之下,拖拉机们温柔多了。我想像三百年前的那次战斗,土枪土炮不停地怒吼,一定激烈之极。交山军的将士们使用的主要是鸟枪。这一带大山之中,出煤、出铁,有的是硝磺和柳木炭,不愁他们造不出鸟枪来。然而我忽然想起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三百年前的交山军就已经使用着鸟枪,而直到抗日战争初期,民兵所使用的还主要是鸟枪。这三百年,人们干什么去了?明末清初这个时间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那些作品的水平,以及他们的思想境界,比起当时欧洲的名家,毫无逊色。交山军手中的武器也不比当时欧洲人的武器落后。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这个想法使我感到气闷。
我在这河边同一位老人谈过话。他有六十多岁了,拉着一匹小骡子来河边饮水。骡子同马相比,价钱低,能干活,好喂养。但是说实话,我不喜欢骡子。我希望看到交城山里的战马,枣红色的,高高的,又踢又咬,总是骄傲地仰着头。我赶过去同那老人说话,他不住地端详我,好像他家丢了一把斧子至今还没有找到似的。谈话中间,我问他交山军的事情,老人显出茫然的样子,后来说道:“呵,听说过。听老年人们道古时说过,前清时候,出过一个葫芦王。后来也常闹土匪。”
他的话使我非常惊奇。转念一想,这用不着惊奇。我也号称是个读书人,却不能充分理解傅山的文章,总觉得觚棱难近。可见三百年前那些包括傅山在内的思想家们的伟大的思想成果,对我们已经是相当地隔膜了。同样道理,交山军英雄们的思想性格,对于我们已经是很难理解了。从现象上看,交山军的英雄们,仅仅是为了抵制剃发,竟然走上流血的道路。傅山也一样,他为了不剃发,当了道士。清朝皇帝请他出来做官,他拒绝,做官不还是要剃发吗?他愿意自食其力,过一种清贫的生活。他研究先秦古籍,发掘战国时代的思想财富。傅山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孔甲抱秦恨,慨然死陈王。”“淡静陶处士,乃有咏荆卿。”于是我们知道了,交山军的斗争是为了反对暴政。
我在走出交城山的时候,默默地想着,我觉得只有明清之际的人能够读懂战国人的著作。这两个时代非常相似,人们的思想情绪也非常相似。我指的不是七国纷争,而是社会的大动荡和士民的大觉醒。所不同的是战国秦楚之际的士民,经过长期的流血斗争终于胜利了;而明清之际觉醒的士民,经过长期的流血斗争却失败了。暴政胜利了,庸俗胜利了;自由失败了,个性失败了。觉醒的士民被暴政压下去,他们的血肉变成了尘土,他们的铮铮铁骨变成了灰烬。所以交山军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出英雄的悲剧。经过这一场巨大的波涛之后,傅山悲叹道:
明月清风遗恨在,千秋万祀属谁知。
当我离开交城山的时候,我忽然产生一些遐想:现在的关帝山或许就是《山海经》里的少阳山,现在的文峪河或许就是《山海经》里的酸水。酸水!多么令人难堪的名字啊!它不停地奔流着,呜咽着,述说着我们中华民族无尽的辛酸。
1984年5月于东花园
注①:见《交山平寇始末》。
注②:见《霜红龛集》卷十四《叙枫林一枝》。
注③:见《霜红龛集》卷十四《学解》。
注④:见《霜红龛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