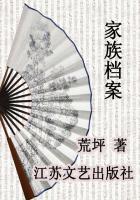桃花峡里有太多的传说。
这些传说煽动着人们的神思遐想,也在或深或浅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说不清是哪年哪月的哪一天,有一位年轻学子,骑着一头怀孕的骒骡进京赶考。走入桃花峡后,忽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学子知道这样的雨是会引起山洪暴发的,心里就很害怕。偏偏在这个急死人的时候,骒骡却是要产驹了,像个要生孩子的孕妇,表现得十分难受和慌乱,怎么也不肯前行。学子既怕洪水袭来,又怕骒骡产驹耽搁时间。他无奈得很,仰头看见自己正在大佛弯的大佛像下,赶忙磕头祷告:大佛爷爷保佑、大佛爷爷保佑,桃花峡不发水,骡子不下驹!
该是大佛显灵,果然云开日出,万事大吉。
学子骑着骒骡进京赶考去了。
只是从此后,下再大的雨,桃花峡也没发过洪水,骒骡也就不再产驹了。
人们把不生养的男女称为骡子。
斌文结婚快三年了,媳妇的肚子还没有动静。人们就在背地里说老霍家是骡子家。骡子家这顶帽子一扣,就很少有人再来请俏孥儿去帮忙了,甚至连他家的席器也租不出去了;喜钱、喜烟、喜糖、喜茶,还有席器的租金什么的明显少了,多年积攒起来的人气好像也在一天天飘散。俏孥儿倒不是太在乎这些,霍把式却是受不了。忽一日,他在他家院门上挂出一块硬纸牌子来,上书:接骨收费,小孩儿五块,大人十块,祖传跌打损伤药膏,视用量取费……牌子一挂出来就在下白彪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人们说,霍把式那两下子也敢挂牌收费,这是老家雀落在树梢上——鸟不大,端得架子还不小。人们还说:骡子家想钱想疯了,乡里乡亲的开口闭口就是个收钱,这是骡子不生养——把事往“绝”里做咧。俏孥儿能受得了穷,却是受不了乡亲们说三道四的,她本来就不同意霍把式这么做,只是理解着霍把式,知道霍把式肚子里有气,想让他发泄发泄,所以就没有硬性反对。现在,被乡亲们这么人前背后地指画,她就觉得实在是不能再迁就霍把式了。她把那牌子摘下来,拿回窑洞,撕成条塞进了火塘。霍把式说:“你这老婆家是怎了?也不和我商量就把牌子烧了火。”
俏孥儿说:“原来就不同意你弄这,你牛头八怪非得要弄,现在倒好,惹了闲几淡话一大堆,你的耳朵就不烧?”
霍把式道:“我有这本事,我赚这钱怎啦?天经地义。我祖传的本事不是为了赚钱,难道是为人民服务的?说我霍继业骡子家,躲闪着我家,我看他们折了腿胳膊还躲闪不?找上门来,老子就收钱,不收白不收!他们要说我霍继业的闲几淡话,让他们说去;好人说我,大吉大利,坏人说我,得病就死!”
俏孥儿说:“算了吧你,挂牌牌没人来,不挂牌牌也没几个人来;就是你真给人家接了骨,人家也都感激你咧,还不是感激你不收钱?你这一收钱,把人情也丢了。”
霍把式说:“我知道。我只是觉得我帮了他们那么多,他们还不说帮我,还要说咱家的闲话,我不服气咧。再说,国家现在讲经济社会、讲脱贫致富,我谋出个路路赚几个钱,也是正当的。可这些人们还是老观念,这不,一说收钱,狗日的们胳膊腿也不折了?”
俏孥儿禁不住一笑:“你这人说话也不和肚皮商量商量,斌文媳妇生不下孩子的事,别人能帮得上忙?你挂牌牌收钱是合理不合法咧!知道不知道?你有行医执照咧、有国家允许的手续咧?不用钱没赚到,还给人家罚了款。打不住狐狸,倒惹得一身骚。”
唉!霍把式叹了一声,不再和俏孥儿强调什么。
骡子家这三个字给霍家带来了太多的压力和烦恼,这三个字实在是太刺激、太恶毒!霍把式出来进去的,就像泄了底气,没精打采,抬不起头来。生生硬硬的风言风语不时像夏日的冰雹敲打着霍把式老两口的心,也把他们想要抱孙子的梦想一天天敲得破碎不堪。
斌文在煤窑上挖煤,因为媳妇没生下孩子,他便进一步成为了煤汉子们开玩笑的对象。
早晨一见面就会被人问:“夜里黑间闹来没?是不是种子没撒对地方咧?”又有人说:“你老婆那是疙瘩旱地还是盐碱地,怎不见出苗?”
斌文埋头干活,不作声儿。但是,斌文无论在什么场合,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和媳妇不能生孩子。他这个老实人甚至在霍把式老两口的提示下编了瞎话说,媳妇是能怀上孩子的,自己也没什么问题,只是一怀上就流产,医生说是习惯性流产,再等一两年,媳妇养好了身体就能生的。其实,他自己清楚,媳妇进门以来根本就没有过妊娠反应。只是这样一个借口,却就给了人们编排故事的线索。故事是从黑矿长开的黑煤窑上传出来的。说斌文家媳妇一怀上孩子就流产,找山里的土郎中看了,郎中说这是需要补胎的。斌文问怎么补?郎中说进城里医院花俩钱儿看看去吧。于是,斌文就带着媳妇进了汾阳县城。走在汾阳城的大街上,见路边有个修理自行车的摊位,那摊位旁边立了一块牌子,牌子上面竖写了“补胎”两个大字。斌文是认识这两个字的,斌文高兴地认为这里就能补胎,或许还便宜,何必去医院花大价钱呢?这便带着媳妇来到摊位前问那正在补胎的师傅:“补胎多少钱?”
师傅头也没抬,说:“这要看眼眼大小。”
师傅指的是车胎破损的“眼眼”大小,斌文却理解错了。
斌文为难了半天,然后对媳妇说:“脱吧、脱吧,不脱了,怎能看见眼眼大小?”
媳妇觉得在大街上人多,不肯脱。
斌文说:“为了看病,为了霍家的后代,不能管那些了。”
媳妇也是这样想的,就把裤子脱了,紧并着光溜溜的两腿站在那里不敢动弹。
修车的师傅一抬头,惊得目瞪口呆,一时说不上话来。
斌文却误解了人家的表现,对媳妇说:“蹲下、蹲下、不蹲下怎能看见眼眼大小?”
这样的笑话传得很快,霍把式都听说啦。霍把式气不打一处来,却是怎么也想不明白:老霍家怎么就成了骡子家啦?老霍家怎么就成了骡子家啦!他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的。虽然他从来没有承认他家祖上是强盗沟的,但是遭遇这种事情,他还是要扪心自问的:难道是祖上在强盗沟造了孽,遭了隔世的报应?
儿媳妇姓任。这里给女孩子取名字喜欢带“花”“月”“草”一类的字。儿媳妇出生在三十里桃花峡山桃花盛开的季节,她的老父亲走过三十里桃花峡的时候,想起了关于樵夫白彪和桃花仙女的传说,于是给她取名为桃花。桃花家可是三代贫农,勤劳肯干的好人家啊。桃花进了霍家的门后,从来没有跟公婆红过脸,公婆说个什么,她都会像圣旨一样对待。对丈夫斌文、对小叔子斌武也是知冷知热的,对街坊邻居更是情情理理。
正像当年霍把式娶回了城里媳妇一样,谁不说霍家的桃花媳妇好呢!
一早起来就打扫院子,还喂猪、喂鸡、洗衣、做饭。不过两年多的光景,霍家的生活就变得滋润甜蜜起来。霍家田地里的庄禾按时播种、按时耕耘、按时按季收成;霍家的院子里,猪圈里猪肥,鸡窝里蛋多。又有斌文按月从煤窑上拿现钱回来,这日子还有个过不好的?逢年过节,霍家杀猪宰羊还能炖鸡肉吃。下白彪岭除了相里彦章家,还有几家的日子能和老霍家比?可这老天爷就是不让你事事如意,这样好的儿媳妇却怎么就没能给霍家生出个孙孙来?
俏孥儿说:“你家几代单传,香火本来就不旺,怕是这斌文身体上有甚的遗传病呢吧?”
霍把式十分不高兴俏孥儿这样说:“能有甚病、能有甚病?单传也传到了我霍继业这里,不是生了两个嗣儿?我还怕是你家有问题咧,你妈你大不生养才抱养了你!”
俏孥儿被霍把式的话呛出了火气:“你口里干净些!我妈大都躺在墓子里啦,还招你惹你啦?说话怎这来地损咧!老两口不生养怎的,有问题也涉及不到你霍家。我是抱养的,要有问题也是我有问题。我有问题?我有问题不是给你生了俩嗣儿一孥儿,你个没良心的!能做损事还不说损话咧!”
俏孥儿一发火儿,霍把式便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瘪了。他扯了扯俏孥儿的衣裳:“算了算了,你还不知道我霍继业,一着急,说话就没有个分寸。”
俏孥儿赌气一扭身子:“做甚做你的去,我们招惹不起你!”
霍把式换了个笑脸:“嘿嘿、嘿嘿,哥哥唤你个妹子还不行?妹子、俏孥儿妹子,快不用火了!”
俏孥儿忍不住笑出了声儿,拍了霍把式一巴掌:“老也老了,没皮没脸。”
霍把式见俏孥儿转怒为喜,又说:“你、你过去问问桃花,怎回事咧,是种种不行还是地地里不长苗苗?”
俏孥儿说:“这可怎问咧嘛?”
霍把式又是没好气地两眼一瞪:“你平时说话口上和抹了油一样,现在怎就不会问了?”
俏孥儿又是有点生气地说:“你瞪甚的眼?就知道促使我,有本事你自家去问!”霍把式心地好,知道疼媳妇。从结婚到现在始终呵护着俏孥儿,舍不得伤俏孥儿的心。即使是在说话上,只要俏孥儿一逞强,他就退却、回避、忍让。现在,他感觉到又惹俏孥儿生气了,这便放缓语气说:“我也是心里急咧,狗日的们骡子家、骡子家地叫得我都想把脸揣进裤裆里咧!”
知夫莫若妻。俏孥儿是真正能够理解霍把式的,也是真正能够为霍把式着想的,她低着头想了想,说:“问就问吧,自家儿媳妇有甚不能问的。”
婆婆俏孥儿想好了要问媳妇桃花这么几个问题,一是两口子晚上过不过性生活?如果过,为什么不生孩子?二是如果说两口子晚上不过性生活,那么是谁的身体有毛病?或者是两口子面和心不和长期生气、不钻一个被窝?三是如果两口子能够进行正常的性生活,那又为什么不怀孕、不生孩儿?俏孥儿想是想好了,但不能按照想好了的直白地去问。她嘴儿巧,很会说话,随便找了个借口就进了儿媳妇的窑洞。
婆媳俩坐在炕沿上亲亲热热地说了些家常话,婆婆不露神色,很容易就把话题扯到了想要问的内容上。
婆婆关切地问:“桃花啊,你们两口子黑间就不?”
媳妇也很聪明,知道婆婆在问什么,低声说:“不不。”
婆婆:“不不嘛不?”
媳妇:“不不还不,要不就更不啦。”
婆婆已经问清楚了,媳妇也已经说明白了。
婆媳俩各自沉默半天。
最后,婆婆长长叹了一声,说:“再蒸一笼莲花馍馍吧,妈和你再去一回孩儿窝。”
媳妇听话地点了点头。
桃花峡里有一处地方,山体石壁的上部是直直的立面,下部则成半圆的球体状,圆滚滚的,其表面不仅光滑,而且润泽,就似弥勒佛的肚腹。美妙的是,在半圆的球体上自然形成两个石洞,一大一小。老人们叫它“孩儿窝”。人们相信老人们说的,把石子扔进大石洞里,求官得官、求财得财;把石子扔进小石洞里,求子得子,求女得女,灵验得很!所以这里的香火一直都很旺盛,常有人跪在那里烧香、上供,然后往那一大一小的石洞里投石子,求官或者求子嗣。其实,婆婆俏孥儿已多次和儿媳妇桃花带着诸多供品来过这里。儿媳妇桃花在每次虔诚地祷告后,就按照婆婆的指点,往那“孩儿窝”里扔石子,每次都扔得很准,却是没有老人们说的那么灵验,身体好歹没有妊娠反应。
难道是斌文有问题?就把斌文带去,斌文却是笨得厉害,很少能把石子扔进“孩儿窝”。好容易有一次扔进去了,那石子却又蹦了出来。
霍把式愤愤不平地想,为什么他家的日子就总是这么坎坎坷坷,又为什么别人家的光景就总是这么顺风顺水?老天不公啊!娶妻生子,天经地义合理合法水到渠成的事情,怎么到了老霍家这里就成了无法攻克的大难题、彪岭关了?霍把式在没办法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来找相里彦章。
看看人家相里彦章,真是人比人气煞个人!相里彦章的儿子们孝顺,他们给相里彦章买了影碟机。相里彦章现在不用收音机听晋剧了,他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图像听戏。听够了、看够了,就去石料场走走看看,或者悠闲地推推小石磨,碾些米面什么的,要不就接着书写些东西、再喝茶、再看戏,心情舒畅的时候还自己哼唱一阵儿晋剧片段。霍把式羡慕得很,因为羡慕,心里经常觉得酸楚。霍把式说:“关了关了吧,我要和你说正事情咧,心里难受,不能听着、看着戏说,还是坐你的八仙桌好说话。”
相里彦章就把里间的门带上,留老伴一个人在那里欣赏,自己和霍把式分别坐在了外间的八仙桌两边。
相里彦章说:“别人说你家是骡子家,你家就真是骡子家啦?我看你还是瞎子拉二胡——自顾自(吱咕吱)吧。自家过自家的日子,由他们说去。”
霍把式说:“我这不是自家也顾不了自家才来找你的?我也管不住人家们说三道四。可这都快三年啦还没个动静,给谁谁不心焦咧!咱这年纪也一天天一年年地大啦。”
相里彦章说:“不行就抱养上一个,说不定真就能引逗的生出一嗣儿半孥儿来。”
霍把式说:“我也想过这事情,抱养个孥子吧,她将来是要嫁人的;嫁出去的孥儿,泼出去的水,那是给别人家养活咧。抱养个侯嗣儿吧,皮亲肉不亲,不连骨头不连筋,将来是个怎还不一定。咱实在是不想弄这拾的孩儿做满月的事情。”
相里彦章:“那可怎咧,这忙我也帮不了。”相里彦章这样说着又问:“孩儿窝去了没?”
霍把式把斌文、斌文媳妇一次次去孩儿窝求子的情况如实汇报给相里彦章。相里彦章思索着,说:“难道是斌文的问题?怎么就连个石子也扔不准?不应该、不应该呀!”
霍把式说:“你可说咧,我霍继业怎就生了这么个球没液!”
相里彦章说:“怕还就是咧、就是咧。”
“就是甚呀?”霍把式没听明白。
“就是个球没液!你是不是没听懂我说的话?”
霍把式摇着头。
相里彦章一边习惯性地蘸着茶水在八仙桌上写字,一边压低了声音说话。霍把式见相里彦章在八仙桌上写字,便起身凑过来,一边辨认着桌子上的字,一边侧耳聆听着相里彦章一本正经的诠释。
“球没液”在汾阳是个贬损人的话。指人没出息,窝囊,成不了大事情。但本意却有两层,没有多少人知道。汾阳人发音,液和沿相同。相里彦章说,球没沿就是没有沿儿,为什么没有沿儿,那是因为包皮过长,包住了看不见。他陪房时观察过了,斌文不是没沿儿;从字面上讲,这个液字,可就是没液体啦,液体是什么?就是精液,没有精液还能生孩儿?
“哎呀、哎呀,”霍把式道,“老哥你不这样说,我还真不知道,球没液这损人的话可是把人损透啦!看我这不积德的口,刚才把我斌文说的!可斌文能是个那?”
“说不来、说不来,”相里彦章从桌子下取了抹布擦着桌子,“再说这没有也不是就什么也没有,有可能是量少,也有可能是成活不了,这是个男人病,得到城里的医院诊断咧。”
这样的谈话过了没几天,霍把式悄悄地把一张诊断单给相里彦章看,果然和相里彦章说的差不多。霍把式把单子装回贴身的衣兜,说:“老哥,这事可就你一人知道,我儿媳妇也没敢让知道咧。唉,我嗣儿精精壮壮的怎就是个球没液!”
“不能治?开药了没?”
“开了,医生说不敢保证,吃着药看吧。”
“能治就不怕,两年不开怀,说不定开怀就生两三个咧!”
“老哥说话准,我信,生他个双黄蛋!”
“儿媳妇是鸡呀,还双黄蛋!”
“一着急就糊涂,口误、口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