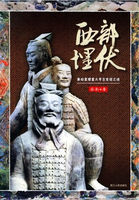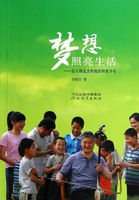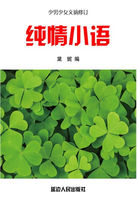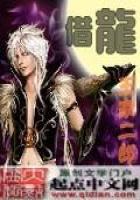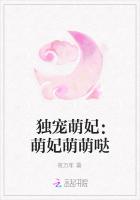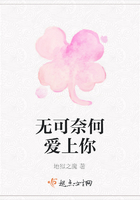四十多年前,我在湘潭市四中读到初中三年级,教语文的老师忽然换了。是外校调来的,叫欧阳觉悟。
这名字叫人觉得挺神,因为写《醉翁亭记》的那位老先生叫欧阳修,我没事时读过这篇文章,所有的印象就是欧阳修很爱喝酒,整天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这位欧阳觉悟老师是不是醉翁的后裔?是不是也爱喝酒?或者也喜欢写诗?有没有一把花白的胡子?
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一个秋雨潇潇的早晨。
第一节课是语文。
往常预备铃响了,教室里依然一片乱哄哄,这回却意外,安静得像是一泓不动声色的湖水,所有的目光都交织在教室的门口,严严实实地布下张网。
窗外的雨声响得很急很密,斜曳的雨点击打在玻璃窗上,叮叮当当,如鸣佩环。
他终于出现在教室门口。
高高瘦瘦的个子,背稍稍有点弯,脸相清癯,但刮得很干净,年纪在半百上下。我们觉得很遗憾:他没有一把飘在胸前的胡子。
我们的教室在三楼,他是撑着一把木弯柄的大黑布伞,一直踱到这里来的,伞沿滴着水。他小心地收好伞,把伞柄挂在讲台边上,很慈祥地看了我们一阵。这使我们觉得好笑,伞怎么到这时候才收呢,走廊上又没有雨。
他的半边身子全淋湿了,头发上也有水滴。他的头发是往后捋的,额角突得很高,颧骨也突得很高。
谁忍不住笑了一声,大家仿佛被感染了,一齐笑了起来。他也微微一笑,用手在下巴上捋了捋,那里其实没有一根胡子,只有一块闪光的青色。我们又笑了起来。
他清了清嗓子,说:“因学校没有房子,我家借住在学校后门边的一座农舍里,旁边有一个荷塘。在塘边走过时,想起欧阳公——就是宋朝的大文豪欧阳修,他写过一首词,里面有一句:‘雨声滴碎荷声’,实在是写得妙,便听了一阵,所以来迟了一会儿。下了课,你们去听听,真是韵味深长。”
他的脸上慢慢地现出一种虔诚,他很坦率地说出迟到的原因,一点也不怕我们小看他。我们感到欧阳老师很亲切。
下课铃响了,我们真的跑到那荷塘边,想听一听“雨声滴碎荷声”的妙处,我们瞪大眼睛,尖起耳朵,终究没有领会到那种说不清的东西。但那空蒙的雨色、碧澄澄的荷色,一直泻入了我们的心底。
他的语文课确实教得不同一般,虽然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湘潭口音,但他善于创造出一个教学的氛围,让我们身临其境,忘记一切。他讲鲁迅的《孔乙己》,说到孔乙己把茴香豆分给几个孩子吃,孩子吃了,仍然把眼睛盯在那个盛豆子的小碟子上,孔乙己忙伸开五指,罩住碟子,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时,欧阳老师便叉开五指,使劲罩在扁扁的铁皮粉笔盒上,眼睛盯着手指,一边摇着头,一边很亲切地说着这些话。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他手背上凸起蚯蚓般的筋络,是青紫色的;手指枯涩而瘦长,仿佛刹那间会“嘣”地折断,就无端地生发出对孔乙己,不,是对他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
他借居在一座土墙茅顶的农舍里,两间卧室,一个厨房,家里一共七口人,师母没有工作,另加五个还在读书的孩子。屋里没有什么摆设,倒有一张老式的书桌和一个大书柜,书柜里放着许多古典文学作品。
但他很快活。常在下午自由活动的时间里,把我们几个语文成绩好的学生叫到他家里,给每人沏上一杯茶,让我们坐在他身边,随手从书柜里取出一本唐诗或是宋词的集子,翻开来,很有韵味地吟哦,脑袋得意地画着圆弧,然后再逐字逐句地讲解。
正讲着,师母走过来说:“晚餐吃白菜好不好?”
他手轻轻一挥:“可以。可以。”
我们的心有些酸,这么一个有学问的老师,就吃白菜?
欧阳老师大约感到了什么,忙说:“白菜是好东西,《本草纲目》上说它可以入药,古人说它味虽淡,却让人百吃不厌,所谓‘大味若淡’,一点也不假。”
我们很认真地点着头。
欧阳老师很喜欢写诗,历年所写的篇什,工工整整地抄在一本厚厚的册子上。
有一回,他念了一首小诗给我们听:“儿衣儿食长儿年,母望儿成欲眼穿。辛苦莫忘晨夜读,学钱多是绩麻钱。”
念完了,就讲了一个故事,作为这首诗的注释。
好多年前,欧阳老师在县中学教语文,班上有一个穷学生,父亲早已亡故,靠母亲日夜纺线绩麻维持生计。可这个学生读书一点也不用功,成绩很差。欧阳老师便把他叫到自己家里,作了这首诗,用毛笔抄好送给他,一句一句地吟,一句一句地解说。那学生仿佛被“点”醒了,痛哭了一场,从此发愤读书,考上了大学。后进入一个军工研究所,成了一个颇有成果的设计师。有一次,那学生出差到湘潭,乘了一辆部队派的吉普车来看望欧阳老师。他让车停在校门外,步行穿过校园,一直走到欧阳老师的办公桌前,立正,行军礼。
欧阳老师愕然地望着面前这个佩着少校肩章的军人,茫然不知所措。欧阳老师教过的学生太多了,怎么也记不起他是谁。
军人递上了那张诗笺。
欧阳老师很平静地讲完这段故事,并不激动。他指着第一句诗说:“这前面的两个‘儿’字,是名词动用,翻译出来是‘给儿衣穿给儿饭吃是为了儿更快地长大……’”
我们觉得胸口发热,脑门子上竟冒出一层汗来。这诗仿佛是为我们写的。
我们记起了很会喝酒的欧阳修,诗人是应该喝酒的。有一次,我们问欧阳老师会不会喝酒,他嗫嚅了一阵,说:“会喝。后来戒了。”
初中毕业后,我到相邻的一个城市去当了名工人,居然业余搞起了文学创作,先写诗,后作小说,细细想来,大概与欧阳老师的熏陶有着某种关系。
“文化大革命”中,中日突然建交。有一天,我回湘潭去探望父母亲,恰好在街上碰到几个初中时的同学,便相约晚上去拜谒欧阳老师。他又调到另一所中学教语文去了,家境也好了,有两个孩子参加了工作。
他现在住在城东的郊外。
这是一座很旧的宿舍楼。穿过拥挤的摆满炉灶的过道,我们敲开了他家的门。他的模样似乎一点也没有变,头发依旧向后捋着,只是青黑中现出秋霜。
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说他仍在教初中的语文课,还说看过我的诗,不过他不懂新诗,他仍然写旧体诗,写得很勤。最近为庆祝中日邦交,写了一首七律,中间有两句他很得意:坐渡金皮跨恨海,小园狮子舞朝阳。他说:“坐、渡是名词动用,各取陪同田中访华代表团中两个高级官员名字中的一个字;金皮是指我们宴请客人时所演奏的日本曲子《金皮罗船》;小园是指日本,狮子是指田中,朝阳是指伟大领袖毛主席。你看如何?”
我说:“修辞手法很高明。”
欧阳老师来了兴趣,又翻出一首新近写的词,是表现越南、老挝人民打击美帝国主义的,开始两句是:越深陷,老惨败……
我说:“老师这两句更妙了,第一句是说美国人在越南越陷越深,在老挝呢,老是吃败仗,‘越’‘老’二字,妙不可言。”
他高兴得眼睛一亮,高喊他的夫人:“快快备酒,我遇了知音了!”
他的酒量果然不错,一连灌了五六杯,稍有点醉意。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欧阳修。
告别欧阳老师,走出门外,秋月正悬挂在中天,洒下一地清辉。路两旁是密密的瓜架,瓜叶嵌着闪亮的银边,瓜架下则是一片黝黑。
我想:欧阳老师生活一定好些了,开了酒戒,有酒催诗,该是他一大乐事。
前些年,欧阳老师在度过八旬高龄之后,因病逝世。他的大女婿,也是一位作家,将其岳丈此生留下的诗词手稿编辑出版,并赠我一册。有写新中国成立前离乱生活的,有写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有写他教书生涯和读书心得的,有写友情和亲情的,多为遣兴吟哦,一般不示于人的作品,有独立的见解、坦荡的情怀,不人云亦云,而且艺术性很高。每每读之,令我感慨万千。
欧阳老师,我永远怀念您!
聂鑫森,一九四八年六月生于湖南湘潭。初中毕业后,一九六五年到株洲市木材公司当工人。一九七八年调《株洲日报》副刊部工作。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先后毕业于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现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株洲市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