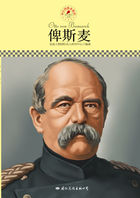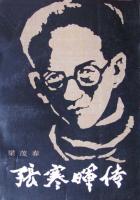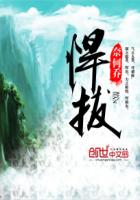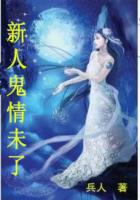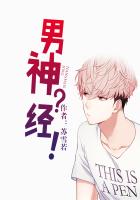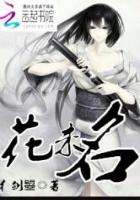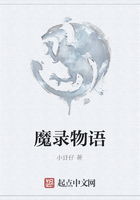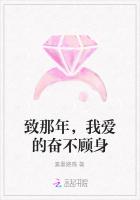柯受良飞跃黄河以后,我在凤凰卫视基本上是打杂阶段。给我的职位是神州电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这个公司实际上是凤凰卫视在内地的一个影子公司,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境外媒体不能在内地成立自己的分支,所以凤凰注册了一个神州电视公司,作为变通。其实就是凤凰卫视在国内的总部。我分管公关和大活动,公关主要是和国内媒体打交道,我分管着一个公关部,员工都很能干,我实际上的工作不多。大活动的事情也不多,柯受良飞黄之后,我们一直在策划大的活动,也有一个部门归我负责,但是,策划案做了一大摞,没有能够实行的。
后来,有一个小企业家愿意出资来打捞甲午海战中沉没的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舰,因为几年以前,在长江里打捞中山舰,动静弄得挺大,所以,不少人在打海里的主意。
有了资金就容易操作,当时我对这位企业家说,先花三十万块钱,如果花了三十万,能够找到这艘军舰,我们继续玩下去,如果找不到,就干脆拉倒。画饼充饥的感觉还是美妙的,当时我们设想,这艘军舰出海时如何庆祝,如何把这艘军舰改造成甲午战争博物馆,如何运用声光电技术,甚至想到了收门票的收入干什么。
那一段时间,我去青岛,找北海舰队,找有关的专家,也去天津,找海军档案馆,费了好大的力气,也在档案里找到了蛛丝马迹,但是,海里的定远舰像是失踪了。这时候,我才深切感到了石沉大海的真正含义。
于是铩羽而归。
电视这个行当,似乎有点排外,如果不是广院的,如果不是某某电视台出来的,想要融进去很难,于是我像是赋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竭力撺掇做一本杂志,老板也原则同意了。
起初的念头是和别人合作,这种合作其实就是买一个刊号,说买也不确切,实际上是租,因为产权还是人家的,我们用而已,每年付几十万元,说是管理费。这种做法尽管不怎么合规,但当时很多人用这种方式做杂志。
但是,和谁合作?颇费思量。
当时,新闻出版署一位领导的孩子为我们推荐了一本杂志,记得属于民间文艺学会,每年要收二十万管理费,这个数字是个正常数,但是,他们要求留下一个人当社长,每个月付八千元工资,这就让我犹豫了,举棋不定。
就在这时候,节目中心的郭志成带来他的同学喻凌霄,和凤凰卫视谈合作一本杂志。喻凌霄是个牵线人,实际上的操作者是个书商,很大的书商,叫席保平。
席保平的思路不同,他主张到香港注册一本杂志,这样,产权明晰,不是租借来的刊号。至于怎么解决在内地发行的问题,他似乎胸有成竹,说,可以用通过新闻出版署批准进口,在内地有限制发行的做法,所谓有限制,就是只准在机场、码头和三星级以上涉外饭店销售。席保平自告奋勇,说他来解决批文。
当然,在他的努力下,这个事情做成了。
正式在凤凰立项,是一九九九年底的事情。那时候,凤凰卫视正在组织“千禧之旅”,从奥林匹克到万里长城,我做国内部分的总协调人,主要是协调千禧之旅的车队进入西藏以后,从青海到甘肃、四川、陕西的当地接待工作。
应当说,甘肃段的事情比较难办。因为我们和甘肃不熟,很多工作要先磨合关系,再说,当时我们做了一个项目,是在嘉峪关边上一平方公里的地上写一个大大的龙字,因为千禧年正是龙年,而这个项目是敦煌石窟著名的艺术家常书鸿先生的儿子常嘉煌策划的。
那时候正是冬天,戈壁上白雪皑皑,雪不厚,黑色的石头零零落落地在雪地上露出来,有点像白色棋盘上散落的棋子。我们找了一辆洒水车,里面装上墨汁,在地上按照画好的线条洒出硕大无朋的龙字,再把墨汁写成的龙字挖成沟,里面放上木柴,龙年到来之际,点上火,用热气球航拍这真正的“火龙”。
实在是壮观无比。
而这个时候,我没有激动,也没有兴奋,我的心,已经到了《凤凰周刊》。
这是个还没有降生的生命,我的任务,是孕育它。
我虽然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创办者之一,但是,从没有做过杂志,特别是这样市场化的杂志,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我现在脑海里还常常有这样一幅画面:我和刘长乐以及凤凰卫视二把手崔强散步在深圳华侨城一带,刘长乐对我说,老周啊,你们也没有见过太多的好杂志,要从头开始做好这样一本杂志,太难了!
老板信心不足,反而成了我的动力。
我很快投入了创业。其实,我在创办中央文献出版社的过程中,若干次说过这样的话:就是给我自己干活,我也不会更卖力气。创办《凤凰周刊》的过程,也同样用得上这句话。
我从凤凰带了一个人,刘于莉,她是千禧之旅时在甘肃戈壁上担任我的助手,这时,她计划去法国留学,出国之前,帮助我工作一段时间。几个月后,她就去了法国,现在,她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剧作家了。
最开始找的参与者是邓康延和蓝艺,接着来了杨小宝、王非、闻正兵等人,他们当时都有比较稳定的工作,为了一个尚不知道模样的杂志而抛弃原有的安宁,也是有胆量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开始阶段就是落实办公室,落实启动资金。当时凤凰卫视投资五百五十万元,做一本周刊,这点钱是十分拮据的,只能过苦日子。有朋友提供了一个办公场地,在联合广场的五楼。是免费的,不过也不能算免费,当时谈的是这个业主把房子给我们用,房租记账,然后,业主卖《凤凰周刊》的广告版面来顶租金。这位业主是房地厂商,胆子也不小,居然身为外行而能够相信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好看。其实,直到两年后《凤凰周刊》搬到荔景大厦办公,他也没有卖出去一页广告。
不过,这位业主帮助了我们初期的创业,至今我念念不忘。
除了解决办公场地,招兵买马,再就是务虚,讨论杂志的内容。
当时主要是两种意见,一种是作为凤凰卫视的附属刊物,电视播什么内容,杂志相应的上什么内容;一种是做一本相对独立的杂志,以时政内容,适当兼顾凤凰卫视的节目内容和主持人的介绍。讨论得很热烈,崔强常常从香港专门赶到深圳来参加讨论,他是这本杂志的编委会主任。
最后,思想是统一的,做一本时政类的独立的杂志。
凤凰周刊正式开始进入工作状态,已经是二〇〇〇年的春节后了。
那一段时间,真的有创业的劲头,大家齐心合力,没日没夜地工作。我那时也租了房子常住在深圳,不过似乎我没有具体做什么事情,我的原则是,大政方针定了以后,不插手具体业务,也不审稿,审稿的任务是主编的。这个习惯我延续到了现在。现在,《领导者》杂志、《财经文摘》杂志、共识网,我一律不审稿,除了大的问题主编拿不准的来问我。我的想法是,这样主编才会知道,自己就是最后一关,会更加小心谨慎。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保留批评权,如果我最后审稿,出了错批评谁?
邓康延后来几次对我说,越是这样,他越是战战兢兢,生怕出错。
但是有一点是我要做到的,万一出了问题,我要扛起来,不能说,我没看过,不负责任。就是说,任务别人扛了,责任我要扛。要不然,这个领导也太好当了,还不人人争当领导?
干活儿没印象了,印象最深的,是晚上带着大家去大排档吃宵夜。只有在这个时候,小伙伴们才轻松下来,喝点啤酒,讲讲笑话,那点辛苦无影无踪了。而每当这个时候,大家成了一家人。后来,很多参与创业的老员工都对我说,那个阶段的《凤凰周刊》,条件不好,钱不多,但是大家团结,玩命干活,是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们决定先试刊三期,三月四月五月各一期,用三个月的时间敲打内容,磨炼队伍,第一期试刊选在了凤凰卫视开播四周年的日子,二〇〇〇年的三月三十一日。而正式出刊就定在了六月,凤凰卫视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时候。
看起来紧张有序,却也有不和谐音符。
问题出在合作者席保平这里。
席保平是个书商,生意做得很大,为人也还好合作。这次合作创办《凤凰周刊》,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生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被任命为副社长,负责经营。但是,他希望能够在《凤凰周刊》有更多的话语权,又碍于我这个社长在,于是,就有意无意地散布说,周总是北京来的,早晚要回去,将来这个杂志是他当家。因为他是书商身份,所以有的编辑人员本能地有些排斥,于是,就有了一点担心。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也不太高兴,正好当时深圳福田地区有一个新楼盘在售,我索性就买了一个一居室的房子,对大家说,我肯定不走,你们看,我买了房子了!
阴差阳错,六千元一平米买的房子翻了好几番,无意中做了一次正确的投资。
故事还没有完。由于向前推进得太快,凤凰卫视一直没有和席保平签正式的合同。直到第一期试刊完成了,才腾出手来整理文件,起草合同,并且决定,我们在二〇〇〇年的“五一”签合同。
“五一”这一天,席保平把合同签了字,交给我,让我签字。事情就是这么巧,我不知怎么想的,我说,这个合同我不能签,我明天到香港,让法务部门再看一遍。结果当天晚上,席保平被公安机关抓了,原因是盗印图书,后来判得很重,有期徒刑二十年。
合同没有签字,也没有生效,席保平就从合作中退了出去。想想很后怕,如果合同签字生效了,席保平是《凤凰周刊》团队的一员,在凤凰卫视上市的关键时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只能感谢老天眷顾了。
这之后,《凤凰周刊》波澜不惊地向前发展。当然也有曲折,但是都还顺利。最主要的是确定刊期上费了些周折。开始一段时间是半月刊,但是总觉得对不起周刊的名义,于是就想一周出一期。但是又觉得负担很重。编辑负担重,疲于写稿编稿,读者负担也重,每周出十块钱买杂志,一年要五百多块,在十几年以前,这还是个不小的数字。于是,我出了一个主意,一个月四本,两本是时政内容,胶订,八十页,十元一本,两本是娱乐内容,骑马订六十四页,五元一本,这样内容也少了,编辑的负担轻一些,也便宜一些。
不过,问题又来了,广告商不愿意在骑马钉杂志上投广告。于是再改,最后确定下来的格局是出旬刊,十天一本,是同样的规格。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凤凰周刊》,都维持了这样的刊期。
再有就是内容的把握,在初期也是要经过磨合的。有些事情好办,例如,二〇一一年的“911”,美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恐怖袭击,编辑部思想很统一,用最快的时间赶出了一期杂志,封面很有冲击力,标题也很震撼,是邓康延的语言:历史在我们眼前爆炸!
但是,有些内容就要费些时间来做说服和解释。记得是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编辑部准备了十几个页码的稿子,准备大规模介绍高行健。他们来问我,我说,不行,现在国内不允许宣传这件事情,我们既然在中国大陆有发行,就要遵守有关规定。当时邓康延是主编,还有一位执行主编冉小林,他们辛辛苦苦组来的稿子眼看要泡汤,他们也着急,但是,这是原则问题,我不能让步。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宣传系统的高级干部,我对他说了这件事情,他说,幸亏你把关了,不然问题就严重了。我想,对于编辑部来说,也许就是一次平常的组稿和被枪毙,但是,这一次也是一堂课,教会我们的年轻编辑怎样适应现在的媒体环境。
《凤凰周刊》总的来说,是在顺利前进,除了凤凰的品牌效应,凤凰卫视在电视画面上给予杂志的支持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经营还不错。所谓经营,主要是广告。当然发行也是,但是,发行的数量多半是为取得广告商的认可。那时候,凤凰卫视有不少广告分公司,他们也承担了为周刊拉广告的任务,有的索性就做了公告套装,就是把电视广告切一小块下来,作为杂志的广告,或者是做电视广告,送杂志广告,而在内部分割时,给杂志分一部分。
在《凤凰周刊》做到两年的时候,基本上做到了盈亏平衡点。有一个月赚了三千块钱,有一个月赔了六百块钱。记得当时一个员工调侃我,说干脆你自掏腰包补上这六百块钱,这个月也没赔钱,多好!
行家都知道,一本杂志如果做到两年持平,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二〇〇二年的六月份,杂志影响力增加了,经营上取得了成效,我还做了一件大事,拿到了万科房地产公司的办公场地约一千六百平米。用拿这个字,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当时这个位于深圳荔枝湖畔的写字楼价格是八千多元一平米,一千六百平米大约是一千三百万元,我们用杂志广告抵掉一半,剩下的六百五十万用月供的办法,每个月记得是八万多,用八年的时间供完。而当时,凤凰周刊租用办公室的租金也要八万多。这是一笔十分合算的生意。记得当时我对刘长乐总裁说,也许,凤凰周刊做了很多年以后,发现赚的钱就是这栋房子。
现在,这个写字楼的单价到了三万多,总价值差不多五千万元了。
不过,我没有搬到这个写字楼里一天。
六月份,凤凰卫视突然做了一个调整,四个高层管理人员对调,负责广告的和负责节目的对调,负责《凤凰周刊》的和负责凤凰网的对调,而且要求两天内调整完毕。
凤凰周刊顿时就炸了锅。
因为这个团队每个人都是我招的,每件事情都是我主导做的,团队有很强的凝聚力。邓康延亲自跑了一趟香港,找到老板,要求老板收回成命,结果,据说他挨了一顿批。甚至还有人对我说,索性我们都离开凤凰,另起炉灶。我当然知道这是绝不可行的,甚至不能有这样的念头。那时候,我回到北京了,写了一段话,字很大,传真到深圳,我让办公室贴在墙上,大意是:我服从老板的决定,也希望大家服从公司的安排,在新的社长的领导下,把《凤凰周刊》做得更好。
说实话,我写这张纸,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周刊的员工,一方面也是为了撇清自己,说明我没有鼓动员工来挽留我。在宣布我走的会上,老板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单位到底战斗力强不强,要表现在主管离开之后,是不是还能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这句话,我始终记得。
二〇〇二年六月到二〇〇三年四月,我在凤凰网工作了不到十个月,还是给凤凰网带来了新的气象。刘长乐曾经专门给我传真了一张纸,上面是他写的一行大字:凤凰网出现的新气象,令人兴奋。
离开凤凰网之后,我开始创办自己的媒体,从《财经文摘》到《领导者》杂志,到共识网。现在,我又在创办一个新的机构,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我似乎一直在不断的创业过程中,不过,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我创办了共识网
五年坎坷路,一首正气歌
这一串脚印
共识需要改革,也需要妥协
起码的共识是推动祖国的前进的动力
共识、妥协与沟通
思想者的盛宴
共识网首秀深圳
从二〇〇九年开始,我创办共识网。五年的时间里,共识网已经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性网站之一。回头看看,一路坎坷,水一脚泥一脚,往前看看,山峰还很高,一路崎岖。
但是,共识网不是人生的起点,我相信也不是终点。创办共识网,是因为有之前打下的基础:我的学生时代,军营生活,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锻炼,以及在凤凰卫视的砥砺。
虽然我现在说不上成功,但是也可以说真正体会到了这样一句歌词的真谛: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