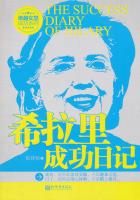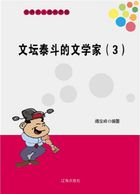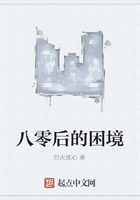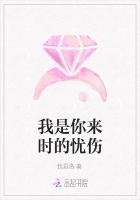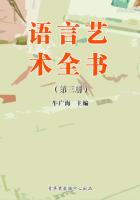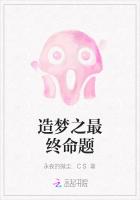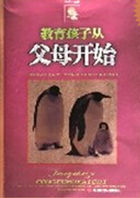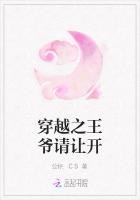八月八日晚上,我邀请在上海的一些专家学者聚餐,理由是请大家对我们《领导者》杂志和共识网提建议和意见。
温州瑞安驻沪商会盛情邀请我到他们的会所来举办这次活动,恭敬不如从命了。
原以为这个地方不是个大酒店,学者们不好找,会影响一些学者的参加,没想到,大家都准时到了。
刘吉院长是从重庆回到上海,下午刚下飞机,赶来了。
华东师大的萧功秦教授一如既往,是骑着摩托车来的,我笑他:会不会有人以为你是送快递的?他笑道,还真的有人以为我是送机票的。像萧先生这样的学者骑着摩托车到处讲学,也是一道风景呢。当然,我也见过******先生骑着自行车到五星级酒店去参加会议。
上海财经学院的裴毅然教授美髯飘飘而来,其实他才刚过五十五岁,曾经在大兴安岭落户过许多年,走到今天这样的学术造诣,当属不易,难得的是,在学术研究之余,他还写小说。
严搏非先生是上海著名的季风书店的老板,他对于图书的了解真的让我叹为观止。
朱小平先生是位奇才,他居然写过厚厚一本数学书,同时写有经济学的图书,还研究历史,说起党史来,我是自叹不如。
相比起小平先生的咄咄逼人,复旦的张汝伦教授温文尔雅,他听的时间比说的时间多,总是在汲取别人的好东西,真是“狡猾”啊,不过,我在网上看到他的一个学生评价说,他认为张教授是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真的很高的评价。
还有一位美女任晓雯,我在微博上认识的,她打破了我的美女没思想的观念,当初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小姑娘讲起理论问题头头是道,寄了一本《领导者》给她,以为她会看不下去,没想到她还真的看进去了。
要说对不起的是赵何娟,本来说好了带她玩的,没想到来的人多,这个会所的桌子小,实在坐不下了,包括何娟在内的几位媒体人只好被舍弃了,我赔罪。
本来,瑞安商会的人告诉我,从瑞安专门还运了些特产过来,没想到,大家对吃什么根本没有兴趣,上来就开始激烈的讨论。例如说“三个代表”理论的产生和作用,这一点,刘吉先生最有发言权,他是当事人。例如说党的历史和党内斗争的话题,朱小平先生很清楚,他的父亲就是建国初期的上海市委常委,小平和体制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本人又博闻强识。说当前社会的左右之争论以及如何看待毛泽东,萧功秦教授和张汝伦教授都是权威人物。说目前图书市场以及内地与港台出版界的比较,严搏非又是行家里手。说中共历史上的许多人物,说当前社会的各种思潮,裴毅然教授非常透彻。
饭桌上吵得一塌糊涂,常常是这个人没说完,那个人打断他;常常是分成几摊说,不知谁听谁的,后来我说,我来当主持人吧,都听我的!我让谁说,谁再说,不过,希望简短。朱小平首先挑战主持人,说:我的话,短了说不清楚。
大家大笑!
内容太多,我又不可能都说,毕竟是个内部研讨,所以,只讲氛围,不说实质,这也是我们能够享受的特权吧!
总之,一次精神大餐。
附 聚会·思想·政改——记沪上一次学人聚会
裴毅然
二〇一〇年八月八日,北京《领导者》杂志兼共识网社长周志兴来沪,邀请几位沪上学人小聚。承蒙浙江瑞安上海商会会长吴敏先生邀请,假座商会会所——徐汇区名都城别墅五十四号。出席者除主人商会会长吴敏先生及周志兴先生,客人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先生、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张汝伦、上海师大史学教授萧功秦、经济学家朱小平、上海季风书园董事长严搏非、中国作协会员任晓雯小姐,以及记者王孔瑞、商会工作处主任李玉迪,以及本人(上海财大文学教授)。不过一桌人,话匣一开,派别林立,侧耳一听,全是最真实的“世声”,还真难得听到呢。聚餐会成了争吵会、辩论会。周志兴先生当晚撰文博客:思想者的盛宴;谓之“吵得一塌糊涂”。
刘吉先生刚从重庆飞至,基本是主讲人,接近中枢,信息多多,但他最热忱宣讲的还是全力参谋的“三个代表”,他详细解释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的内涵,指出“三个代表”如何具体凝聚了江总书记“专家治国”的思路。通过他的介绍,我们这些中青年学人自是进一步理解了中央的难处,知晓政改必须面对的种种现实掣肘。
朱小平先生出身红门,真正的“红二代”,父亲乃三八式,中共进城后首届上海市委常委,家里曾有象征级别的“红机子”。他介绍了当前“红色文化”再起风云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十年改革既取得重大成果但政改滞后,意识形态一仍其旧,许多社会矛盾无法化解且日益突显,从而造成社会底层许多人近乎本能地运用红色文化语汇进行宣泄,他们对许多社会现象强烈不满,同时他们又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其他文化形态。另一方面,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属于雷蒙·阿隆所说的“左派”,用红色语汇诠释社会矛盾是他们进入更高权力阶层的敲门砖。此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近几年来,一些老一代高干由于个人原因对当前社会矛盾提出政治诉求,也本能地再次高调呼喊红色口号。与此同时,一大批所谓的“干部子弟”深受父辈影响,纷纷加入这一大合唱,推波助澜。二〇〇六年,一位曾位居相当高层的老一代领导人最后一次生日聚会,贺客来了三百余人,大多是声名在外的“红二代”,最后一个节目高唱《东方红》,全体起立山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都说小平也是“红二代”,他摆摆手:“‘红二代’是有级别的,五级以上,我父亲才八级,本人进不去!”小平最后总结自己的发言:“看来真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针对“国情特殊论”与“农民参政能力”,严搏非先生发表见解:“要全体农民了解历史信息与国家大事,不太现实,亦无必要;他们只要通过选举捍卫自己一村一镇的利益就可以了。”对呵,先在基层农民那里推行维权式民主,然后由村主任上镇里进行维护村落利益的选举,镇里再上县里维权选举,如此这般逐级维权,由一县而到一市,一市进至一省,一省最后至中央,不也可以“农村包围城市”、“由地方至中央”,搞成渐进式民主?民主的价值根基不就落实于维权么?逻辑正确,关系很顺呵!难道农民一日未知识化文凭化,民主就“囿于国情”无法开展么?至少,民主可以先搞起来,逐步完善。民主确实是个高档货,需要相当的社会成分整体配合,需要一个通过实践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如要求一上来就完美化,事实就等于取消民主。
我们几位中年学人发言很少。张汝伦教授几无“长篇发言”,萧功秦教授评了几句,本人也只是向刘吉先生提了几个稍涉敏感的问题。但感觉得到,几位学人对时局对改革的思路相对一致,大体认同刘吉先生的“旧瓶装新酒论”,走“告别革命”的路子,希望能够在“集中”之下完成社会转型,走向民主。讨论中甚至细化到如何具体操作民主。本人发言不多,但感到这一代人文知识分子较之“五四”确实有了长足进步,意识到“稳定”的重要性,宁慢勿躁,已非直取中军式的重起炉灶。席间当然少不了风波骤起,时有争论,这当然十分正常。如果一桌人所思所想都那么齐崭崭,只能是“文革景象”。
值得注意的倒是几位非学界人士的政论。浙江瑞安驻沪商会会长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少壮派,仪容整齐,红光焕发,一看就是成功商士。席间,他唯一一次发言是评毛:“我认为,毛泽东首先是个伟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后来的邓小平,当然也就没有我今天的从商机会与事业。”
坐在我身边的一位中年记者,一直闷不出声,他对我悄悄发议论:他们都不行!我问他:“那么你看该怎么办?学西方吗?”“不用!”“那么,学谁?”“可以学老祖宗呵!我们有老祖宗呵!”我还是不明白,追着问:“怎么学?”他答曰:“老早不是有皇帝么?现在既然谁都不服谁,为什么不学学老祖宗呢?”呵!真没想到,身边端坐着一位“帝制派”!这位“七〇后”(估摸他出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怎么会有这种“意识形态”?看来,不得不找找“子错父责”呵!
聚会散后,走出别墅,胸内翻腾,深感民间思想之杂乱,形成共识之艰难。结合平时听得的各种“世声”,实事求是地说,当今社会意识形态处于十分混乱混沌状态,历史车轮从相当意义上重回“第二个五四”。只是这次意识形态重建过程甚长,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红色思潮全面退落以后,“王纲解纽”,中央虽然努力再三,但至今尚未形成朝野认同的意识形态。而社会共识度低,矛盾冲突点自然就多,维稳的难度就大。意识形态认同,即社会成员价值观趋同,乃是最大的维稳工程。公安维稳,尽管必不可少,究竟类乎扬汤止沸,治标而已。当然,囿于历史积重,意识形态不得不带着“历史”一起走,无法径走直线,只能“政治地”走曲线。由此看来,周志兴先生为自己的平台取名“共识网”,含意深远呵!就当今国情,确实需要尽可能地形成共识,有共识才有共力呵!
国家是全体国人的,从理论上来说,每位公民都有言政权、参与权,而最后的决定与选用,又只能是唯一的。从现实国情看来,如何既让大家讲话,又保持理性进行与社会稳定,确实是一项考量当代国人集体智慧的大课题。当然,首当其冲考量的是最高领导层,既要走又要稳,既要自由又要和谐,弹好政改这首乐曲,难度与价值同在呵!不过,根据中外前人经验,解决与平衡社会成员之间的分歧,大概只有走“多数政治”之路,即只能“少数服从多数”。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社会最大的维稳器,让争端合理合法地公开进行,而非暗中憋着使劲,最后暴力解决。此外,民主还是效率,不仅可相对迅速地纠错制贪,还可收集各方智慧,使全社会拥有更多的选择项目。一花独放与百花齐放,谁的芬芳更浓烈呢?新闻自由的身后是“社会守夜神”(新闻工作者成为社会的第一敏感器),言论自由的身后则是“智慧博弈”呵!
二〇一〇年八月至十月十一日于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