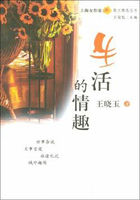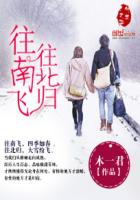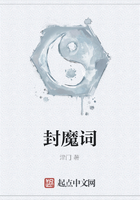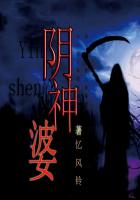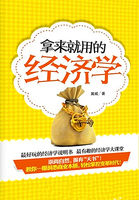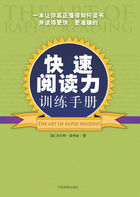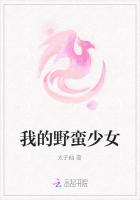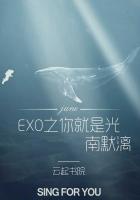2012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终于走访了向往已久的高平良户村,原以为和其他历史名村差不多,无非是些残留下来的农业文明的碎片,有点满不在乎,走的时候连录音笔和手机都忘记带了。
进了村子,正遇到有人家出殡,灵棚里的八音会吹得嘹亮热闹。
拐过一个弯就看出了良户的不同寻常。随处可见的古建筑虽已破败陈旧,却依旧遮不住往日高门大户的繁华和气派。在一座气度不凡的大门前停了下来,见门口的石狮子不知何故被泥巴糊了,门口挂着一个木牌,根据上面的说明文字,得知此处叫“室接青云”,一座明清时期的祠堂,此处曾有牌坊连壁坊,有种玉亭、攀龙鳞、附凤翼、振家声等建筑群,很想进去看看,大门却是锁着的。
没有熟人,又忘记了带相关证件,只好逢人就问,却说拿钥匙的人不在,需要等等。在等待钥匙的时间里,随意看了几家普通人家。才知道良户的富贵不是一处两处,而是非常普遍的存在过,随便一个人家的门楣,或者堆放杂物的角落,都能看到精美的石雕砖雕木雕,角角落落散发着岁月的沧桑,如一张发黄的宣纸上洇开了陈年的笔墨,顺着视觉的触摸,漫漶到我的心里,让我震撼,让我惊讶,让我的心跳加速。
天下着些微微的雪花,刚刚的盖了地面。
进到一座院子,一户人家的窗子里传出热闹的说话声,正琢磨要不要进去打问一番,就见花布门帘挑了起来,走出一位老乡,很热情的说:“进来吧,外面冷,进来暖和暖和吧。”我便骑驴就坡登堂入室了。
屋子里烟雾腾腾,有三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人正抽烟闲聊,另外还有一位老妇人和两个半大的女孩子,老乡请我们坐下,问我从哪里来的,做什么来了。我自报了家门,老乡很热情的请我们坐在土炕上,随意啦呱了起来。
在和老乡的闲聊中,得知良户最早只有田姓和郭姓两户人家,原本叫两户,后来各种姓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才改为了良户。良户从唐代始形成村落,发展到金元明清逐渐鼎盛,形成了风格独具的建筑群,除了官宦府邸,商贾豪宅和普通民居各具风格外,有过观音阁,文昌庙,玉虚观,关帝庙、九子庙、龙王庙、三官庙、祖师庙、汤帝庙,白爷宫等寺庙建筑。上了年纪的老乡们至今记得良户当年的华丽和豪奢,到处是飞檐斗拱、四梁八柱的华美建筑,家家的门楣上有烂漫纷披的木雕和字体遒劲的匾额,寻常人家也都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有门当户对,户户大门两侧都有雕工精美的石狮子,整个村子随坡就势,依山而建,层层递进,高下相间,四维包裹,结构严谨,古色古香,村口曾经有过非常华美高大的牌楼,当年的良户全村只有一个进出口,必须通过牌楼的阁才能进到村里。
良户曾经富甲一方,当时有个说法,说田家官大,郭家钱多,发展到后来,望族名门不止田家和郭家了。历史上的良户历来尊儒重教,世世代代延续着耕读传家的遗风,明清两朝出过一个家族里有祖孙、兄弟相继科甲的盛况,历史上产生过六名进士,十多名举人,此中,清朝重臣浙江巡抚田逢吉最为显赫。
田氏一族曾是高平明清时期的名门望族,田逢吉为清代康熙年间名臣,字凝之,号沛苍,书香门第,耕读传家,五代为官,清顺治乙未(公元1655年)进士,初选翰林编修,官至户部右侍郎,康熙帝经筵讲官及内阁史学士等职,调任浙江巡抚后,遭遇耿精忠的“三藩之乱”,田逢吉率制府李之芳督师金衢,部署军务,日夜勤勉,积劳成疾,后告归乡里,卒于家中。田逢吉去世后,皇帝即颁旨官赠其祖父田可耘为通奉大夫,内国史院学士加一级,敕封其父田驭远为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级,加封通奉大夫,内国史院学士。良户至今留有一副颂赞田逢吉历史功绩的对联门匾,曰:“名流翰院光留良户,德惠浙江史汇长平”,横额:“来骥天南”。田逢吉之弟田光复进士及第,田逢吉之孙田长文也是康熙五十一年进士。
随着政权的更迭,田家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衰落了,但那些曾经记录了当年盛世繁华的豪奢建筑,却依旧静静地屹立在丹河边,昭示着岁月的变迁,安然地走过了民国,走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后,尤其是1966年,良户所有承载着中华历史文明的华美建筑群,宿命般迅速地终结了完整的存在,在一场接一场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中沦为废墟。
采访中,说话最多的是一位姓王的老乡,老乡说:“哎,那时候的良户是甚的光景,我那时候十几岁了,记事哩,每天放学回来,不走阁门就进不了村,那时候的良户村到处是严丝合缝的高门大户。有文峰塔,松鹏庙,还有祭祀李世民的皇王宫,观音阁,玉虚观……多了,有东街,西街,后街,太平街,村里有染坊,油坊,当铺,丝绸铺,木匠店,杂货铺,更房……
我问:“什么叫更房?”
王老乡说:“打更你知道吧,以前没有钟表,村里有专门的人打更报时,到一个时辰就要打更,手里拿着梆子和铜锣,铎铎铎,咚……三更了!五更了!”
我问他:“1966年文革的时候你多大了?”
王老乡说:“十六七了吧?”
我又问:“是红卫兵吗?”
王老乡说:“是啊。不过我可没参加过打砸抢。”
旁边姓宁的老乡说:“我可是参加过拆庙。”
我问“你们村里这么富有,一定有过不少地主吧?”
王老乡说:“有啊。不过我们不记得斗地主时候的事情了,听老人们说,当时真正有钱的人姓高,因为儿子在共产党的部队上当高官,知道政策,土改之前写回封信来,让他父亲赶快把家里的土地财产赠与穷人,他父亲照办了,所以斗地主的时候反到没有被划成地主成分。相反有一家人家并没有什么钱,只因为娶了小老婆,人们就认为他有钱,说他,没钱你娶什么小老婆,你不当地主谁当哩。那人说,那地主就地主吧。结果就把他划成了地主了。后来每次运动来了就批斗他,让他扫大街,那时候哪里都是这个样,搞阶级斗争,毛主席让横扫牛鬼蛇神,要消灭剥削阶级,这些你们知道吧?”
我说:“过来人了,这些当然知道。”
王老乡说着拿出一本画册来,给我介绍良户,说:“你看,这是田家的祖坟,坟上的石人石马,你看看,这石人都没有脑袋了,还有两面石碑。”
我问:“田家的祖坟还在吗?”
王老乡说:“没了,人民公社时期,村里要修水渠引水,没有石料,就把田家的祖坟扒了,那坟可是气派了,一色是石头圈的,牌楼,石人石马多下了,那些石雕都打了石料砌到水渠上去了。田家的坟里挖出来都是三层棺椁,我们这里叫套棺,棺材里的尸骨掏出来随便往野地里一扔拉倒,那时候时兴破四旧立四新,文物全当四旧给砸碎了,碎瓷片飞的到处是,金属的文物都练了钢铁……”
我问:“那坟墓上石人脑袋也是文革时期砸掉的吗?”
王老乡说:“那到不是,是改革开放后,文物值钱了,被人偷了。”
我问:“那可是田家的祖坟啊,当时挖人家祖坟,田家的后人就没有人出来阻止吗?”
姓宁的老人说:“你要知道那时候是集体所有制,村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了,你不同意也没用啊。再说,你敢不同意吗?你敢不同意就打你个反革命,斗也斗死你,谁敢?”
在座的还有一位姓田的老人,是田家后人,说:“毛主席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场的人接着一起念起来:“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念完大家都哗哗的笑了起来。
王老乡说:“坟拆了,石雕砸了,结果呢,水渠也没水了,原先有条河,如今河也干了,河床也差不多都被垃圾填了。”
拆庙挖坟,欺师灭祖,用这两句话概括当时的行为一点也不为过。在国人心里,历来挖祖坟是比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更为不共戴天的行为,但是身处其时,人们除了乖乖接受又能有什么选择呢?可悲的是,祖坟挖了,水也没了,河也干了,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换来如今这一无所有啊?用什么词汇能形容这种令人痛心的滑稽呢?
王老乡说:“现在的良户和以前不能比啊,没什么看头了,就这来的人都说好呢,在我们眼里也就是一堆垃圾和废墟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我去皇城相府看过,你们知道皇城相府一进大门那个牌楼吧?”
我说:“知道,很气派。”
王老乡说:“那牌楼算什么呀,比起我们村当年的牌楼差了不是一点,我们的牌楼那才叫个气派。真是不在了,不然你看了就知道了,不过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我问:“这里文革的时候闹的凶吗?”
王老乡说:“凶,怎么不凶,观音阁你们看到没有,建在良户村的中轴线上,有讲究的,拆的就剩下一个遗址了。
我问:“不都是自己一个家族的人吗,怎么还这么闹腾呢。
王老乡说:“你们不知道,最早带领全村人破四旧的人正是田家的后人,他家就在侍郎府里,侍郎府你去过没有,就在寨上。带领大家造反的这个人当过兵,在部队上是个副营级干部,复原回来后,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他就带头把他家照壁上的一条蟾给砸碎了,那条蟾专家们来看过,都说真可惜呀。专家说那个东西全中国只有两处,一处在北京故宫,一处就在我们良户。”
听着这些叙述让我的心感到很痛,啧啧嘴说:“真是造孽啊。”
王老乡说:“破四旧的时候,红卫兵们都是拿着八磅重的铁锤到处乱砸,把观音阁里的佛像都砸了,佛像砸了,观音阁也拆了。八磅重的铁锤知道吧?”
王老乡用手比划着:“这么大的铁疙瘩,最重的有十六磅重的,抡起来起来砰砰的几下,那些雕像就成垃圾了。后来一家家都跟着拆跟着砸,把所有的石雕砖雕木雕全部敲坏,就成现在这样了,现在的良户基本上都没有东西了。
我真有些不忍听下去了,问老乡:“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你们残留的东西?”
老乡们说:“可以啊,你是为我们做好事呢,我们再忙也愿意陪。”
说着一群人从他家院子里走了出来。走了没几步,拿钥匙的人打来电话说他回来了。我说:“既然那人回来了,就不麻烦你们了。”
和老乡们告辞了,绕到后街,见了拿钥匙的人,四十开外的样子,头发有些花白,方颊宽颐,身材适中,有点落拓不羁,从衣着上看不像一个农民,自我介绍说:“我叫宁宇,是这个村里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我本人是个反革命分子。”这样的自我介绍很是有些特别,我呵呵的笑了起来,告诉了宁宇我的来意和身份。宁宇说:“那你找我就找对人了。”
手里拿着一大把钥匙的宁宇带着我们参观了玉虚观、汤帝庙、文昌阁等遗址,大多破烂不堪,废墟一片,只有玉虚观保留了金元时期的两座座大殿,看上去典型的金代风格,浑朴伟岸,释放着历史的凝重。玉虚观曾经作为学校使用过,门楣上苍劲的“玉虚观”三个字依旧清晰,上方后加的“培育英才”四个字,昭示着历史的足迹。
一路上宁宇东一句西一句的讲述解着良户的变迁史,由此得知他本人是一个位收藏爱好者。话说的投机,宁宇带我们看了他的收藏。宁宇的收藏很杂,许多东西都堆放在露天,屋子里也是满满当当,无处下脚。有古老的纺花车,有雕刻精美的压窗石,有各种旧建筑上的砖雕,有木雕,有根雕,门匾,有战国时期的陶片,有汉代的瓦釜和陶罐,箱子里有各种历史时期的旧照片,旧衣服,甚至还有马恩列斯毛的挂象,我想拍几张,宁宇不让。他说从前曾经收藏过许多文物,有现在的三倍多,1993年让县公安局一古脑的全部拉走,整整的拉了三卡车,理由是说他没有资格个人收藏文物,后来他到处寻访,问来问去,公安局说是给了文物馆,文物馆说根本没有收到这个东西,全部下落不明了。他说自己的收藏是不花一分钱的东西,都是随手捡来旧砖破瓦。
宁宇指着石匾上几个浑朴的大字说:“这字写的多好,这样凝神敛气的字现在的人是写不出来的。现在的人写字写的再好也有股浮躁之气。”我很认同的他的观点。
宁宇出生高贵,爷爷是当年国民党黄埔军校的特务培训官,解放后在监狱里过了一生,父亲是《新华日报》的右派,由于家庭背景的缘故,宁宇从小被当做五类分子的子弟对待,政治上备受歧视,在学校没有人愿意和他玩耍,他便从小习惯了自由自在独来独往,人们给他起了外号叫“野兽”,他说野兽这个名字很好,野兽就是自由的意思,自由多好。他说他现在还有一个外号,叫“疯子”,意思说他和正常人不一样,不修房不盖屋,不务正业,整天弄些破砖烂瓦。
宁宇说良户的文化底蕴十分厚重,周边又是长平之战的古战场,人文历史十分厚重,随便出去就能捡到好东西,靠捡破烂也足够活命了。他很喜欢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那些收藏品在外人眼里是垃圾,在他眼里都是宝贝。在宁宇淡淡的话里话外,透漏着他作为一个良户人的骄傲。
宁宇告诉我说:“良户有过许多庙宇,庙宇里的镀金神像佛像金灿灿的,非常漂亮,大跃进时期全部砸的练了钢铁,有的直接拉去充了任务。有一个看庙的老头趁人不注意,偷偷的把三尊佛像藏到毛坑里,人们问他要东西,他不肯说,人们就吊起来打他让他说出佛像的下落,老头不肯说,可是儿子很革命,把他父亲给出卖了,说他知道在哪里。于是人们把佛像从茅坑里起出来,砸碎了送去练了钢铁。后来文物值钱了,儿子很后悔,说真不该来着……你不要笑,这都是发生在良户的真事。那个时候出身不好的子女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很多都写过‘绝交书’,表明自己决心要和反动的家庭决裂,我姑姑就给我爷爷写过绝交书,我父亲说,那没有用的,再绝交你身上流淌的血液也是反动的,谁信你啊。”
宁宇说自己在良户没房子,解放前的两串大院分给了贫下中农,他们一家被撵到汤帝庙里居住,汤帝庙正殿如今是村委办公处,右厢房就是他从前的家,宁宇就在这间房子里长大,左厢房完全坍塌了,和正殿对着的戏台也剩下了一个架子,且歪斜的很厉害,宁宇说,他正在呼吁这座古戏台的修复,只是人微言轻,说的话没人听。不知道当年扭曲人性的岁月给宁宇的心灵留下过怎样的创伤,能看到的是他的另类和狂放,或者称呼他乡间异人更准确些。
宁宇指着关帝庙远处的一片新房说:“我住的地方多好啊,视野多开阔,我父亲叮嘱我,这辈子不要修房,说要那些干什么,一土改还不都是别人的。我在破庙里一样要长大。住在没有人和你争的地方,多安心”。宁宇的父亲80岁了,现在是中国老年书法家协会的会员。老人写的一笔好字,所有的宫观寺庙,门前挂着说明文字,都出自宁宇父亲的手笔。而所有景观门口用原木做的匾,正是宁宇的创意,算是富贵留痕了。
从良户出来,宁宇带我们向明代古堡蟠龙寨走去,也就是老乡们说的寨上。田逢吉的侍郎府就在这座盘龙寨。蟠龙寨距离良户只有几百米,却是一个独立的村落,寨门高大雄伟,原本有一围寨墙和寨门一般高,后来都被拆掉了。如今存在的一截是新修复过的。
来到侍郎府门前,一眼就看到照壁上被田家后人砸掉的蟾,根据遗存的线条,似乎更像一条麒麟,尽管没有了原貌,但能想象出当年这座府邸是何等的富丽堂皇,那些成为残片的砖雕石雕是多么的细腻生动。宁宇告诉我说,文革时期,侍郎府光拆下来的木雕就拉了有整整两卡车。
侍郎府边上有“勋第昭远院”一座,为田家老宅,六宅院、七宅院、秦家东西院。此外还存留着一座院子叫“福善庆”,为田家管家居住的院子,福善庆的佛堂和东宅相连,后有花园,前有书房,曾有一副对联曰:“一勤天下无难事,百忍堂前有太和”。如今只剩了门面尚在,里面的老房子大多已面目全非,不忍细看了。
良户的建筑,证明了封建社会的农村曾经有过的荣华富贵和儒雅风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想象不出我们的农村曾经有过如此气象的奢华,中国的农民们竟然有过这样蕴藉温雅的生存环境,而先人们从官场上退隐之后会这样精心建设自己的家乡。还证明了一个乡村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乡绅们负担着儒学的传承,承载着恩泽乡里教化一方的社会责任,为朝廷培育出了许许多多的栋梁之才。证明了那时的农民活得有尊严,有希望。农民的子弟只要苦读,就有可能鱼跃龙门,身价百倍,由十年寒窗而一朝显赫。证明了乡村所以能世世代代繁荣发达,皆因汇集了社会所有的元素和功能,而这一切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定和谐是多么重要的啊。惟其如此,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人文历史才会绵延数千年,如浩浩大江川流不息。
宁宇感叹说,几千年来,无论怎么改朝换代,历朝历代都会自觉的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即便是外族来掌握政权也概不例外,如金代,元代,清朝,都没敢仗着手握生杀大权而无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都会尊孔重教,尊重历史,唯有当今不同……
良户的前人为后人留下的古建筑本是一只聚宝盆,可让良户今天直到往后的家家户户衣食无忧,坐享其成。但在历史大潮的胁迫下,不肖子孙们亲手把这只聚宝盆给毁掉了,他们毁掉的不只是个人的财富子孙的未来,更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结晶。被抛尸荒野的先人们,假如在天有灵,会怎样看待不肖子孙种种不可饶恕的罪孽呢。画册上说良户是风水宝地,但曾经的风水被如此破坏后还会是宝地吗?
宁宇说,文革是对中华民族文明遗存的一次灭绝性的破坏,而比文革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新农村建设,农民们没有文化,不懂的旧建筑的价值,再加上家家户户娶媳妇,女方都要求男方必须有新房,所以许多人家拆了旧房盖新房。后来懂得旧房子值钱了,又因为没有文化,盲目的自己修复,用瓷砖,用水泥,用所有自己认为是好东西的东西,结果呢,只能是进一步破坏。
路过白爷宫,我看到了里面贴满红色瓷砖的外墙,已然没有了任何价值,只能作为一个遗址看了。
还有一户人家的堂屋,原本是金元时期的建筑,被返修成了普通的民房。宁宇说,在保护文物方面,还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旧房子的确不好住了,潮湿,阴暗,这也是事实。老百姓要想住的舒适点,免不了会拆掉旧房子改建新房子。政府号召保护文物,可保护是需要钱的,没有钱光说一句话管什么用。
看到侍郎府的后院旧堂屋变成了三层丑陋的红砖楼,真为屋主人感到痛心。良户到处有这样的红砖新房,与青砖青瓦的古村落显得格格不入,有些大煞风景。宁宇说他曾经劝阻村民不要用红砖,但是没有人肯听。于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古村落在文革灭绝性破坏之后继续被新农村建设破坏着。
和宁宇告别了,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走出村口,停下车来回头又看了一眼良户,巨大的广告牌子上写着: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良户。然而承载着中国历史文化的良户,曾经的古建群已然废墟一片,这片废墟在萧索的冬日里无言地诉说着,它以自己尴尬的存在方式,记录了灿烂的中华农业文明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
良户村口沿河道修了仿古的亭台和廊坊,河床干涸,沿河堤散落着刺眼的各色垃圾……,华丽的现代古建映衬着满眼不可挽救的残败和颓废……想象良户的当年,四围有青山环绕,一条清澈的河水,辉映着华美的村落,古木森森,田亩齐齐,书声朗朗,春去秋来,四时八节,晨钟暮鼓,敬畏天地君亲师,老有养,幼有教,病有医,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牛羊鸡犬,士农工商,各得其所,该是多么和谐,多么的美好,与大自然的节拍是多么吻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又该是多么舒心惬意……
相信良户的命运只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缩影,普天之下被文革和新农村建设毁掉的良户一定不在少数,中国大地没有一个角落能躲过这一场又一场的劫难,而中国的农村自此一衰再衰,美丽的自然村多是田地荒芜,房倒屋塌,难怪有学者说如今是‘国在山河破’,细想来这话不是戏虐,而是事实。
如今的良户村在村口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牌坊,看上去造价不菲,但无论花多少钱来恢复,美仑美奂的良户原貌是永远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