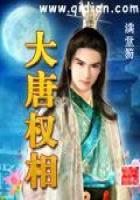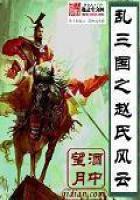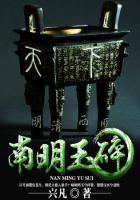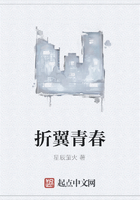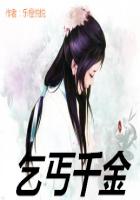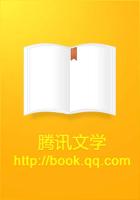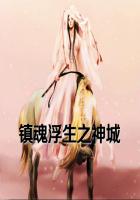第十四节 西夏信访工作制度探索
西夏作为西北地区一支带有少数民族色彩的地方割据势力,在其建国前后,模仿唐宋制度,建立了一整套符合西夏党项羌族民族特点的制度,信访工作制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从目前对西夏史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西夏文书、秘书、档案的研究仍然是一大弱项,而西夏信访工作制度就更薄弱了。本文拟就西夏信访工作制度作一粗浅的探索,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西夏信访工作制度的渊源
信访工作制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为我国制度建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总体上来看,历代统治者为了防止官逼民反,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多不同程度地注意体察民情,设置有听取臣民建议、接待百姓申诉冤屈的官职或信访机构。
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有了进善旗、敢谏之鼓等方式,由部落联盟首领直接听取民众的意见,开我国信访工作之先河。据《大戴记·保傅》《淮南子·主术篇》等古籍记载,尧在位时,曾于庭前设置“进善旌”,舜继位后,由于事务日繁,无暇顾及,就在庭前设置“敢谏之鼓”,允许民众击鼓,建言陈事。舜时的纳言,其职责之一是“听下言纳于上”,兼管信访事务。西周初年,周公下令在朝门外设置“肺石”,并号令民众:“凡远近孤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然后通过“士”将情况上报六卿或天子,这里的“士”就是专职的信访官员了。约自晋代始,设置“登闻鼓”,一直沿用至清代,成为信访活动中一项重要制度。据《文献通考·刑考》记载,隋代已将击鼓者申诉的内容由专人记录下来,上奏皇帝,这可视为信访活动中登记制度的起始。秦汉时,宫城外门设有公车司马令一职,其副手为公车司马丞,他们的职责之一是接待和安排上书或请求面见皇帝陈言的吏民,也是兼管信访事务的官员。隋代,炀帝设置了谒者台,以谒者大夫为主官,下隶有通事谒者等属官,负责吏民申奏冤屈等事,可视做早期兼职的信访机构。唐代,武则天时创设起专职的中央信访机构匦使院,并诏令各州县,凡欲进京投书告密者,由州县官府负责供给驿马,沿途以五品官的待遇供给食宿,以保证他们尽快入京投书,并严令各地官员不得查询上访者投书内容。匦使院的设置,首开了一条使民间下情大量上达中央政府的渠道,掀起了一个历史上信访活动的高潮,在此高潮中建立起了比较正规的信访制度,如接待人员在受理上访时,须及时办理,否则,将受处罚;上访投书,须备两份,正本呈皇帝,副本交知匦使。宋仿唐代匦使院,设立鼓司,受理天下投书。中央信访机构分为两个,鼓院为初级机构,检院为高级机构,隶属门下省,规定吏民须先投诉鼓院,遭拒绝或认为处理不公,可再至检院上访,使上访者多了一个申诉机会,以防被一个部门所压制,同时也使信访机构相互制约,趋于合理。检院处理上访案件,规定急事当天将奏报皇帝,一般的每5天呈进一次。后又专置匦函,命御史中丞为理匦使,负责处理屡经申诉而未得解决或事关机密的投书,相当于今天专门处理老大难信访案件的小组。这都说明信访制度已很严密,臻于完善。
西夏的信访工作制度是怎样的呢?据《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但是,在建国初期,元昊的建官立制等,并不是简单、机械地去照搬宋朝的文化制度,而是根据党项社会政治、经济的实力状况,有取舍地吸收、学习,把宋朝的典章制度与党项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加以改造,变为适合本民族性格的东西。如,元昊把宋朝的礼乐制度加以简化,礼九拜改三拜,乐五音改为一音,以适应“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蕃俗”。在官僚机构上,元昊将宋朝的24司改为16司,“仿宋制,置尚书令,考百官庶府之事而会决之”。唐宋朝仪,“以元日、五日朔、冬至行大朝会礼,群臣上寿,设宫县万舞,其常朝仪,百官入赴文德殿,正衙,曰常参,五日赴崇德殿,曰起居”。元昊将其改为六日为常参、九日为起居。元昊的措施中,也有完全摹仿宋制的,但却不是主要方面。西夏仁孝时期,是西夏国发展的鼎盛时期,从其制定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其受中原王朝的深刻影响,信访工作制度也不例外。据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记载,西夏官职分上、次、中、下、末五等司,“匦匣司”属西夏官制次等司中,是主管西夏信访工作的机构,从其名称来看,显然是摹仿唐宋主管信访工作的机构“匦使院”并有所改革而来;从其级别来看,属西夏国次等司,仅次于上等中书省、枢密院,由此可以看出,西夏国对信访工作的重视程度了。西夏的信访工作制度一直延续到西夏灭亡,甚至对元以后各朝的信访工作制度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西夏信访工作制度的有关内容规定
西夏信访工作制度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西夏《天盛律令》中。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全书二十卷,分一百五十门,一千四百六十一条,其详细程度为现存中古法律之最。法典总计二十余万言,没有注释和案例,全部是律令条文,其内容包括刑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多方位地反映了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给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大量资料”。因此,我们以《天盛律令》资料为主,结合其他汉文文献资料,具体分析一下西夏信访工作制度的有关内容。
(一)西夏信访工作制度的程序
第一,不许越司或御前告状。西夏的信访工作借鉴唐宋信访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采取就地解决信访案件的方法,不允许越级到更上一等司或皇帝面前告状。若所属司内无法解决或遭拒绝或处理不公,根据西夏法律规定,才可越司去告状。如“诸人有互相争讼陈告者,推问公事种种已出时”,若属于京城地区所辖范围的,“当告于中兴府、御史,余文当告于职管处,应取状。其中有谓受枉误者时,于局分都案、案头、司吏争讼者当告于所属司大人,应转争讼局分人则转当地大人”。“若所属司问者于大人、承旨有争论时,当入状于匦匣中”,匦匣司官员应按照西夏所规定的信访工作的程序进行处理,即匦匣司官员首先要“当问告者,如何枉误,有何争讼言语,当仔细明之”;其次,根据询问记载的材料,与原所辖司上报的文书进行对比审查,“谓我语之确凿,敢只关则令只关,然后当使所争讼处来文,当仔细审察文字判写”;再次,若原所属司上报文书“与告者语同,有显见之枉误,则当问其问者大人、承旨为谁,有何住滞,而使脱罪”;最后,匦匣司官员“再于所属司大人或转或令问,及全部司别转令问,应如何,依时节告时,应过问,依上谕所出实行”。如果原所属司处理是公正的,并无冤枉之嫌,那么,匦匣司官员要根据有关规定,将告者及上报的文书一并退回原所属司内,依律令执行,“若无枉误语,告者无确凿语,妄避罪日长,囗语上有添补,则当使脱罪,引送前置文处,当综合,依律令语法实行”。
第二,不服原所属司的处理,又另告他处,若推问先判不枉,则告者要承罪。若诸人告状,经所属司处理,但诸人认为不公,西夏法律允许状告他处,但仍要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状告。首先,“诸人因互相争讼而投奔地边,经略使上职管者因种种公事当告原先所属监军司”,如果说“其中谓已枉误而不服,则告于刺史”。其次,状告到刺史处时,刺史大人则要认真对待,“敢只关则当取文而视之”。若确实存在不公之处,刺史则要“于局分争讼者当引送监军司,局分当转之,应遣不争讼之人。于大人争讼,则枉误缘由当有谕文,告于职管经略处”。再次,状告到职管经略处时,按规定“经略争讼人应转则转,当另问于不争讼处。若局分大小皆有争讼,则当转司,当令于附近相邻司内寻问。若无相邻司,则应遣人则遣之,应问于本人则当问之。于律令限期内当判断毕”。又次,若经略局分大小亦有争讼,则必须投书于西夏最高信访机构匦匣司处理,即“入状于匦匣中。枉误语是实,则转司,寻问于本人,应遣其余何人奏时,当过问,依上谕所出实行”。最后,经仔细核对,原所属司处理是公正的,应退回到原所属司去执行,“若无枉误语,则因妄语而令脱罪,引送置文处判断”。
第三,诸司争讼不决,入状于匦匣,匦匣司判枉,上报中书、枢密,仍不决,可告御前。如果诸司官员处理信访案件不公,有冤枉之嫌,最后入状于匦匣中时,匦匣司官员处理时同样亦出现枉误,而告者不服,这时“则当依文武次第报于中书、枢密”,中书省、枢密院的官员按照一定的程序“只关取文、司局分大小转承次第等,匦匣司人当告依法为之”;若中书省、枢密院官员处理同一起信访案件,同样“亦枉误,则可告御前而转司,另遣细问者奏量实行”;若其中无故越司而告御前并击鼓鸣冤等时,则“徒三个月,情由当问于局分”。
第四,西夏时期,特别是西夏中期,西夏统治者为了赢得民心,巩固其统治地位,对信访工作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即于宋绍兴三十二年(夏天盛十四年、公元1162年)“冬十月,移中书、枢密院于内门外”,将西夏国最高军政机构中书省、枢密院从朝堂内移置于朝堂外,使西夏国的两个最高机构及其官员能经常接触并听到最下层诸人的各种声音,并能随时处理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其政令畅通,深入人心。这正如清代学者吴广成给“冬十月,移中书、枢密院于内门外”这句话作的按语那样:“自古君臣一德,无殊家人父子。自叔孙定朝仪,冠履之分严,堂阶之情隔,于是朝有数,见有时。延及后世,遂有不御朝、不见臣下之弊矣。今仁孝励精图治,恐见闻未及,将中书、枢密院移置内门外,以便顾问,则上无勿知之隐,下无不达之情,夏政之善可知矣。”吴广成的这个按语是针对西夏政治制度亦即信访工作制度方面所作的评说。这个按语分析了仁孝移中书、枢密院于内门外,使上下之情相通的作用。这是对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励精图治、勤劳政事的颂扬。由此也可见西夏信访工作制度之完善和严密。
(二)西夏信访工作中违律的处罚规定
西夏《天盛律令》规定,信访工作过程中,对信访官员总的要求是:办事公正无私,仔细认真,防止各种冤案的出现。若在信访工作过程中,不按规定执行而导致出现偏袒枉误、贿赂徇情等种种违反律令的行为时,要依据不同情况进行处罚。
1.若信访人员对被上访人员所告之事“未问显明”,但过后又不许被上访人员超越本司另告他处而不告于局分,则“告者、取状者等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若有如此之事,信访人员应“当引送先所告处,立便问之已明时,先告者有不服,及问语已明而判断时不服,诸司有告者勿判断其语,当再问之”;若已告别司,但经别司寻问,与“前语同而不枉”,这属于有罪人无理陈告,扰乱社会,则要加重处罚,“与前有罪上徒五年以内者加一等。有自徒六年以上罪者,不需于现承罪上加之,而依为伪证法,获徒六年时笞六十,获三种长期、无期徒刑等笞八十,应获死罪笞一百”;若有罪人加重处罚之后仍然表示不服,于是“派儿子、兄弟令陈告者”,再次申冤,西夏律令规定,“由应当问者行问。当问本人,肯只关则重行推问陈诉,前已枉未枉罪依前所示法为之,儿子、兄弟罪勿治。若犯罪者未放而有空名,则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若有罪人不肯,儿子、兄弟自告,则不许取状推问。违律时,取状、告者等一律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
2.信访官员未受贿徇情,但调查寻问不彻底,致使判断定罪时出现了差错,同样要治罪,“诸司局分大人未取贿赂,未徇情,当事人未聚集,问情不足,欲断局分问者之语,谓依官方及大人指挥当脱之,以威胁语强使脱之时,获死罪及长期徒刑者徒三年,短期徒刑自三年至六年者徒一年,自徒二年至徒一个月者十杖,获杖罪勿治”。
3.信访官员因受贿而徇情枉法,导致枉判错判,造成影响者,更要处罚,但要视不同情况而治罪:被上访人员本来无罪而治罪,是杖罪而判劳役,有劳役者为长期徒刑,获长期徒刑而令承死罪等时,“枉者当承全罪”;有杖罪而加杖数,应获劳役而加年数,是三种长期、无期徒刑而依次加之等时,“枉法者当自承所加之罪。原本犯罪者自身所有罪行依法判断,勿使枉者承之”,若不应革职,无理相怨而加罪以革其职,或虽应革职而减罪则不革职,“与此次第加之而多黜其官,多加其黥,又不应黥而黥之等,于同等枉法罪状各加一等判断”;“有重罪者减半,亦所减半多少,由枉罪者自承之”;“前述罪既加,已使受黥杖,已超前罪,则当去所受之黥。以自身实罪而应受黥者,依前所受,不需再为之。其中已减罪,有使受轻罪之黥杖,则依原先实有重罪应获之黥杖劳役而承之,当去前黥”。
4.因受贿而枉判公事或者说根本未判断者,其处罚则“依前判断所至之罪状依次减一等”。其中受贿数目太大时,则与枉法贪赃罪比较,要“从其重判断”。
5.判断上访案件时,信访官员“虽未有贿,然徇情以枉公事者”,而且冤屈的确很明显,其处罚“则与取贿而枉公事罪状相同”。
6.诸局分官员在寻问判断公事中,即“未取贿赂”,又“未徇情”,虽然说寻问诉讼人情节充足,“然未得实情,无理判断等罪,依所定判断”:“问讯已足,知情人皆已问而同之,被告人谓‘我服罪’,实话未准而判断误者,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问讯已足,实话已准,律令语法分明时,推寻误而增减罪情,犯十恶罪中以重为轻者,局分大小致误者与枉法罪相同。除此之外,获死罪、长期徒刑、短期徒刑而加之,则比枉法罪减二等,减之则减三等,判断未至则依次再减一等”;“问讯已足,实话虽已准,然彼之罪于律令不明,轻重当判为何未得,应奏报时,其处判断未受贿徇情而加之,则比枉法罪减三等,减之则减五等”。
7.诸司信访官员在判断公事时,“由司内大人当面指挥。指挥语未暇予之,不许预先遣人取证据物。违律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证据物当予举报者,予物者罪勿治”。
8.信访工作中,同样存在保密工作,因此,西夏规定,“诸局分所判断公事及所行种种他语等,所定未明,此时不许预先于他人处宣说。违律于他处谈论时,预先谈论所告语者徒二年,说诸司判断语者徒六个月,其中微语杖罪时,他处说者七杖。有于局分处推究者,亦与说者相同”。
综上所述,西夏国摹仿唐宋设置信访机构,并开展信访活动,建立了完善而严密的信访工作制度,这对西夏统治阶级了解民情、调整方略、制定政策、整肃吏治、缓和各种矛盾、稳定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西夏国信访工作制度对我们今天的信访工作同样是有借鉴意义的。
(原载《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