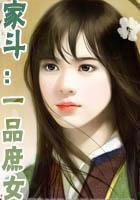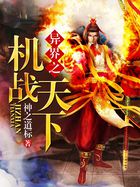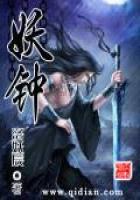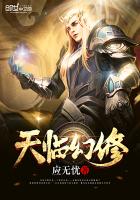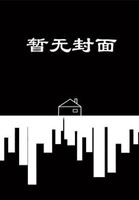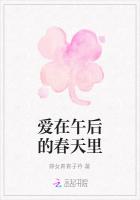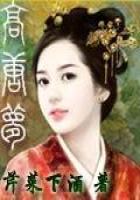《燕燕序》云:“卫庄姜送归妾也。”《笺》云:“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於是大归,庄姜远送於野,作诗以见志。”余按:此篇之文但有惜别之意,绝无感时悲遇之情。而《诗》称“之子于归”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闻有称大归为於归者。恐系卫女嫁於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绝不类庄姜、戴妫事也。自庄公之立至是已三十有九年,庄姜、戴妫恐不复存。《史记》以为戴妫先死而後庄姜以桓公为己子,虽未敢必其然,然献公之出也定姜见於《传》,其入也敬姒见於《传》,而记桓公之弑,州吁之杀,绝无一语及於庄姜、戴妫,若无二人然者,则二人固未必存也。且庄姜既以桓公为己子矣,庄姜当大归,何以大归者反在戴妫?而古者妇人送迎不出门,庄姜亦不应远送於野也。又按:《鲁诗》、《韩诗》及《列女传》皆以此为定姜所作:或以为献公无礼於定姜,故定姜作此;或以为定姜归其娣送之而作;或以为定姜送妇作。然以词意观之,时势考之,皆未有以见其必然。盖皆各以其意揣度言之,是以参差不一,皆未可执以为实也。说并见前条下。
《终风》非庄姜伤己遭州吁侮慢诗
《终风序》云:“庄姜遭州吁之暴,见侮慢不能正也。”余按:州吁,弑君之贼也;庄姜,妇人,不能讨则已耳,岂当爱之而复望其爱己。乃曰:“顾我则笑,谑浪笑傲。”此何言也而可以出之口!曰:“寤言不寐,愿言则怀。”此何人也而可以存此心!庄姜果赋此诗,一何其无耻乎!朱子《集传》固已觉其不合,乃以“终风”为指庄公。然比之以“终风且暴”,斥之以“谑浪笑傲”,皆非庄姜所当施之於庄公者。且既谓庄姜不见答於庄公矣,又何以有“顾我则笑”之语?详其词意,绝与庄姜之事不类,是以施之於州吁不合,施之於庄公亦不合也。窃谓年远事湮,《诗》说失传者多,宁可谓我不知,不可使古人受诬於千载之上。说并详前两条下。
击鼓非州吁伐郑事
天下之事有我所知,有我所不知。不可谓有所知者已尽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断无有在我所知之外者也。《击鼓》一诗,序以为“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则是即《春秋》鲁隐公四年四国伐郑事也。然今考之《经》文则大不然。凡两国不相和而为和之曰“平”,《春秋》“平莒及郯”、“卒平郑、卫”是也。今也卫自伐郑以媚宋耳,而诗乃云“平陈与宋”,宋与陈初无隙也,何平之有!东门之役,五日而还,不为久也;秋而再伐,州吁旋死,则亦旬月而还师矣。而诗乃曰“爰居,爰处,爰丧其马”,苟非师老岁淹,暴露已久,何至为是言乎?细玩此诗,其非州吁伐郑之事明甚。盖《春秋》之始上去平王东迁已四十有九年,其间诸侯交兵之事盖多有之,但不见於经传,无可考耳。我所未知遂谓必无是事,凡所言者皆我所知,苟取其近似者而附会之,呜乎,何其谬也!且卫有孙氏,卫之世卿也,故曰“从孙子仲”。《序》乃以为公孙文仲,亦误。朱子《诗传》不驳其失,以为或然,固已异矣。乃後人之复为委曲弥缝其说则尤大谬。或云“先和陈、宋而後进兵”,然则何以不言其後而但言其先?或云“自夏而秋仅隔一时,必帅师在途,又闻後命,未得班师故也”,然则《春秋》何以两书伐郑?且卫与郑数百里耳,五日而还,不匝旬而至国矣,何至历三月而犹未归乎?嗟夫,但欲曲护前人之失,遂不顾其说之不通,古人之诗其晦於後人之说诗者岂可胜道哉!
《式微》、《旄丘》非黎侯寓卫事
《式微序》云:“黎侯寓於卫,其臣劝以归也。”《旄邱序》云:“责卫伯也: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於卫;卫不能修方伯连帅之职,黎之臣子以责於卫也。”余按:《春秋》宣公十五年《传》文,酆舒杀晋伯姬,晋侯将伐之,伯宗斥酆舒有五罪,而夺黎氏地居其一焉。其年,晋侯灭赤狄潞氏,立黎侯而还。则是黎之失国在鲁文、宣之世,酆舒为政之时,上距卫之渡河已数十年,黎侯何由得寄於卫,卫亦安能复黎之国乎?其时不符,一也。黎在山西;卫在山东。而诗乃云:“狐裘蒙茸,匪车不东。”方欲西归而反以“不东”为解,岂非所谓“北辕将楚”乎!其地不合,二也。且黎既失国,则其故土为狄所据,黎侯安能归国,而其臣乃劝之?卫自宣公以後日就微弱,而狄日以强大,晋文、襄之盛且不暇於制狄,而奈何以之责卫乎?细玩诗词,或果有邻国之君寓於卫,或别有所指而传者失之,均未可知。说《毛诗》者但见《春秋传》有夺黎氏地及立黎侯之事,未暇细考,遂附会而为之说耳。後人乃强为之解,谓黎侯凡再失国,黎侯寓在卫东,故云“匪车不东”,欲以曲全《序》说,谬矣!
《新台》、《二子乘舟》非卫宣公及、寿事
《新台序》云:“刺卫宣公也:纳之妻,作新台於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二子乘舟序》云:“思、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其事盖本之《春秋传》。然诗所言殊与《传》所载者不类。何者?,宣公之子也。以父而夺子妻?禽兽行也,此真所谓“言之丑者”。乃但笑其“蘧除”、“戚施”,若憎宣公之老且丑者,少知名义者肯为是言乎!既至而知其美,故夺取之。未至而先筑台,又不於国而於河上,欲何为者?寿死於盗,始至莘,诗何以称“二子乘舟”?自卫至齐皆遵陆而行,特济水时偶一乘舟耳。既非於河上遇盗,何不言其乘车,而独於其乘舟咏之思之?细玩二诗之词,与《传》所载、寿之事了不相涉,其非此事明矣。
《左传》记宣公夷姜生急子事不可信
然即《传》文亦有未可以全信者。宣公之立在鲁隐公四年,石蜡既杀州吁,迎於邢而立之。而《传》称宣公於夷姜,生急子(即《序》之)。谓於夷姜在为公子时乎,则当庄、桓之世必不敢,而在邢又不能。且石蜡讨贼立君,亦必择其贤者,左公子氵曳,右公子职,何人不可以立,而必立此淫乱之人乎?谓於夷姜在已为君後乎,则宣公在位仅十有九年,急子之娶少亦当十四五岁,早亦当在宣公十六七年之时,则宣公卒时寿、朔皆尚在襁褓,寿安能盗旌而先?即朔亦不能构急子也。此乃必无之事,昔人固有辨之者矣(偶忘为何书何人之说。〔通世按;此说见明沈起元《左灯》,而《左传孔疏》亦既疑之矣〕)。盖缘《左传》一书采摘太广,但有所得,即缀於篇,而不暇辨其是非虚实。况此事乃後日所追述,非若朝聘侵伐,史臣按月而书者此,固未可尽执为实也。嗟夫,《左传》犹不能以无误,况於《诗序》,乌在其可以尽信乎!
《诗序》惟《风》多得实
《诗序》惟《风》多得实。《定之方中》,《经》有明文,《载驰》,《传》有明文,不待言矣。《柏舟》以为共姜自誓之诗。今玩其词,“我仪”、“我特”之称,“之死靡他”之语,其为妇人守贞不贰之作无疑;而“{髟}彼两髦”属之於世子,语亦符合。此必有所传而云然,非揣度而为之说也。《墙茨》、《偕老》、《鹑奔》三篇,以宣姜、昭伯之事当之,虽无确据,然玩其词意与其事正相合,序说近是。惟《传》以《鹑奔》为假惠公之言以刺之,尚恐未然。观其称“君”而不称母,或卫之群公子所作,未可知也。《ぐ》以下三篇亦得诗意,但时世则未可知耳。唯采《唐》说者多疑之;说见後条。
卫俗非郑所能及
《郑风》二十一篇,男女相悦者不下十篇,其守正不淫者一篇而已。《风》凡十篇,贞者一篇,淫者一篇,而刺淫者乃至四篇之多。卫俗非郑能所及也!且《东门》不过自明其志而已,未尝敢斥淫者之失。而《》乃云“不可道”,“言之丑”,“子之不淑”,“人之无良”,“大无信,不知命”,深斥痛绝,至於如是,何哉?盖风俗所在,虽贤人亦无如之何。彼既习於淫矣,而有一守正者出焉,方且嫉之笑之,求得免焉足矣,何敢反以责人。若公然深斥之,痛绝之,不一而足,则是先王之礼教犹存,民间之风俗未坏,贤者多而不肖者少,见无礼者群然怪之,是以绝之斥之而无所忌,人亦以为是而传而诵之也。吴季札云“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岂不信与!吾故读《墙茨》、《君子偕老》、《鹑奔》三篇而知卫之必亡,而又知卫之必将复兴也。至其立言之妙,则《墙茨》、《君子偕老》二篇为最。《墙茨》一篇初不明斥其恶,而但云“不可道”,“言之丑”,不言之刺甚於言矣。《君子偕老》先从对面著笔,而以“象服是宜”一句跌醒,然後用二语点出主意,笔法之巧,最耐咀嚼玩味。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良不诬也。《相鼠》刺无礼仪,亦足以见风俗之美。
《桑中》等篇作诗者无刺意
《诗序》云:“《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於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吕氏祖谦云:“诗之为体不同,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此类是也。”严氏粲云:“或以《桑中》为淫奔者所自作,则非所谓止乎礼义矣。当从国史所题以为刺也。”朱子《诗序辨说》云:“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又云:“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已。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又云:“以是为刺,不惟无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余按:《桑中》一篇但有叹美之意,绝无规戒之言。若如是而可以为刺,则曹植之《洛神赋》,李商隐之《无题诗》,韩之《香奁集》,莫非刺淫者矣。夫《子虚》、《上林》,劝百讽一,古人犹以为讥,况有劝而无讽,乃反可谓之刺诗乎!余尝细核《序》文,比其前後而参观之,同一题为刺而其文互异。《新台》以为刺宣公,则其文云“国人恶之而作是诗”。《南山》以为刺宣公,则其文云“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诸如此类,《序》以为作诗者之刺其君,文甚明也。若《桑中序》首言“刺奔”而下但言“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远序》首言“刺荒”而下但言“哀公好田猎,国人化之,习於田猎谓之贤,闲於驰逐谓之好”,《丰序》首言“刺乱”而下但言“婚姻道缺”,《著序》首言“刺时”而下但言“时不亲迎”,皆无一言及於诗人之剌之者,与《新台》、《南山》诸篇之文绝不类。疑作《序》者以录此诗於《国风》中以垂戒於後世故谓之刺,未必果谓作此诗者之刺之也。《凯风序》云:“美孝子也。”而诗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为美之乎?抑为责之乎?疑《序》亦以录此诗为美之,非以作此诗为美之也。《静女》、《有狐》之“刺时”,《溱洧》、《绸缪》之“刺乱”,恐亦皆当如是,正不必曲为说以附会之也。
《干旄》访贤才
卫之重封,由於齐桓。齐桓所封者,邢与卫也。然邢仅二十馀年而遂亡,而卫历春秋及战国秦又数百年而始亡,何哉?吾读《干旄》之篇而知卫之所以久存良有由也。盖国家之治惟赖贤才,而贤才不易得,故人君於贤才不惟当举之用之,而且当鼓之舞之。旌旄之贲於浚,所以下贤也,即所以劝贤也。下贤,则有以咨诹治道。劝贤,则人皆争自濯磨而贤才将不胜其用。故季札至卫,而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君子之所以多,正由其君好贤,因而其卿大夫咸知下士,躬访贤才於畎亩中,以故人皆竞於贤耳。是知立国之规模未有不在於好贤者。读《诗》者能以此篇例之,则授之以政而无不达者矣。
《硕人》非闵庄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