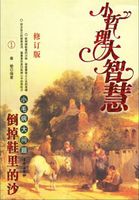也因了这层销售业务关系,我们的接触日益增多。接触越多,越觉得她待人真诚与友善的人格魅力。每次去送货、结账,她总是笑脸相迎,泡茶、敬烟、递槟榔,用的是星城人的全套礼数。彼此交谈,她也不像别人直奔生意主题,而是先嘘寒问暖,再慢慢导入。我常常想,对我这个下游客户尚能如此,更何况上游客户,足见她对客户的亲和力。送货是有经济学的。有的客户为不占用资金,每次要货少,要货次数多,这样就增加了我的送货运费成本。而她总能计划一周或一旬的常用量,每次要货多,要货次数少,这样就减少了我的送货运费成本。我常常想,这不单是出于女性的细腻,更多的还是设身处地想别人。结账也是有经济学的。“精明”的客户是占用货款,拿别人的资金赚自己的钱。而她总能在约定的时间足额付清,从不拖欠,也不抹货款尾数,就是星城人说的“打板子”。总之与她交往,你不会感到生意人之间的尔虞我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心里不必设防,怎么着你都放心。
接触越多,越觉得她在同行里的出类拔萃,尤其作为女性,更属凤毛麟角。她原是星城一家国企技艺精湛的车工,在改革开放初期,跟随父辈扬帆下海,创办了的这家机械加工厂。民营企业灵活的经营机制,精益求精的技术加工,急客户所急的服务精神,让她的厂没几年就声名鹊起。不但收益上大有斩获,而且培养了一批批精干技工。这些精干技工中的佼佼者,羽翼丰满后,又一个个开厂成了老板,客观上又推动了这个机械加工业的发展,适应了汽车修理行业的需求。工厂由她经营管理后,凭借积累的客户资源与经验,驾轻就熟,她一样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因为每月要去几次工厂,常常耳闻目睹她的风采。说她是老板,却又是十足的“全武行”,车间哪里活紧,她就在哪里顶岗。顶车工,她得心应手,娴熟的技艺让车轮飞转;顶清洗工,在满池油污中作业,她不怕脏也不怕累。清理工装模具、打扫铁屑卫生,甚至食堂帮厨,在她眼里,总有干不完的活。常常还要驾车外出揽业务,拉回一车车要加工的活,又送出一车车加工过的活。难得有坐办公室的时间,进入办公室,往往也是接待客户,接业务电话,或记账结算。我常常感到惊讶,一个瘦削的女性,何以如此大的能量?浑身上下总像有使不完的劲,总是洋溢着一种激情,一股感染人的力量。她是工厂的灵魂,有她领军,工人们总是那样紧张而有序地工作着,工厂总是那样机器轰鸣,生机勃勃。
也许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家族企业原因,去年,她移交了经营权,离开了为之倾注青春激情与勤奋汗水的工厂,赋闲在家,相夫教子。从过去火热的工厂生活中走过,回归到狭小静谧的家庭,我想,她会有一段时间的心理落差。好在她能很快适应新的生活,每日里恪尽家庭主妇职守,然后上上网,与网友聊聊天。还参加了自行车车友会,隔三差五地与车友们结伴出游,最好的成绩是自行车能一气骑上岳麓山。五月去台湾旅游,九月又计划去西藏,还发奋学英语,准备赴西欧领略域外风情……。看她网上晒出的图像,人比过去胖了,但却依然青春洋溢,风采照人。在她身上还是可以看到过去的那样一种劲,那样一种激情,充满着对人生的感悟,对生活的热爱。
尽管她离开工厂后,我们少有交往,但也许是我与她有一些相似的人生经历,也许都是性情中人,也许彼此珍惜与收藏着友好,我们终又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后来,又成了兄妹。只是我在称呼她上颇费了一番思量,还叫X总吧,显得生份;直呼其名吧,又太随意。有次网上聊天突来灵感,取其网名的第一个汉字以冠之,就叫阿妹吧。
于是,也就有了这篇文章。
“血梯”
王统照
中夜的雨声,真如秋蟹爬沙似的,急一阵又缓一阵。风时时由窗棂透入,令人骤添寒栗。坐在惨白光的灯下,更无一点睡意,但有凄清的、幽咽的意念在胸头冲撞。回忆日间所见,尤觉怆然!这强力凌弱的世界,这风潇雨晦的时间,这永不能避却争斗的人生……真如古人所说的“忧患与生俱来”。
昨天下午,由城外归来,经过宣武门前的桥头。我正坐在车上低首沉思,忽而填然一声,引起我的回顾:却看几簇白旗的影中,闪出一群白衣短装的青年,他们脱帽当扇,额汗如珠,在这广衢的左右,从渴望而激热的哑喉中对着路人讲演。那是中国的青年!是热血沸腾的男儿!在这样细雨阴云的天气中,在这凄惨无欢的傍晚,来作努力与抗争的宣传,当我从他们的队旁经过时,我便觉得泪痕晕在睫下!是由于外物的激动,还是内心的启发?我不能判别,又何须判别。但桥下水流恬恬,仿佛替冤死者的灵魂咽泣,河边临风摇舞的柳条,仿佛借别这惨淡的黄昏。直到我到了宣武门内,我在车子上的哀梦还似为泪网封住,尚未曾醒。
我们不必再讲正义了,人道了,信如平伯君之言,正义原是有弯影的(记不十分清了姑举其意),何况这奇怪的世界原就是兽道横行,凭空造出甚么“人道”来,正如“藐姑射的仙人可望而不可即”。我们真个理会得世界,只有尖利的铁,与灿烂的血呢!平和之门谁知道建造在那一层的天上?但究竟是在天上,你能无梯而登么?我们如果要希望着到那门下歇一歇足儿,我们只有先造此高高无上的梯子。用甚么材料作成?谁能知道,大概总有血液吧。如果此梯上面无血液,你攀上去时一定会觉得冰冷欲死,不能奋勇上登的。我们第一步既是要来造梯,谁还能够可惜这区区的血液!
人类根性不是恶的,谁也不敢相信!小孩子就好杀害昆虫,看它那欲死不死的状态便可一开他们那天真的笑颜。往往是猴子皮气发作的人类(岂止登山何时何地不是如此!),“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的话,并非苛论。随便杀死你,随便制服你,这正是人类的恶本能;不过它要向对方看看,然后如何对付。所以同时人类也正是乖巧不过,——这也或者是其为万物之灵的地方。假定打你的人是个柔弱的妇女,是个矮小的少年,你便为怒目横眉向他伸手指,若是个雄赳赳的军士,你或者只可以瞪他一眼。在网罗中的中国人,几十年来即连瞪眼的怒气敢形诸颜色者有几次?只有向暗里饮泣,只有低头赔个小心,或者还要回嗔作喜,媚眼承欢。耻辱……耻辱的声音,近几年来早已迸发了,然而横加的耻辱,却日多一日!我们不要只是瞪眼便算完事,再进一步吧,至少也须另有点激怒的表现!
总是无价值的……但我们须要挣扎!
总是达不到和平之门的……但我们要造此血梯!
人终是要慷厉,要奋发,要造此奇怪的梯的!
但风雨声中,十字街头,终是只有几个白衣的青年在喊呼,在哭,在挥动白旗吗?
这强力凌弱的世界,这风雨如晦的时间,这永不能避却的争斗的人生……然而“生的人”,就只有抗进,激发,勇往的精神,可以指导一切了……无论如何,血梯是要造的!成功与否,只有那常在微笑的上帝知道!
雨声还是一点一滴的未曾停止,不知那里传过来的柝声,偏在这中夜里警响。我扶头听去,那柝声时低时昂,却有自然的节奏,好似在奏着催促“黎明来”的音乐!
可怕的冷静
闻一多
一个从灾荒里长成的民族,挨着一切的苦难,总像挨着天灾一样,以麻木的坚忍承受打击,没有招架,没有愤怒,甚至没有呻吟,像冬眠的蛰虫一般,只在半死状态中静候着第二个春天的来临,——这样便是今天的中国,快挨过了第七个年头的国难,它还准备再挨下去,直到那一天,大概一觉醒来,自然会发现胜利就在眼前。客观上,战争与饥饿本也久已打成一片了,因此,愈是实质的战斗员,愈有挨饿的责任,不像人家最前线的人们吃得最好昨饱,我们这里真正的饿莩恰恰就是真正的兵士。抗战与灾荒既已打成一片,抗战期中的现象,便更酷肖荒年的现象了。照例是灾情愈重,发财的愈多,结果贫穷的更加贫穷,富贵的更加富贵。照例是灾情严重了,呼呈的声音海外比国内更响,于是救济的主要责任落在外人身上,而国内人士,相形之下,便愈能显出他们那“不动心”的沉着而雍容的风度了。现在一切荒年的社会现象在抗战中又重演一次,不过规模更大,严重性更深刻些罢了。但是说来奇怪,分明是痼疾愈深,危机愈大,社会表层偏要装出一副太平影象的面孔。配合着冠冕堂皇的要人谈话和报纸社评的,是一般社会情绪——今天一个画展,明天一个堂会,“顾左右而言地”的副刊和小报一天天充斥起来,内容一天比一天软性化。从抗战开始以来,没有见过今天这样“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的景象,这不知道是肺结核患者脸上的红晕呢,还是将死前的回光返照!一部分人为着旁人的剥削,在饥饿中畜生似的沉默着,另一部分人却在舒适中兴高采烈的粉饰着太平,这现象是叫人不能不寒心的,如果他还有一点同情心与正义感的话。然而不知道是为了谁的体面,你还不能声张。最可虑的是不通世故而血气方刚的青年,面对这种事实,又将作何感想?对了怕支摇抗战,但饥饿能抗战吗?粉饰饥饿就是抗战吗?如果抗战是天经地义,不要忘记当年的青年,便是撑持这天经地义最有力的支柱,可见青年盲目而又不盲目,在平时他不免盲目,在非常时期他却永远是不盲目的。原来非常时期所需要的往往不是审慎,而勇气,而在这上面,青年是比任何人都强的。正如当年激起抗战怒潮的是青年,今天将要完成抗战大业的力量,也正是这蕴藏在青年心灵中的烦躁。这不是浮动,而是活力的脉搏。
民族必需生存,抗战必需胜利,在这最高原则之下,任何平时的轨范都是可以暂时搁置的枝节。火烧上了眉毛,就得抢救。这是一个非常时期!
从抗战开始到今天,我们遭遇过两个关键,当初要不要抗战,是第一个关键,今天要不要胜利,是第二个关键,而第一个关键本来早已决定了第二个,因为既打算抗战,当然要胜利。但事实上目前的一切分明是朝着胜利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可怪的,是一部分人虽然看出方向的错误,却还要力持冷静,或从一些烦琐的立场,认为不便声张,不必声张。眼看青年完成抗战,争取胜利的意志必须贯彻,然而没有老年人中年人的智慧予以调节与指导,青年的力量不免浪费。万一还有人固执起来,利用他们的地位与力量,阴止了青年意志的贯彻,那结果便更不堪设想了。时机太危急了,这不是冷静的时候,希望老年人中年人的步调能与青年齐一,早点促成胜利的来临!大众的坚忍的沉默是可原谅的,因为他们是灾荒中生长的,而灾荒养成了他们的麻木,有有着粉饰太平的职责的人们是可原谅的,因为他们也有理由麻木。
可是负有领导青年责任的人们,如果过度的冷静,也是可怕的,不这不宜冷静的时候!
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民国三十三年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演讲词
闻一多
诸位!我们抗战了七年多,到今天所得的是什么?眼看见盟国都在反攻,我们还在溃退,人家在收复失地,我们还在继续失地。虽然如此,我们还不警惕,还不悔过,反而涎着脸皮跟盟友说:“谁叫你们早不帮我们,弄到今天这地步!”那意思仿佛是说:“现在是轮着你要胜利了,我偏败给你瞧瞧尸这种无赖的流氓意识的表现,究竟是给谁开玩笑!溃退和失地是真不能避免的吗?不是有几十万吃得顶饱,斗志顶旺的大军,被另外几十万喂得也顶好,装备得顶精的大军监视着吗?这监视和被监视的力量,为什么让他们冻结在那里?不拿来保卫国土,抵抗敌人?原来打了七年仗,牺牲了几千万人民的生命,数万万人民的财产,只是陪着你们少数人斗意气的?又是给谁开的玩笑!几个月的工夫,郑州失了,洛阳失了,长沙失了,衡阳失了。现在桂林又危在旦夕,柳州也将不保,整个抗战最后的根据地——大西南受着威胁,如今谁又能保证敌人早晚不进攻贵阳,昆明,甚至重庆?到那时,我们的军队怎样?还是监视的监视,被监视的被监视吗?到那时我们的人民又将怎样,准备乖乖的当顺民吗?还是撒开腿逃?逃又逃到哪里去?逃出去了又怎么办?诸位啊!想想,这都是你们自己的事啊!国家是人人自己的国家,身家性命是人人自己的身家性命,自己的事为什么要让旁人摆布,自己还装聋作哑!谁敢掐住你们的脖子!谁有资格不许你们讲话!用人民的血汗养的军队,为什么不拿出来为人民抵抗敌人?以人民的子弟组成的队伍,为什么不放他们来保卫人民自己的家乡?我们要抗议!我们要叫喊!我们要愤怒!我们的第一个呼声是:拿出国家的实力来保卫大西南,这抗战的最后根据地的大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