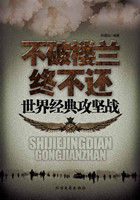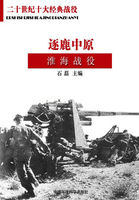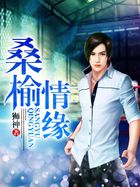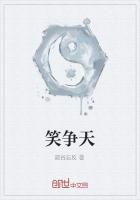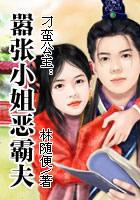黎塞留,法国红衣主教,首席枢密大臣(首相),世界上第一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基人,后来也被人们认为是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之父,黎塞留运用外交战打击败了欧洲如日中天的哈布斯堡王朝,成为法国大陆霸权奠基者,他曾彻底粉碎了华伦斯坦统一德意志的梦想,美国政治家基辛格认为他使德国统一推迟近三百年。黎塞留内政也很值得称道,始终对路易十三忠心耿耿,但他的名声不是太好,法国作家大仲马在《三剑客》中将其形容为奸雄。
现代均势战略发源于17世纪的欧洲。其始作俑者就是法国首相黎塞留,他虽然是天主教的高级僧侣,但却从不让所谓宗教情绪影响法国的国家利益,他曾说过一段在当时令人瞠目结舌的话:“人可不朽,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救赎唯有现下,否则万劫不复。”换一种说法,即国家是一次性的,不论在什么世界里,行王道并没有荣耀可言,国家唯有实力强大,才值得称道。
在政治中,均势、相互制衡战略侧重于“挑拨、制造”对手间的矛盾冲突,使对手在相互间的敌对状态中削弱,保持各自实力上的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彻底吃得掉谁的状态,从而巧妙、有效地使自己得到利益与安全!
自十五世纪后期以来,德国的哈布斯堡家族通过“婚姻外交”,与各国王室通婚,先后继承了许多领地,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尼德兰、西班牙、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等领地均在哈布斯堡的统治之下,新航路发现后整个拉丁美洲也落入哈布斯堡王室手中。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期哈布斯堡是欧洲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大有统一西欧的趋势,法国在它的包围下有被吃掉的危险。
早在16世纪,欧洲天主教内部分裂,一批脱离天主教的新派别因为不承认罗马教皇权威而被称为“抗议宗”,统称“新教”,与被视为“旧教”的天主教相敌对。
这时的法国权力阶层并不想被吞并而失去利益。黎塞留主教强调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这一观念,坚持国家权力高于神权,法国是以天主教文化传统浓厚的国家,法国这时并不把新教各国看作主要敌人,而是把同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看作最危险的敌人。
为了冲破包围,天主教阵营的法国支持新教国家阵营,和丹麦、瑞典、荷兰及德意志新教诸侯国组成反哈布斯堡王朝的集团,并与英国、俄国的结盟。哈布斯堡王朝集团由奥地利、西班牙与德意志的天主教诸侯国组成,并得到罗马教皇及波兰的支持。
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激烈交锋,最后彻底打垮哈布斯堡王朝的欧洲霸权,提升法国势力的正是通过“三十年战争”完成的。
最初,法国正值内乱,无力出兵参战,只能通过外交战。1625年在法国的游说下,丹麦、荷兰和英国三国结成同盟。法国又资助丹麦出兵德国,助新教诸侯反对皇帝,把德国的一场内战国际化,形成国际战争。之后黎塞留又促使瑞典参战。1631年元月13日黎塞留与瑞典签订巴瓦尔德条约,瑞典国王率数万军队进攻德国,法国每年资助瑞典100万里佛尔的无偿援助。为了让德国保持分裂割据状态,黎塞留又劝诱天主教诸侯,包括巴伐利亚选侯马克西米连一世等,使其保持中立。
在民族国家意识的驱使下,欧洲多国卷入到连年不断的战火中,形成这样的结果,或者是形成一些国家称霸局面,或者形成国际间的一种均势。最终18世纪的欧洲,没有哪个国家能强大到吞并别的国家,建立起大帝国的地步;而每当有一个国家可能坐大时,别的邻国就便会联合起来,左右夹击使其削弱。
最终,三十年战争是在1648年以哈布斯堡王朝的失败、法国和瑞典的胜利而结束的。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使德国诸侯各自独立,进一步削弱了皇帝的地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确立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领土、主权与独立等原则,被认为是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也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得以形成,由它决定的国际法也真正产生。
三十年战争后,神圣罗马帝国变得名存实亡。荷兰与瑞士的独立受到保障,而荷兰更成为新的海上霸主。西班牙不论陆战还是海战均告失败,失去了欧洲一流强国的地位。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占有了阿尔萨斯与洛林,获得了欧洲霸主的地位。瑞典国王取得了德意志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土地,一跃成为北欧强国。
德国四分五裂态势的继续符合法国的利益。虽然黎塞留这时已去世几年,但这次反哈布斯堡斗争的胜利,仍应归功于他的均势战略。哈布斯堡王室衰落后,法国霸权代之而起。
因此,均势战略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在一个地区,当一个国家实力,远远超过该地区其他国家实力的时候,那么另外一个地区的霸主,就要帮助这个地区那些实力不够的国家,提高它们的实力,以此来恢复这个地区原有的均势,进而达到不使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成为该地区的霸主的目的。
均势作为一种战略,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假设的,即国际体系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认为独立比权力更重要。对国家而言,要实现均势通常有两种手段,即增强自身的实力,或和其他国家结盟。
国家这一概念本身起源于欧洲。在大多数现代国家里,都存在着日益增强的民主的压力,同时,所有的国家,不管其是否民主,都必须设法鼓动人民,获得他们的支持。
在历史上,大国的战略总是分而治之,寻找均势。大国在初期开疆拓土,一旦固定下来,就会通过在各地区安插不同的代理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大国的高明之处在于使用经济与外交手段进行拉帮结派,小心谨慎地使敌对的力量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马汉曾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斯塔布斯的观点:“不论怎样定义均势,也不论在哪些强国之间有必要保持一种平衡以使弱者不至于为强者压垮,均势是将现代欧洲历史的情节串接起来的首要因素。它是在1500至1800年的三个世纪中最重要的观念。无论上演什么戏剧,均势永远是情节的钥匙。”
英国曾是均势战略的成功的实施者。英国对欧洲大陆的种种干预,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命运。英国的地缘位置特殊,独立于欧洲大陆外,因此不需要在欧洲扩张便能维护其利益;但如果在欧洲大陆出现出没有对手的强大帝国,那么,以英国的资源与地理位置便很难以与之对抗。由此英国一直充当欧洲大陆弱者一方盟友的角色,先是竭力阻挠法国,之后是德国和俄国的欧洲霸主地位。它不断介入,它曾与瑞典、西班牙、荷兰等组成近代欧洲第一个反法联盟,对法国进行遏制,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南征北战,横扫欧洲,几乎建立起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同盟。英国又联合欧洲大陆上其他一些国家,组织反法同盟,经过陆地和海上的反复较量,最终法国失败。在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大陆又处于一种新的均势状态。英国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与巩固。
十九世纪的均衡体系有两种模式:包括英国帕默斯顿、狄斯累里所主张的模式,及德国的俾斯麦模式。英国模式是等到其势力均衡受到直接的威胁后,才开始介入,并且一直站到弱者这一方。英国“分治”的均势战略最为常见,在英国人离开的地方经常会发生血腥冲突:印度与中国、印度与巴基斯坦、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伊拉克与科威特,还有非洲的许多地方。与英国不同,俾斯麦则设法防止挑战发生,它主张尽可能建立交叉重叠的盟国体系,用影响力让竞争者的主张温和下来。而俾斯麦之后,他的均势战略在德国没有继承者。英国模式与俾斯麦模式的区别在于岛国与大陆国家地缘环境不同,大陆国家与其他国家没有地理间隔,因此没有条件等均势遭到破坏,须及早做出安排。在俾斯麦之后,德国从均势维持的角色变成了破坏角色,不断挑起周边战争,并战败,失去了德国统一时所取得的大片土地和人口。原因是德国处在大国包围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具备打破均势的地缘政治条件。岛国的均势也有种种区别。英国的殖民地都远离本土,在美洲、非洲和亚洲都有殖民地,不会对欧洲的均势产生直接影响。日本崛起后,海外殖民地已被列强瓜分完毕,日本只能侵略邻国,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打破了亚洲的均势,引来美国参战。
英国在二战后衰败,美国继承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遗产。美国在欧亚大陆之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均势制造者与破坏者,战争取决于美国的利益。自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运用这一套均势战略,在表面上重视和发展与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巴西等这些大国关系的同时,利用他们之间或他们与其周边次级力量中心之间一切可能存在的矛盾、竞争、冲突,对其进行制约、制衡。如借英、意制衡法、德,借东欧制衡西欧,借乌克兰制衡俄罗斯,借阿根廷制衡巴西,借韩国制衡日本,借巴基斯担制衡印度,借日、俄、印、韩及东盟一些国家制衡中国等等。就连一个二百多万人口,完全夹在中俄之间,距美国万里之遥且并对美国经贸利益几无意义的内陆国家蒙古也紧紧抓住不放,声称做“第三邻国”,战略目的不言自明。即使在欧洲,美国也不能容忍建立独立的欧洲军队。在中东,以色列必须靠美国的支持与援助才能够对抗阿拉伯国家与巴勒斯坦人,而阿拉伯国家为了对付以色列,也离不开美国支持。在另一方面,如果某一范围内没有美国的势力,那么美国就会制造些混乱,使这些国家分裂,使自己变成这一均势的参与者及维持者,使冲突的各方都离不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