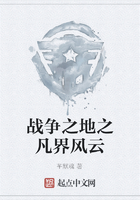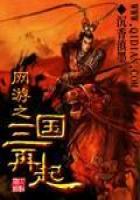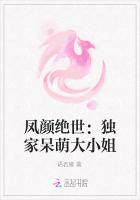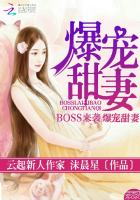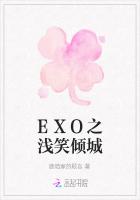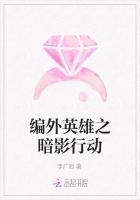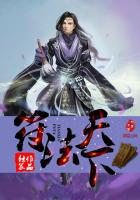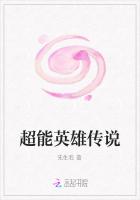一个谷仓里,一群老鼠受到一头恶猫的迫害。老鼠们开了—个会,大家想出了一个办法,一致认为对付这只猫的最好办法是在猫的脖子上挂一只铃。这样,无论猫走到哪里,铃声就会响起来,但问题是派谁去挂钟呢。这是前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在1963年面对以色列威胁时所引用的一个故事,对于当时数量众多,但一盘散沙的阿拉伯国家的一个莫大的讽刺。
政治学中有个著名的“猎鹿博弈”定律,几个猎人联手去围捕一只鹿,猎人如做好分工,抓住鹿的可能性就会很大。这时正好有只兔子从身边经过,其中任何一个猎人只要一转身就能抓到这只兔子,鹿会乘机逃跑,只有抓住兔子的猎子的获得小部分利益,其他猎人将一无所获。显然,这样猎鹿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点,而合作猎鹿的好处要比打兔子的好处大得多。“合作”的道理人人都懂,在实际中很难合作的原因就在于此。
国家作为一个自我生长的组织,一经建立,便会将巩固、追求自身权力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并开始依据领土概念进行统治,如划分与控制边界,统治生活在境内的居民、建立一各官僚秩序等。
国家的权力与地理要素密切相关。地理位置、版图、资源配置等地缘政治要素,对一个国家国家影响力和权力大小有着密切的影响。国家实力取决于领土大小、地理位置,和它所拥有的必要的物质及人力资源等要素。如果将权力比喻成肌肉,那么地缘版图就是骨骼,一个国家实力能强大到哪种程度,还要受其疆域大小限制,它决定着国家实力增长的极限。
“中间地带”一直是强国谋求和维持霸权的根基所在。世界上大部分冲突,都会出现在受大国挤压的地区。霸权国家的势力范围要超越其中心地区,以它们的权力征服较小的国家,包围次强国的势力范围,并相互蚕食对方的边缘地带。
政治家通过研究发现,打击和削弱对手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或分裂领土,使其永久性失去国力增长的前提。由于破碎地带的各政权实力相仿,没有能发挥主导作用的核心,所以谁也支配不了谁,谁也不服从谁,形成一种复杂的斗争不息的均势状态。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汉斯.J.摩根索曾指出:减少较重砝码的方法也体在“分而治之”这一准则中。打算削弱竞争对手或使对手保持衰弱的国家,都采用这种通过分裂竞争对手,或使之保持分裂的分而治之的方法。通俗说,就是国家分得越小,越容易掌控。例如英国在十九世纪前本土面积不及其殖民地面积1%,却建立“日不落帝国”,凭借的就是“分而治之”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惩罚战败国,用得最多的手段,就是将对手肢解,如一战后肢解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二战后将德国、朝鲜、越南等等国家一分为二等。联合国刚建立时,世界只有五十多个国家,而现在国家总数近二百个。
在历史上,欧洲世界与阿拉伯世界围绕在地中海周边争斗了一千多年。最终欧洲人控制了地中海的西、北部(欧洲),阿拉伯人控制了地中海的东、南部(北非,包括阿拉伯半岛)。在这场千年较量中,双方在很长时间可谓势均力敌,特别是后来阿拉伯世界又吸收了西进的突厥人势力,更是达到了顶峰。但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崩溃,宣告了欧洲取得的胜利。阿拉伯世界按照欧洲殖民者的意图组建的国家,不可避免的沦为了欧洲的附庸。
奥斯曼帝国曾统治巴尔干半岛曾达五百年,它建立了一种稳定的秩序。巴尔干半岛内部各民族、宗教间一直保持和平与和谐。奥斯曼帝国势力退出后,巴尔干半岛被沙俄、英国和德国等强国争夺与肢解,成为“欧洲的火药库”。并在1914年爆发了以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暗杀为导火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接着又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东地区是强国地缘战略的牺牲品,已成为世界地缘版图中最大的破碎地带,最终彻底消除了该地区出现世界性大国的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奥斯曼帝国将自己绑到德国、奥匈帝国等组成的“同盟国”战车上,因此英国将奥斯曼帝国视为削弱和瓜分的对象,并有意挑动奥斯曼帝国内阿拉伯各省独立与叛乱,英国看中了阿拉伯半岛麦加地区的主要家族之一,哈希姆家族首领侯赛因.伊本.阿里,在1915年7月到1916年1月间,英国外交官亨利.麦克马洪与侯赛因做了一笔政治交易,史称“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英国承诺在战争之后建立一个北到亚历山大勒塔,东到伊朗边境,南到波斯湾,西接红海、地中海的阿拉伯国家。接着阿拉伯人随后在1916年6月发动起义,与英军一起推翻奥斯曼帝国统治。
英国与侯赛因.伊本.阿里达成协议不久,又与法国秘密签订了“赛克斯-皮科特协定”,秘密地将阿拉伯世界划分不同势力范围,法国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控制波斯,伊拉克和巴勒斯坦。
这时,英国极力鼓动犹太人向阿拉伯土地移民。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著名的《贝尔福宣言》,称乐意看到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
英国十分清楚,安插一个犹太国家,会使阿拉伯世界持久混乱与分裂,更易于控制。后来事实证明,以色列成了西方防止阿拉伯民族实现联合的心腹大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复兴运动风靡整个阿拉伯世界,显示出将阿拉伯世界整合的趋势。但由于在战争中屡次败于以色列,导致纳赛尔壮志未酬身先死,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而当时阿拉伯人的主要领导人侯赛因.伊本.阿里,目光短浅,更多地考虑个人与家族利益,因此在阿拉伯人建国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设计出一套“分家”的战略构想:即由他的一个儿子费萨尔统治叙利亚和伊拉克,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担任巴勒斯坦国王,而他本人担任汉志国王。这一战略构想,与当年欧洲遭遇十分相似。
侯赛因的设想,正中英法等国的下怀。现在中东的边界,正是由一战后的战胜国根据1916年英国与法国“赛克斯—皮科特协定”所划的边界。这一灾难性的建国史,使中东四分五裂,使阿拉伯世界埋下虚弱、内部动荡的种子,始终难以强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来,阿拉伯民族凭借庞大的人口、宗教、历史纽带,本来有潜质建立统一国家,但由于英国与法国的策略,使这一地区最终被分裂为二十多个阿拉伯国家。
二战之后,沙特害怕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在同属哈希姆家族的统治者下实现联合,埃及一心想扩大自己的势力,也反对这种联合,因此与沙特联手阻止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三国联合。同时,叙利亚和伊拉克谁也不肯依附对方,叙利亚怕伊拉克吞并它,于是依靠埃及,甚至依靠俄国。黎巴嫩则害怕被叙利亚吞并。约旦与叙利亚之间,开始是叙利亚怕被约旦吞并,后来变成了叙利亚威胁了约旦。
由于缺乏足以主导地区局势的“核心国家”,中东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结构,地区局势持续动荡。而没有了强大对手制约,以色列在中东肆无忌惮,成为阿拉伯国家安全的经常性威胁。迄今为止,中东地区大多地区战争和冲突,都与以色列有关。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政治学家基肖尔.马赫布巴尼在《亚洲人会思考吗》一书中提到,在一切穆斯林和亲西方势力的冲突中,不管是阿塞拜疆的、巴勒斯坦的、伊拉克的,还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都是失败的一方,而且败得很惨。伊斯兰世界是如此的不统一以至于它无法联合成一股力量。尽管有对伊斯兰世界的毫无理由的恐惧,西方世界看起来却几乎是故意朝着一条旨在激怒伊斯兰世界的道路前进。西方反对缅甸、秘鲁或者尼日利亚的集权政体,但容忍阿尔及利亚的集权政体。这种双重标准是有害的。波斯尼亚的集体仇杀制造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但强大的欧洲国家在面对发生在他们眼前的种族屠杀时却无所作为。这一下揭掉了西方道德权威的伪装,这种伪装在近代曾发挥良性作用。冷战结束至今,西方在世界上共发动了5场地区战争,包括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及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有4场都在伊斯兰世界,3次直接针对阿拉伯国家。而阿拉伯世界却难以做出有力回击。有人曾正确地指出,阿拉伯世界之所以如此,根源就是阿拉伯人不团结。但阿拉伯人“不团结”,并非天性如此,而是源于中东地缘被“巴尔干化”,地缘版图碎片化直接导致各小国间难以形成合力。同心协力。迄今,第三世界的其他两大地缘破碎地带——非洲和东南亚,已分别通过非盟和东盟地区性组织,很大程度实现地区联合,而中东至今没有地区性政治经济组织,即使囊括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阿盟,内部凝聚力也不断弱化,从而使阿拉伯世界始终难以摆脱动荡、孱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