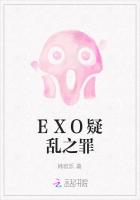佛山地区的收容所在一个叫石湾的地方,从广州解来的一车人,分成几队分别入住几个监房,乐义和欧进他们被安排在最靠边的一间监房。这里的管理人员似乎宽容了些,指令的语气并不威严。
这监房比广州天河的小许多,但相对于犯人人数却显得宽裕,床还是用木板靠墙壁拼成两溜对面的通铺床,只不过床脚不是用砖垒砌,而是用木方钉成架子,中间的人行通道较宽阔,人走动没有挤逼感。
监房关押的都是佛山地区的人,有阳江人、江门人、顺德人、中山人等等,各人说话口音各异,有的乐义他们根本听不懂。或者环境不挤迫,监房很安静,没有旧人对新入来的犯人暴躁地来个下马威的现象。
乐义他们找到睡觉的地方,把书包一甩,坐下。乐义环视一下全屋,便悄声对国志说:“这里没监霸了。”
国志莞尔一笑:“哪里监房都有监霸,只是他辨不清我们这批人有多少是同乡,暂不露头而已。监霸很蛇精,看到多同乡的人,他吞不下就有所顾忌的,不敢立即造次。一会儿吧,一会儿就有人来试试我们的斤两了。”
果然,后来进来的人都找到歇息的地方聊天了。有个衣着最新净,脸上划了条一寸长狰狞刀疤的青年人凑过来,这是个比他们先入来的人。
“你们是哪里人?”他对国志套近乎,但语调不甚客气,大概是因为国志年长稳重之故,他把他当作头儿。
“三水县,兄弟你呢?”国志不动声色地问。
“阳江县织篑公社。”
乐义第一次听说“阳江”这地方。
“很远哟。”国志说。
“是的。那四个人是你们兄弟吧?”
“对。”
“因何事入格进牢房。呢?”
“偷渡香港。”
“哦,我比你们重多了。我是流氓犯,和人打架,你瞧,脸上的刀疤就是证明。我在织篑街是有名的高手。妈的,那天猪肉佬竟敢惹我,我赤手空拳对着他手握猪肉刀,把他打个叫爷叫奶奶,只可惜不小心给他划伤了一点儿。”阳江人说着,从裤袋掏出包挤压得皱巴巴的“大钟”牌卷烟,抽出一支叼在嘴里,又塞回裤袋,掏火柴点燃,神气地吐出长烟柱。
套近乎聊天却不共烟,岂不是故意蔑视人了!阳江人这样套近乎分明是软招下马威。本来定睛听他俩谈话的乐义,故意大动作地躺下身子,表示不屑理会他。要不要我给你多划条刀疤,乐义心里不服气地说。
刀疤脸继续眉飞色舞口沫四溅:“我这是第三次入格进监房。了,第一次是私下造刀卖,造祖宗的传统刀,给关押在阳江县城游斗。第二次是大队治保主任多管闲事,我们几个兄弟经常聚头喝酒,不关他的事他偏要理,我教训了他,打破他的头,打跛他的脚,被判坐了两年牢。他妈的,我真倒霉,前些日子又撞上第三次,就是这次了,我去食品站买猪肉。猪肉佬秤了算账,我不够钱,欠一角,便说明天补回。卖猪肉的不肯,说什么公家账不能赊,要剜回一小块肉。他妈的,他不睁眼看看我是谁,敢和我计较,我不管他,提了肉就离去,谁知他竟拿了猪肉刀拦门口。织篑街谁不识我蛮牛?他这样做岂不是不给我的脸子!我便不惧他持刀,和他打起来,他划伤了我的脸,我夺了他的刀,把他重重打趴地上。他不死也伤了,起码要住两个月医院。公安局说我问题严重,解来地区收容所等候发落。”
刀疤脸越夸耀,乐义越藐视他,他心里轻蔑地冷笑,卖弄什么?不过是现个刀疤做本钱虚张声势唬人罢了,与芦苞街上那个外强中干的痞子二爷一路货色,找个机会杀杀他的威,让他出出洋相。
刀疤脸很斯文,他每次打了饭就蹲在饭堂门口,有几个人打饭出来很自觉地往他,以及他的哥们的饭兜拨点菜和饭。洗澡前规定他先取衣服,他在晾衣绳上,看中哪件衣服就取哪件去换,没人敢作声,而且换下的衣服有人代洗。
“无怪乎全牢房就他的衣服最新。”虽然这些都没惹着乐义他们,但乐义看着刀疤脸趾高气扬的嚣张样很刺眼,全身雄气勃勃,躁动不安,他对国志说:“刀疤脸不知天高地厚,我找个茬挫挫他的气焰,灭他威风。”
国志劝乐义:“算了,那阳江仔不过是没牙佬拣豆腐吃——专门欺软的。他不惹我们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算了。”
起初乐义听从国志的劝告,对刀疤脸的霸道行为视若无睹,可闲下来,脑海老是给武松那句“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便死也不怕”的话,撺掇得义气涌动十分难受。从深圳收容所一路打过来,打出了成就感,他还是决意要制服刀疤脸,巩固成就,也释解监房日子的压抑郁闷气。
这天放风洗澡,刀疤脸依然如故地首先去晾衣绳上取干净衣服,这次选中的是件八成新的湖水蓝色短袖衬衣。
乐义对欧进他们点点头使个眼色,提醒他们看着情势,做好帮忙的准备。欧进会意,乐义于是上前拦住刀疤脸,“对不起,这件我看上了,我正要去洗澡。”
“兄弟,你好像有意和我过不去吧?”刀疤脸挑衅地问。
“不敢,我的确看上这件了,你要回你自己的吧。”乐义的语调绵里藏针。
刀疤脸凶恶地瞪着眼睛,指点脸上的刀疤威胁地说:“你别耍风车,要和我见识就明说,老子关了三次监房坐了两年牢,什么人未领教过,什么场面没见识过?”
自从揍过二爷,乐义对任何凶恶的目光都是不屑一顾的,他嗤之以鼻地蔑视着刀疤脸:“你关三次监房坐两年牢算什么?我从深圳一直坐牢坐到这里,还没有见过要我叫爷的监霸。你老母的,在阿哥我最憋屈的时候,你污我眼惹我烦恼,要不要替你多添一两道疤痕?”
“我哪惹了你?”
“你霸占别人的衣服,吃饭要人孝敬你。”
“哦,原来你眼红我,想在这一仓里做大哥。”刀疤脸说着冷不丁一拳冲向乐义脸门。
乐义一直都提防着对方动手,他左手将来拳托起,屈起右手疾跨一步抢入刀疤脸的门户,狠狠地一肘撞向刀疤脸的肋下。刀疤脸啊哟一声退后几步,没来得及站稳,乐义的拳头好似擂鼓一样打得他身体“咚咚”作响。
欧进看着乐义解恨地打刀疤脸,回想到在广州收容所低三下四生活的屈辱,他便大叫一句流行的政治口号:“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
乐义一步跨入刀疤脸门户,前弓步勾着刀疤脸的腿,扭腰一掌打在刀疤脸的胸膛,刀疤脸被打得往后退,但脚给乐义马弓步勾着,于是整个人失去重心,打个趔趄就摔成仰八叉。乐义果真一脚踏在他的身上。
跟刀疤脸一起享受霸权的四个阳江仔跳下床,走向刀疤脸。欧进见状对国志他们一挥手“上”,便冲上去,看到乐义教训刀疤,他早就心痒手痒得痉挛,管那几个阳江仔是扶刀疤脸还是围攻乐义,不由分说挥拳便打。几个平时受过刀疤脸欺负的人,见状也参与打斗。阳江人明显处于劣势,只有挨打求饶了。乐义退出圈子,靠床边坐下,欣赏眼前的热闹。
“妈的,我也要前去踢他两脚出口气。”身后有人说。乐义正想回头说句“去出口气吧”却听见另一人说:“去什么,别高兴得太早,虎逐狼走罢了。”
乐义听了心里不服气。妈的,我打刀疤脸不是为了争做监霸,好,我就义气义气给你们看。于是他就向众人宣布:“各位,今后谁也不准欺负谁,要各守规矩相安无事。”
这下,整个仓的人都开心了。
“我们都听大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