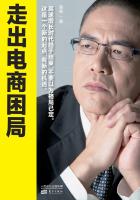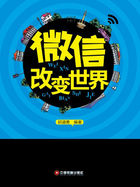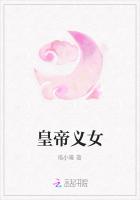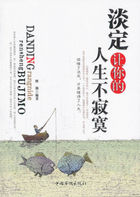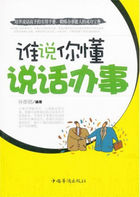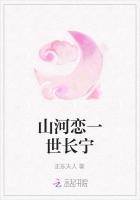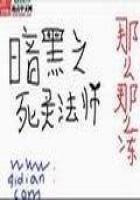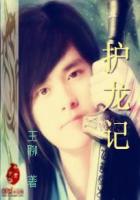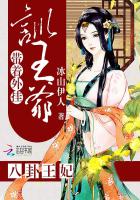一切竟是如此容易,李梅简直惊呆了。按照陈灿文事先的安排,李梅拿出千分之三的手续费(7万多)分给了几个中间人。事后,宋汇贤在香港带了20万港币去感谢陈灿文,但陈老大说,这是交情所致,忙是要帮的,钱却不能收,等你以后做大了,我们有的是合作机会。
经此一役,宋汇贤夫妇彻底打了个翻身仗。李梅也非常机敏,她马上通过各种有关系的身份,注册了多家自己实际控股的进出口企业,为骗税做着积极的准备。
事实上,骗税的人何止李梅夫妇,在当时的广东来说,出口退税是个非常时髦的词,以至于很多人在说起职业的时候,都会用“我是搞出口的”来定位自己,而且,每天注册进出口企业的,也是人山人海。
表象的出口繁荣似乎让人看到了国家扩大出口贸易政策所显现出来的成果。但如此简单的退税手续,谁敢保证这些注册公司有几个在搞实实在在的出口贸易?
比如,当时深圳最早的骗税专业户是赫赫有名的文石兴所掌握的赫赫有名的海诚集团,因此,骗税这门技术基本上没经过什么循序渐进的发展,直接在他手里就炉火纯青,因为人家搞的是集团化运作。
后来,这文总太不低调,海诚集团也跟着不低调,慢慢就招了风了。但是这海诚集团能骗税这么多年,肯定不是区区的几个小公务员做内线就能大旗不倒。因此,有关部门开会是否要缉捕海诚公司文总的会议还没结束,消息就已经到了文总的办公室。文总一生大概只有这次做得比较低调,非常配合这个消息,直接走人(出逃境外)。
文总走了,留下的却是活生生的“行业技术”。海诚的人员随着海诚集团的落马,也基本上就树倒猢狲散了。他们后来分布在广东甚至其他沿海地区,大都成了地下钱庄出口骗税的技术骨干。
地下行动在迅速蔓延,广东省由于当时的贸易和外汇流量占全国的一半,这预示着大家都在忙着退税,没多久,国家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首先表现出来的是退税额太大,国家的钱有点跟不上了,各地开始出现打白条的情况。
于是,针对特区的优惠退税规定收紧了:申报退税时,除了需要出口合同之外,还要提供写明离岸价的出口销售发票以及进货发票。
李梅刚准备好大干一番,就遭遇到了这个难题。但这些难题在那几个中间人眼里,基本上等于跨一个小门槛,压根儿没当回事儿。事实上,这是一帮专业级骗子,干的就是伪造窜单的活儿,因此,新政策一下来,他们不管什么,还是能搞出来,申请退税,一样都不缺。
就这样,借着退税而来的资金,李梅的套汇生意也越做越大。
对于这个后起之秀,关系遍布广东珠三角的邱国建自然一清二楚。等到后来高建明也知道这个人的时候,心里翻了五味瓶,自己心里其实一直对这个女人念念不忘,苦于无法寻找,可是等到终于有了消息,却已嫁做人妇。淡淡的忧伤也着实困扰了高建明很长时间。
不过所有这些,高建明都没有和邱国建袒露过,这也许是唯一一件对邱国建来说是高建明的秘密。
事实上,对于李梅的事,手下有些人也劝过邱国建,虽然是后辈,但这个人确实有一套,干脆咱们也学习李梅好榜样吧?
邱国建当即拍案而起,大声喝止。在他看来,虽然同为地下行当,他和李梅有着本质的区别。做退税是无本的买卖,是标准的骗钱,这种做法根本就是自己找死。而他,只是在做生意,尽管也搞过几次骗汇的事儿,但说到底,还是实打实拿出本钱买汇,充其量是和官方做了把不正当的生意而已。
这个想法和高建明不谋而合,他认为李梅此举风险极大,一旦她出事,不仅她自己伤不起,很可能会牵扯出整个地下钱庄行业。但他明白自己的潜意识--一旦她出事,他心痛无比。
面对这种局面,大家一时都陷入沉默,不知道如何是好。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本本分分”地做生意。
李梅的套汇、提现等生意虽然越做越大,但她一直没有放弃骗税这门生意。不过,此时,国家关于出口退税,又有了新的严苛的程序规定:出口合同、销售发票、出口报关单,缺一不可。
伪造合同,搞发票这些事还算小事,可报关单没有过硬的海关关系,用假的蒙混过关比登天还难。不过,一件事之后,李梅的过硬手段便彻底显露出来了。
谁也想不出,李梅是怎么发动海关关系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疏通和策划,李梅居然采用货柜空进空出的方式,轻松获取报关单,第一笔50万美元的“出口贸易”就这么轻松搞定了!
显然,海关内部已经被李梅打通了。
光搞定海关是不行的。因为等到后来,国家再次要求出口企业退税时必须完成收汇,持有出口结汇水单和收汇已核销凭证方可办理。显然,李梅必须打通银行环节。
李梅第一次拿收汇已核销证明是利用一笔300万港币的出口合同来操作的。那个时候,似乎任何事情已经难不倒这个神通广大的女人了。她通过自己的网络和手段,在麾下养了一批银行内部对结汇手续了如指掌的志同道合的专业门徒,里应外合的局面一旦形成,收汇手续就变得再简单不过了:李梅先通过丈夫在香港组织300万港币的外汇,并通过银行的“内人们”将钱打进银行,这样,就名正言顺地获得了结汇凭证。
按照当时的汇率100∶105.3,合同额为315.9万人民币,李梅顺利获得了53.6万元的出口退税。
至于打进银行的那些外汇,其身份也只是“暂住”而已,李梅自然不会让它们在银行寂寞下去。
通常,李梅再通过其老公在香港和海外的公司来签订相应数额的假进口合同,然后在银行内线们的大力配合下,把这些外汇兑到香港公司。
本钱一点儿没损失(充其量支出一些小小的兑换手续费),外汇就这样一进一出,他们就凭空获取了高额的收益!
但是,“骗”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一点李梅其实比谁都清楚,况且,在这一时期,李梅夫妇已经凭借到手的资本,完成了初步积累,换汇生意开始转入“正轨”了。
李梅收手,当然不代表骗税从此在社会消退。
3 吸金大法高利贷
地下金融活动的猖獗和活跃,如果说反映的是金融秩序问题,还不如说折射出了金融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任何时候,需求与供给都是市场的一个基本原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推向国际化,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策马扬鞭,需求日趋旺盛,致使国内企业的投资与资金需求全面增长,而国家外汇体制对经济发展形成不同步的制约,使得这些金融需求无法得到及时满足。时间又恰恰是企业的生命,为了利益,路不通只能谋求他法,这也就为地下钱庄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客户基础。
90年代,地下钱庄“业务模式”除了普遍的套汇、提现和走私付汇、骗汇、骗税、洗钱等,还有就是“长盛不衰”的地下放贷业务,尤其是在浙江、福建东南沿海一带,地下钱庄的很多业务就主要以民间放贷为主。
早在1985年,乐清县就出现了以金融投机性为主的“抬会”(也叫经济互助会),一拨小老板组织一个所谓的堂会,主要工作由会主主持,把会员的资金聚拢,然后交由会员们轮流使用,大都用于短期投机行为。模式一般为,先用的人支付利息,后用的人吃进利息。比如,温州抬会的规矩是:会员入会费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12个月,共计10.8万元;从第十三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这样,一个1.6万元的会员要一直玩下去,到第六个月就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十二个月,要发展到691个会员,到第十八个月,就要发展到20883个会员!
当时在乐清,这样的抬会大大小小有1300多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人!从1985年开始到1986年年末,光是温州九县两区,就有30万人卷入其中,涉及的金额高达12亿!甚至还一度出现了“官会”。
这种游戏有种令人疯狂痴迷的“魅力”,但“魅力”的背后,却是一系列的问题--只要有几个上层会员外撤,资金链就会相继断裂。事实也如此,1986年春夏之交,正当大家做着发大财的黄粱美梦时,资金链突然崩裂,会主一看局面不可控,卷款潜逃了。于是,大规模的倒会相继出现了。
到了1988年,抬会彻底搞不下去了,但生活和赚钱还要继续。个体私营和股份合作经济需要快速发展,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活人让尿憋死了,那是尿人!
江浙一带的小老板们,办法多得是,胆子大得多,他们相继把目光投向地下金融市场。
于是,在乐清和苍南等地又相继出现了从事吸收社会存款和发放抵押贷款的典当商行,到了1992年以后,这种地下投融资的规模已经相当惊人了。特别是义乌商品市场,以及永康的五金制造和电动工具产业园区的形成,在当时的发展速度可以用惊出眼珠子来形容。
与此同时,这些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就比较掉链子了,国有商业银行执行的是“存量调整、增量移位”的信贷方针,他们的年末存款余额均小于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有的还差距比较大,再考虑到年末资金回笼的存款波动因素,差距就更离谱了。这只能说明一点--这些地方的信贷供给能力普遍不足,缺口很大,无法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
还有,企业即使起早贪黑跑关系找门路,能在银行借钱,但拖沓冗长的贷款手续,也让企业叫苦连连--那边项目催着要钱,这边有钱不出,催着要礼,老板可真不是好当的。
这种情况,对于借钱手续简便、效率奇高的地下资金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利好,各地地下钱庄都纷纷出动,大有为私营经济发展“添砖加瓦”的架势。只要资金能够及时跟进,坐家里都有人上门找钱,利率却比官方高得多。
他们运作的特点也非常鲜明:
首先,是标准高利贷。地下钱庄惯用的手法是以稍微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方式先吸取民间存款资金,然后在出借资金时,将利率再抬高到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以上,有的最高月息达30%,利滚利、息生息更是家常便饭。
其次,借贷方式非常隐秘。无论是吸收还是贷出资金,只私下里写条:提前将借期内的利息算出来,在借条上的金额是本利合计的总额;或者是在付给借出款项时,先把借期利息扣除,而借条上仍写明原借款数额。这种隐秘方式,100%规避了有关部门的查处风险,违法证据在这种模式下,是绝对无迹可寻的。
当然,地下,总离不开暴力。借出人之所以敢于凭一张条子借出百万千万资金,一点都不担心死贷风险,是因为他们往往有着特殊的追债手段。不少钱庄都有一支自己的专业追债队伍,小债由小混混和恶棍出马搞定,大债就动用黑势力。因此,借高利贷者通常就几种下场--好的,短期投机成功获利,如期还债;差的砸锅卖铁咬牙还债,妻儿跟着吃苦受罪;再不济的,就只能跑路,终身浪迹天涯了。
浙江的陆兆维就是其中的一个跑路分子。不过,1997年跑路,2008年的时候又回来了,而且是手握数十亿资产的高调回归!
这要从2008年以后的形势说起。
首先,抬会彻底沉寂了,曾经多豪壮,结局多凄美,都成了历史翻页。
但是,玩金融,赚钱实在太容易了,致使很多豪人,如江浙地区以温州富豪为首的温州炒客们,还有就是内蒙古新崛起的鄂尔多斯暴发户(大都是政府占用土地而获得的补偿款),根本就不想沉下心来投资实业,而国内“投资”渠道也就那么几条--银行低息了,股市跌跌不休了,楼市也众人喊打了,大宗商品市场更是风声鹤唳,突然间,钱没了出口!
资本天生就是闲不住的,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资本性格。
于是,有些人首先搬着钱跳出来,开始投放“民间贷款”。
人群和羊群没一点区别,只要有一个打头的,后面的冲得比打头的还兴奋。
民间信贷就此抬头,民间资本迅速聚拢。以放贷为主要任务的地下钱庄便也雨后春笋了。
民间资本常被一些所谓的砖头家们称为“游资”,从称呼来看,貌似有点瞧不起民间资本。可他们真的知道民间资本的聚合力量吗?
有放贷的,就有借贷的,这些信贷资金到底流向了何方?
事实上,除了少量的借贷资金进入了实业之外,大部分资金仍旧停留在了虚拟资本领域,就像股票的实质就是一张传来传去的白条一样,地下信贷资金也依靠迅速转移而形成了一种风险随时可能爆发的强大流动性,貌似相对平衡的“三角债”、“四角债”等,用来衔接关系的只是草绳,随时都可能会断裂。而几年前包头高利贷钱庄的金利斌自焚事件,也为民间放贷风险提供了佐证。
陆兆维就在这种情况下轻轻地来了,正如当初他轻轻地走了一样。
谁也不知道这个跑路者这些年做了什么,只知道他当初走时仓皇,而如今回归,却已行囊鼓鼓,装满了钱。
陆兆维一回来,就大展拳脚。知情人知道他从事的是外贸生意,但大家都知道,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下,外贸生意都比较悲催。但陆兆维就在这种低谷时期,还是能维持一年200万美金左右的销售额,享有10%左右的利润率。
实际上,多年来,陆兆维的外贸生意一直就是这种规模。行情好的时候如此,不好的时候,也如此,一向四平八稳。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企业做大的想法,更没有国内的老板们动不动就要奔向纳斯达克的雄心壮志。他的主要兴趣点还在冒险上,每年赚的钱,除了维持现有业务规模之外,都用于积极主动热情地寻找投机机会。
起初,陆兄在全国各地买房子,可以这么说,无论国内哪个一线城市,对他来说,都可以算是回家。后来,他又去证券公司的VIP室做股市,甚至还跟着游资炒农产品。少小跑路老大回,直到后来回到老家台州,才算稳定下来,三心二意做外贸,一心一意谋放贷。
陆兆维之所以选择这种生意,和他一个老乡有关。
闻化明,台州人,在江浙一带的好几个城市都有服装生意。偶然机会,通过朋友认识了老乡陆兆维。从朋友嘴里,他听说了陆兆维当年的“英雄事迹”,颇为敬仰。
世界就这样,你踏踏实实做企业,没人认为你能干;你要是踏踏实实把企业做烂,然后再华丽地跑路,大家就把你当英雄!
一来二去,烟酒糖茶、澡堂子歌厅,没几天两人就熟到彼此倒背如流了!陆兆维当然也搞清了闻化明的路子--看似每天服装铺里忙活,其实这些服装的后面藏了一项更大的生意--放贷。这方面,陆兆维是专业出身,跑路之前就玩这个,因此,闻化明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他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