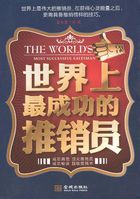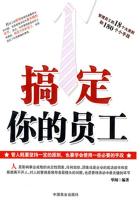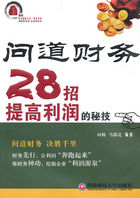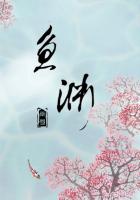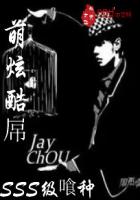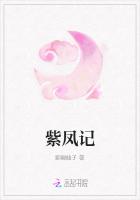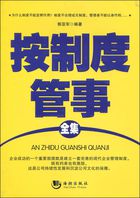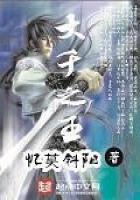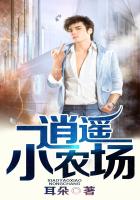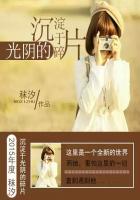几分钟之后,包房门再度被打开,一阵香风来袭,从外面进来几个高个旗袍,也不客气,莺燕一般就飘落在几个人身边。高建明马上明白,他的猜测是正确的,他们叫了三陪。但高父就很纳闷,来这么多眼热心跳的美女干什么呀。就在此时,小个子大哥大却已经动手了,一把搂过美女,一边上下其手,一边高举酒杯,用广普(广东普通话)说着“大家干杯”。
高父也跟着端起杯,一个香气逼人的女人贴了上来,帮着他把酒杯往嘴里送。旁边的高建明更受欢迎,美女直接坐他腿上,吐气如兰地在他耳边说:“帅哥,真壮哦……”
父子俩同在这种场合下,恐怕是天下最尴尬的事了。
高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个劲往后躲;高建明也边推身上的美女,边偷看父亲这边。窘态引得大家好一阵哄笑。
亲戚显然见惯了这等风月场合,本着不避讳、不客气、不尴尬的“三不”原则,扯过一个女人到自己的腿上,女人喂他喝酒,他的手则在她那让人极度膨胀的身体上摸索探寻着。
醉了,高父醉了;高建明也醉了。其他人什么情况,也许就他俩不知道。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身在酒店的豪华客房里。高父想努力回忆昨晚的情形,但除了贴在他怀里的那个高挑女人之外,记忆如同被抹去一般--那晚,他已经不存在了!
高建明血气方刚,一旦接触了女人,最原始的欲望就被彻底唤醒了。他满脑子都是旗袍女的影子,仿佛现在还软玉温香地坐在他年轻有力的怀中,越是怕父亲看出来,越是努力让自己不要想这些事,自己身上的女人余香仿佛越是清晰。他有些生硬,怕父亲看到,就腿上搭了被角,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亲戚过来的时候,父子俩正像“文化大革命”时等待红卫兵上台恶斗的走资派一样,都在延续着昨晚的尴尬--低着头,互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想问发生什么事,又觉得无法启齿,只是有种深深的罪恶感。
亲戚也没说什么,只是问他们睡得好不好之类的。之后,亲戚让高建明回单位上班。高建明走后,亲戚先扯了几句家长里短,突然话锋一转,开始告诉高父邀请他过来的原因。
亲戚和小个子大哥大有些生意,由于亲戚是国家单位的人,不便于亲自打理,想让高父代为经营。
这一聊不要紧,一直深埋于父亲心中的关于亲戚的很多疑问也就此解开了。
原来,亲戚虽然在战友的安排下进了事业单位工作,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条发财之路。
一朝舍命,换来生死之交。战友除了给他尽量安排大大小小的生活之外,还经常给他一些侨汇券。前面也说了,这东西在当时就是时尚奢侈品,普通人可遇不可求,能迅速提高生活质量。
渐渐地,亲戚家里的侨汇券积压了。
他就和战友说,不用再照顾他的生活了,该有的都有了,现在什么也不缺,那么多侨汇券也用不了。可战友的一句话让他感觉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兄弟:“我没别的可给你的,只有这些,给你就等于给我自己!你用不了,就卖了!”
感情到这分上,再推辞就没天理了。于是,亲戚就积攒了很多,卖来卖去,渐渐地和一个叫邱国建的倒卖者混熟了。后来,邱国建就建议亲戚一边在单位上班,一边通过自己的路子收购侨汇券,然后再以较高的价格卖给他,两人一起发财。
浓缩的绝对都是精华。别看邱国建个子小,但路子野,头脑精,据说背景也很硬。熟络了之后,亲戚和邱国建的地下生意一如水银泻地一般,自然通畅,越做越大。
到了1982年的时候,精明的邱国建看到另外一条路--外汇券,赚钱能力一点儿都不比侨汇券差。于是决定转变经营策略,生意开始转向,亲戚仍旧是邱国建铁打的合作伙伴。
当时外汇券和人民币的黑市比价已经是1.2∶1了,也就是说,1元外汇券能够卖到1.2元。他仗着自己以前的大摊子以及不黑不白的背景,敢于随意搞乱以“规则就是信义”的黑市行情,竟然直接以1.2元的价格大肆收购。
这么做生意显然不厚道,其他黄牛不干了。纷纷找他说理,说他破坏行规。但这些人和邱国建一过招,结局大都只有一个--有理也说不清。
其他的小黄牛没办法,也就只能任他乱来。不过邱国建有个和其他黄牛不同的策略:他收购之后不卖,当然,1.2元收再1.2元卖,显然是有病,邱国建绝对没这风格。
问题是,再高的话,他如何卖出去?谁接盘子?
其实,这次他玩的是另一种别人都没玩过的游戏,用现在时髦的说法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以外汇券为介质,倒卖只有外汇券才能买到的东西。
这需要细说,才能看到邱国建的生意头脑是何等的强大。
友谊商店本来就有潜规则,拿外汇券买东西,可以给暗折扣。由于手握巨额的外汇券,而且在友谊商店还有内应,因此邱国建可以在这里随意组织这些社会稀缺的紧俏货源。以当时标价100元的商品为例,普通人拿着外汇券去买,如果懂得砍价,可以90元外汇券买到。而邱国建搞的是“奢侈品批发”,里应外合加上数量巨大,竟可以用60元外汇券买到!
要知道,这些让人着迷的货,没有外汇券的人想都想疯了,就是买不到。到了邱国建的手里,这些货不用外汇券也能买,但价格是140元!
价格高不要紧,不要忘记,没外汇券的人毕竟占绝大多数。因此,他组织的货源基本上在卖方市场,供不应求,往往是闪电的速度就能消化。这种销售速度也只能在2005年以后的房地产市场才能见到。
现在,这里面就有个很巧妙的算术了:
邱国建花144元买120元的外汇券,然后可以买到两件友谊商店标价100元的商品,再转手以140元一件的价格销售,流水就是280元,净利润是136元,利润率将近100%!
回头再看看那些风吹日晒的小黄牛们,花1.2元甚至更高的成本买1元的外汇券,然后再1.4元卖给需要的人,赚2毛顶天3毛的差价,利润率只有区区的20%左右!
一样的外汇券,却是不一样的日月。
这世上,有人穷尽一生挣钱养家,有人却能坐地生财貌美如花!大家每天都吃喝拉撒睡,尽管拉的都一样,但总会吃的不同、喝的不同、睡的内容也不同。
高建明父亲听了亲戚的介绍,对这个邱国建简直佩服得想死。其实他哪里知道,每天收音机里所说的“投机倒把”,说的就是邱国建这样的。
“这么高级的生意,我哪有那能力能帮你打理呀?”高父想到这事,不是一般的心虚。
“不是这个,现在我们不想做这个生意了,是想你帮我打理别的。”亲戚说话的时候心里就非常有底。
“啊?这么赚钱的生意,不做了?”在高父的眼里,这生意比他自己所在的厂子都大。
“这生意刚开始好赚,后来搞的人越来越多,风险也就大了很多。毕竟,都是国家禁止的事儿。”亲戚拍了拍高父的肩膀头,“我知道你人靠得住,讲信义,才想请你过来一起搞的。现在我们又发现另一个赚钱门道了。”
“?”高父的脸上写满了符号。
“钱庄!”
故事讲到这里,可以先暂停一个段落。回过头我们再总结外汇券这个东西。
外汇券发行的初衷,就是为了调剂较高质量、较高消费的紧俏商品供应,也就是把好东西留给外汇。同时,这还能让外汇与人民币之间有个巧妙的沟通。但是刚刚发行4年,也就是到了1984年的时候,以外汇券阻止国内人购买紧俏商品的策略基本失效了不说,还始料未及地衍生出繁荣的外汇券地下市场。据经济学家张五常的文章《人民币的历程》里记载,当时相关部门对此也都心知肚明,他们默认继续保留外汇券体制的原因是,认为外汇券的价格分歧会带来较多的外汇进账。张五常也曾经数次向他们解释过这里面的问题,但由于里面牵涉一个弹性系数分析的问题,当时很多人都根本听不明白。
其实按照张五常的理解,当时的中国就是一国两币,事实上很多国外的媒体对当时中国的情形进行报道时,也有过与张五常类似的评价:
很显然,人民币是劣币,外汇券是良币。权衡当时的中国,张五常认为大名鼎鼎的格拉森“劣币驱逐良币”定律(Gresham's Law)根本就不在适用范围,甚至错得有些离谱。因为一旦市场知道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劣币就不会对良币形成驱逐态势。这倒是比较合当时的金融当局者的胃口的。
当时有个有意思的事情。
1986年,很多老外也开始变得鸡贼,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学会了讨价还价,相关金融部门发现外汇券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当年6月的时候,曾经表示要取消外汇券,当年8月的时候公布,说11月起外汇券将不再使用。可是张五常有点手痒,同年9月站出来演了一把“货币的发声训练”--发表了一篇特多余的文章,叫《外汇管制可以休矣》。结果这一嗓子不要紧,外汇券的取消却因此而推迟了7年!
这当然是张五常自己在《人民币的历程》一文里说的,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量,在我们这里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但老张的观点却显示出他对中国外汇黑市的理解要比国内某些人透彻得多:
他说人民币与外汇券共存,经过市场讨价还价后,从表面上看是不同价,事实上是同价的,因为这里面涵盖着的非法倒卖行为就是个“真实的汇率”问题,这个真实的汇率,是官方汇率与外汇券黑市汇率的叠加效应。很明显,外汇券的存在,更多的起着一种烟雾的作用--把非法行为遮掩起来。一旦取消外汇券,那就是驱散烟雾,非法汇兑即刻就会变得黑白分明。这样,如果允许外币流通,那么外汇券所形成的价格分歧导致外币购物的价格低出不少,要纠正只能进行外币的价格管制,但这样就没法打开国门做生意;如果不准外币流通,那么在官价汇率与市场明显脱节的情况下,外贸、旅游及外资炒汇黑市会更进一步繁荣,要约束,则只能加强外汇监管。
两条路摆在面前,中国怎么走?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开放初见成效,外汇储备步入良性循环,逐年增加,国家不再需要特别的刺激外汇增长的措施,同时由于实行了市场经济,紧俏商品已不再紧俏。于是,外汇管理部门启动了一系列外汇管理制度改革。1994年1月1日,中国正式取消各类外汇留成、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走上了外环监管之路,外汇券遂成历史浮云。
但是,从侨汇券到外汇券,留给民间的除了回忆与收藏之外,还有什么呢?
那就是,原先的倒卖侨汇券和外汇券的“黄牛党们”,失业了!
确切地说,也不能叫失业,而是这个地下行业也随着两券的离去而酝酿新一轮的洗牌。
利益就是操作之母。
多年的地下经营,大家的思路也相当开阔,资本永无眠,从来就不甘寂寞,没券可炒,自然会猎寻新的目标。洗牌加洗脑,有的黄牛被冲走了,剩下的,在利益链条的导引下,就像高建明父亲的亲戚和邱国建之类的人物,开始将目光瞄准另一块黑市沃土--地下钱庄,模式进一步升级,开始直接玩外汇。
只要有汇兑需求和汇兑限制两个因素存在,利益空间就永远存在,一定会有人去经营,也肯定会自发形成市场。尽管这样的市场开始可能是零碎而复杂的,一旦形成蚂蚁搬家的态势,往日的黄牛就会脱胎换骨,形成巨大的交易量。
这就是政府难以扫清地下钱庄的道理,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一层蒙在地下钱庄上面的监管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