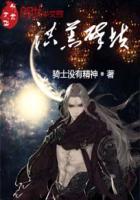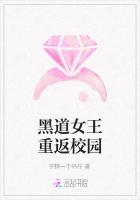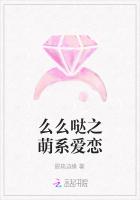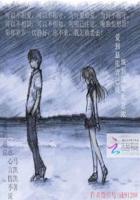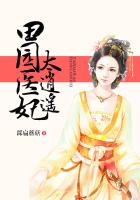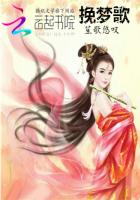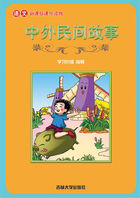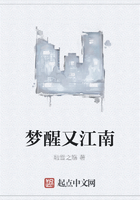对于写小说,我记住三位名家的话。
一是沈从文,他说:小说要调皮。
二是陆文夫,他说:小说就是要往小处说说。
三是高行健,他说:小说是作家的自言自语。
三位名家都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写作跟作者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我性子急,经常噜苏不起来,换句话说,就是细节部分“细”不下去,往往粗枝大叶,以致小说有骨架,而血肉不够丰满。另一方面,造成粗线条的原因是,下笔时老是顾及读者,急于向他们传达某种理念,所以一提枪上马就直奔主题,不能从容地在内心世界徘徊漫步。
引发上面一段议论,是在读了汉基兄的长篇小说新作《灰影》后产生的感想。汉基兄伏案两年,得字十万。他把《灰影》书稿送来,我拜读后,对他说,故事好,骨架子也好,就是瘦了些,最好加长些,十万字只能算个大中篇哩。他接受我的意见,就去添油加醋,着手拉长它。
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加了。我说,加了多少?答:六千来字。然后传真给我,我一看笑了,汉基兄惜墨如金矣!原来他在开篇的前面加了一个“引子”,也就是戴了一顶帽子,内文也加了一些,但不过是撒了点葱花椒粉,下了点毛毛雨。不禁慨叹,这是汉基兄的个性使然。他为人率直,不喜欢噜苏,因此,行文也就干净明快,流畅清爽。
《灰影》写的是新移民的故事。国内某名牌大学毕业的易奇新,移居香港后,绿印天涯,学历不被承认,挣扎于社会底层,受尽了白眼和奚落。他聪明干练,却始终得不到赏识,反被排挤,被嘲弄。大陆新移民的背景,像一个巨大的灰影笼罩着他,使他无法突破,无法摆脱这个无形的“灰影”给他带来的命运的错厄。围绕着易奇新命途的浮沉颠簸,还交织了身边红男绿女的爱恨情欲,以及权钱交易、尔虞我诈的商场争斗,纷然杂陈,显得热闹好看。故事虽以线型发展,但也不乏起伏跌宕的波漪,颇为引人人胜。
小说或多或少都带有作者的自传性。《灰影》也不例外,易奇新的身上隐约闪现着作者的影子。汉基兄是20世纪60年代的广州暨南大学毕业生。七十年代末,在经历了许多政治风波后移居香港,初来乍到,备尝艰辛,他做过工厂、看更以及写字楼低级文员……到了年逾花甲的时候,回首往事,咀嚼人生,洋洋洒洒,写出这十万余言的《灰影》,一叶心中郁气。可谓“阅透人情知纸厚,踏穿世路觉山平”,笔笔写下都真切实在,字里行间融注了对人生的感悟,人性的喟叹。尤其是同样做过“绿印客”的新移民,读之更感同身受,为主人翁的遭遇慽然动容。
汉基兄近年写作颇勤,已结集出版有散文集《四季灯》、短篇小说集《野玫瑰与黑牡丹》及长篇小说《野寮》。上述几本书,边读边浮现汉基兄的模样:光着头,穿着夏威夷恤,笑呵呵地站在向前,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一看就让人感到他的晚年过得颇滋润,因此,就可以静下心来,搞搞纯文学。青少年时做的不醒的文学梦,到老的时候,终能一圆,这当然是人生一大乐事,夫复何求?我曾写了两句话赠给文兄李远荣:“砚田老牛,墨池春花”,今移来作为这篇小文的结尾,窃以为这两句话亦是汉基兄的写照。在此,谨祝汉基兄体健笔健,砚润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