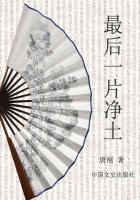果园的白杏、金色的麦浪、清凉的水塘、简陋的校园、住院的温馨、艰难的生活,无不唤起每个人儿时顽皮、痛楚与快乐的回忆。年轻人都希望早日走出校门走上工作岗位,他们的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一旦真的到了广阔天地里呢?天确实是广了,地也大了,视野也宽了,但是就有大的作为吗?那可不一定,说不好还会有灭顶之灾呢!那一个接一个的陷阱,总是不停发生的事故,奸邪人的险恶用心,偶尔发生的自然灾害、无可奈何的行贿等,无不令人如履薄冰、如坐针毡。人的一生艰辛困厄、危机四伏,如何涉险过关,如何避开风波,如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些亘古的难题谁也无法破解。正像李祥出生的那个情景,天空晴好湛蓝,阳光明媚如洗,可就是雪罩四野寒气逼人。
一生的危险〇第〇四〇章一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刮了一夜的寒风早已停了,乡村还沉浸在一片祥和的寂静之中,突然一声洪亮的婴啼给一家农院带来了久久的沸腾:添丁了。在中国的农村,虽然已经解放了几十年,但男孩传宗接代的风俗却是没有丝毫的改变,所以农家出生男孩无疑会给一个家庭带来无限的欢乐。这个家庭更是没有例外,因为孩子的父亲只有弟兄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就做了父亲,当然是不知如何的高兴,可他高兴之余未免又有些茫然:父亲因为耐不过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痛苦地去了,留下了自己和四个姐妹,妈妈又常年有病,如今又添了人口,虽说希望从此有所寄托,但这生活的艰难却无疑是又进了一层。他深深懂得,维持这个家的生计,自己今后得付出更加艰辛的劳动。
他走出堂屋,到了门外,院子里还积着厚厚的白雪,阳光斜照,耀人眼目。几个妹妹正在铲雪,见哥哥出来纷纷围拢过来,嚷嚷着要哥哥给小侄儿起名字。他沉吟片刻,又望了望几个天真烂漫的妹子,若有所思地说:“父亲去的早,这是我们的不幸,希望这个孩子能给我们带来吉祥,就叫他瑞祥吧。”妹妹们高兴地跳起来,扔下手中的锹笑着跑进屋告诉她们的嫂嫂去了。
光阴荏苒,瑞祥已经长到了五岁。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年关将至,年货还没有着落,听说邻县的大蒜很便宜,父亲决意跑一趟,贩一车蒜挣几个钱度过新年。几天之后,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奶奶、母亲和姑姑们无法入睡,她们都在惦记着还在奔波劳碌的亲人,半夜时分,院外有了人声,她们急忙跑出屋子,打开门,屋外大雪连天,一个“雪人”正匆匆往屋里赶,进了屋就扑通摔倒在地,她们赶紧打掉来人身上的积雪,姑姑们喊着哥哥,母亲只是抽嘘着不做声,很快父亲坐起来,扫视大家一眼,嘴角抿着幸福的笑,无力地说:“我的裤腿里全是雪,帮帮忙给我倒出来。”母亲再也不能抑制,失声痛哭起来,姑姑们也哭成了一团。瑞祥被哭声惊醒,光着屁股跑了出来,看着软绵绵的父亲,哇地哭了,这时大人们才发现了一丝不挂的孩子。
第二天,瑞祥发起了高烧,雪还在撕扯着天地,没有丝毫停下来的迹象。大人们只是细心地看顾着发烧的孩子,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危险。到了夜间,瑞祥开始说胡话,小脸烧得通红,脑门热得像是火炭一般。父亲急了,急忙去了生产队套车,等他赶着车回到家的时候,女人们已经是哭作了一团,原来瑞祥已经气若游丝了。看到车来了,她们忙手忙脚地把瑞祥抱上车,马车拉着父母孩子急急地向公社卫生院奔去。医生检查完嗔怪着父母:怎么搞的?再晚一会,孩子的命都丢了!原来瑞祥的病已经转成了急性肺炎。
瑞祥出院的时候,已经是大年三十了,别人家都在欢天喜地放鞭炮,可瑞祥家却是一片冷清。父亲没有吱声,出去了。不到一个时辰,他笑呵呵地进了屋子,一只手提着冻肉,另一只手提着一个纸包。他把肉交给母亲,把纸包放在炕上,打开,原来是长长的两挂鞭炮。“先放它一挂!”他笑着说完就拿着鞭炮出了屋,一家人都来到院子里,父亲把鞭炮挂到小树上,划着火柴,鞭炮就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
浓夏的艳阳高高挂在湛蓝的天空上,半人高的玉米舒展起油绿宽大的叶子尽情接受着阳光抚育,果园里已然泛黄的杏儿、羞的起了红晕的李子、青绿圆润的鸭梨、长着密密绒毛的夭桃、让阳光晒得发烫的细沙路,还有那个有深有浅的水塘,所有这些无不时刻在吸引着年幼好奇的小瑞祥。午饭将要结束的时候,奶奶一如既往地叮嘱着唯一的孙子:吃完饭跟奶奶睡觉,外边那么热总是疯跑会中暑的。妈妈更是坚决:就跑吧,大中午的,外边一个大人都没有,要是让贩小孩的抓去卖喽,你可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瑞祥有一搭没一搭地点着头,根本就没把这些话望心里装。一如既往,吃完饭就拿个枕头躺在了一边,因为旁边的父亲虽然没有吱声,他也不敢硬来,如果父亲一说话事情就麻烦了。屋子里很快就安静下来了,奶奶轻声唤了几声瑞祥,瑞祥假装睡着不吭声,奶奶以为孙子已经睡熟,就放心地躺下睡去了。过了一会儿,瑞祥睁开眼见大人们一动不动,就蹑手蹑脚地下了炕,光着小脚丫高抬腿轻落足,小心翼翼地出了屋,迈过堂屋门槛撒腿便跑。
到了村外,和早已等在树阴下的堂弟张嘎打过招呼。照计划他们今天是先要光顾许老头看着的果园子,大吃一顿后去水塘洗澡。心照不宣,两个孩子刷地钻进玉米地,径直向果园子里那棵白杏树靠过去。到了近前,两双小眼睛向四周逡巡几遍,见没什么动静就开始了行动。瑞祥一砖头上去,杏儿哗啦啦落了一地,小家伙兴奋之下正要冲出去拣,不好,许老头的屋子里冲出来一个壮汉,啊?许老头的儿子怎么在?瑞祥和张嘎顿时傻了眼。但很快瑞祥醒过味儿来,他让张嘎往东跑,自己往西,并如此这般说了几句就撒腿跑开了。大人追小孩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同时追两个就远远没那么容易,何况两个孩子各奔东西,哪个是头首先就得费番心思,擒贼先擒王嘛。因为张嘎个头高些,所以壮汉直接向张嘎奔去,张嘎不但个头高,身体也壮,所以跑的相对要快。但毕竟是个孩子,很快壮汉就接近了张嘎,瑞祥见时候到了就扯开嗓子,破口大骂那壮汉。壮汉怎么能忍受一个孩子的辱骂,于是撇开张嘎扭头来追瑞祥,张嘎又是如法炮制。如此几个回合,最后倒把那壮汉累倒在地。两个小家伙见阴谋得逞便拍着手欢声笑语地向水塘跑去。
水塘在村子的西口,水面很大,不是很深,最深的地方在正中央,大概有两米。此时天气正热,清凉的水面幽幽地闪着银光,格外吸引人。两个小孩子到了塘边,三下五除二,甩脱了衣服,扑通扑通跳了进去。沁人心脾的凉爽顿时让两个孩子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了,他们嬉笑着玩着水仗,慢慢地向水中央靠近。突然,瑞祥就觉得脚下一空,人便一下子没进了水里,还没来得及叫喊,水就猛得涌进嘴里。张嘎吓得妈呀一声,疯了似的冲上岸来,大声呼救。还好,水塘离住户很近,片刻工夫,闻声的人赶来纷纷下水,把呛晕的瑞祥抱了上来,懂行的人让孩子趴在腿上,瑞祥很快就吐出了几口脏水,眼睛也随之慢慢睁开了。
父亲闻讯赶来,他没有训斥自己的儿子,也没有埋怨与自己儿子同龄的侄儿,谢了众人后就领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可是,父亲并没有把他们领进家门,而是领进了村里的学校。学校很小,只有两个教室,教室也很破旧,干打垒的墙,木条窗户,窗户纸上戳满了窟窿。唯一的老师是瑞祥的堂姑姑,很胖,样子很凶。父亲叫她大姐,对她很客气,说:“大姐,这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他们是你的侄子,你可以随意管教他们,名字你就看着起吧!”胖姑姑很严肃地答应了。父亲没有更多的嘱咐,黑着脸离开了。
所以,祥瑞的大名——李祥不是他最亲近的人起的,而是他的启蒙老师按照他小名的原意定下的。
二
瑞祥上五年级了,那一年正是“文革”将要结束的1975年。就要过年了,正是数九寒天的季节,凛冽的寒风吹得大人们都躲进屋子聊天取暖。瑞祥顾不得寒气袭人约了几个同龄的小孩子一同到麦场抢球玩耍。麦场上精光一片,只有寒风掠着干而且发白的场院。他们唧唧喳喳的踢着皮球,皮球被一脚踢飞顺着风势向南滚去,滚进了麦场边的壕沟里,瑞祥蹬着风火轮般第一个追到。就在他将要触到皮球的刹那,伙伴们也冲了上来,众人一下子把他拥倒在地,就听嘎巴两声脆响,他就觉得左小腿像钢针扎过一样钻心的疼了起来。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大问题,只是要伙伴将他送到一个当村的土医生那里,医生也说无甚大事。当时天已然黑了,腿没有医好,一动就钻心的疼,父亲看着不行,第二天一大早就用自行车驮着他赶到了县医院。一路上,父亲不住地问疼吗?瑞祥尽管疼得脸上冒虚汗,咬住牙关就是不说疼字。父亲也宽慰他说:“就是嘛,男子汉就应该这样,看人家李玉和,让日本打得浑身是血,就是不当叛徒!”爷俩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三十几里地在不经意间走完了。
他们进了医院,找到骨科,X光一照,父亲的脸顿时白了:小腿骨全断了。给瑞祥看腿的医生是一个黑瘦的中年人,很严肃。他看完片子,闪亮的黑眼珠盯了一会儿瑞祥,像是在说调皮蛋看你还淘不?他向护士招招手,护士马上就推来了一辆铺着褥子的四轮车,医生示意父亲帮忙,于是他们把瑞祥搭到了车子上。四轮车由护士推着进了一间手术室,把瑞祥那条伤腿放在了一个显示屏下。通过显示屏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小腿的那两根骨头断成了斜茬。准备就绪,黑脸医生脱掉了白大褂,握住瑞祥的左脚,用力向下拽,瑞祥疼的再也忍受不住了,就尽情地大哭起来。过了好大一会,终于结束了,瑞祥也停止了号啕。借着泪眼,瑞祥见那医生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不住地从他黑瘦的脸上滚落,想必是要费很大的气力吧?瑞祥暗自为刚才的软弱而后悔,发誓以后坚决挺住,绝不再哭出一声。
从此瑞祥便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住院生活。医院里来往的人很多,他住的病房里有四张病床,其他的三张床上躺着的也是伤了骨头的病人,一个中年妇女,两个比他稍大点的男孩。伺候那个中年妇女的是她的丈夫,很和善,总是坐在瑞祥的身边讲故事,什么敌后武工队呀,什么雁翎队呀,什么雨来、小秃,都是他家乡的人物,虽然他也听父亲讲过这些,但没有这个人讲得那么有趣。
一连四天,每天黑脸医生都要给他检查一次腿骨对接的情况,最后一次医生的脸显得更黑了,他对父亲说:“这是第四次了,如果这次接上再滑开,孩子的腿就很可能残废了,我想接上后还是打石膏吧,这个得和你商量,因为石膏一旦打上,就不能打开,也就是说无论接的好坏,全凭他的造化了!”无奈之下父亲只能同意。还算万幸,等过了两天的又一次例行检查之后,黑脸医生终于长长的吁了一口气,父亲见状脸上也露出了几天来少见的笑容。
农村的家庭本来就是勉强度日,如果一旦发生什么灾难,那就非常艰难了。瑞祥家当然也不能例外,为了治好瑞祥的腿,父亲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卖光了,就是那头刚刚一百斤的肥猪也没能幸免,换的钱交了住院费。东厢房草垛上有几枚夏天没有拣到的鸡蛋,奶奶也没有舍得吃,让父亲带到了医院。父亲捧着鸡蛋,眼里含满了泪水,哽咽着对躺在病床上的孩子说:“你奶奶体弱多病,本应该多补补身子,可是家里哪有这个条件哪?拣了这么几个鸡蛋,她竟一个也不吃,全让我给你带来了,是你爸爸没本事啊!”瑞祥看着一向坚强的爸爸掉了眼泪,哇地哭出了声。病房的人都过来解劝,父子们才止住悲声,父亲像是有些尴尬,勉强挤出笑容算是和大家打了招呼。那几个鸡蛋瑞祥说什么也不吃,执意让父亲给奶奶带了回去。
经过这场灾难家里的生活更显得艰难了,无奈之下,坚强的父亲只好丢弃那种不信鬼神的信念,骑了一百多里地的自行车找到了那位名气很大的风水先生。
春节过后,瑞祥出院了,在家里又躺了两个多月,总算熬过了一百天,他终于可以坐起来了。这一天,奶奶正在忙活着给瑞祥做饭,突然门外有人高喊:“屋里有人吗?”从窗户上的玻璃,瑞祥看出来来人正是医院里给他讲故事的那个中年男人,奶奶当然是不认得。瑞祥急忙告诉了奶奶。那人进了屋,亲昵地摸摸瑞祥的脑袋,问了几句有关伤腿的话,又从包里拿出很多小孩吃的玩的东西,然后就和奶奶唠起了家常。不一会父亲也从地里回来了,两个男人像是老朋友重逢似的亲热地攀谈起来。突然,那人说话吞吐起来,脸上也泛起了微微的红晕,只听他对父亲说:“不瞒兄弟说,我虽年长你几岁,可是膝下没有儿子,只有几个丫头,我看你这儿子孝顺聪明,我想认个义子,不知道兄弟是否嫌弃?”几句突兀的话说得父亲也是一片茫然,好半天没回过神来。倒是恰好进屋的奶奶替他解了围,她笑呵呵地说:“大侄子真会讲话,我的孙子哪有那么好,这事啊,不急,等我们孩子妈妈回来再说也不迟啊!”话题就这么岔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