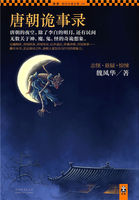在三月份我的生日到来之前,学校里发生的一切,我在这儿全都略过不提了。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斯蒂福思比先前更让人钦佩羡慕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他最迟在这一学期的末尾,就要离开学校。在我看来,他比以前更加潇洒不羁,因而也就比以前更让人喜欢了。可是除此之外,我已什么都不记得。当时留在我脑子里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它似乎把所有较小的回忆全都给吞没,独自留存下来了。
就连从我回校到我生日隔了有整整两个月这一点,也难以叫我相信。我只能认为事实是这样,因为我知道事实一定是这样,要不我就会认为它们之间没有间隔,我的生日是紧跟着我返校的日期了。
那一天的事,我记得真是太清楚了。我现在还能嗅到迷漫在四周的雾气,还能看到雾气中那朦胧的白霜,还能觉出那蒙霜的湿漉漉的头发披落在脸颊上。我看着教室中昏暗的景象,一支支毕剥作响的蜡烛,照亮着多雾的早晨。同学们一个个往手上呵气,往地上跺脚;他们呼出的热气,在湿冷的空气中像烟似的缭绕。
那是在早饭以后,我们已被从运动场召进教室,夏普先生进来叫道:
“大卫·科波菲尔,到小客厅去。”
我心里想,一定是佩格蒂给我捎来一篮东西了,所以听到这叫喊声我高兴极了。当我匆匆忙忙从座位上走出时,周围的一些同学都要求我分东西时别忘了他们。
“别急,大卫,”夏普先生说,“有的是时间,我的孩子,别急。”
他说话时那种充满感情的口气,要是我想一想,一定会感到吃惊,可是当时我没有去想。我急忙来到小客厅,只见克拉克尔先生正坐在那儿吃早饭,面前放着手杖和报纸;克拉克尔太太手中拿着一封拆开的信。但是没有篮子。
“大卫·科波菲尔,”克拉克尔太太把我领到一张沙发跟前,在我旁边坐下后对我说,“我特意把你叫来,是要跟你谈谈。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的孩子。”
我当然朝克拉克尔先生看了,可他只是摇着头,没有朝我看;他本来还想要叹气的,却让一大片涂了奶油的面包给噎住了。
“你还太年轻,不懂得什么是世事变化无常,”克拉克尔太太说,“什么叫人有旦夕祸福。可是这种事,我们都得经历的,大卫。我们当中,有的人年轻时就经历了,有的人到老了才经历到,还有的人一辈子老是经历这种事。”
我一直盯住她看着。
“你在假期结束离家回校时,”克拉克尔太太停了一会儿说,“你家里的人都好吗?”接着又停了一会儿,“你妈妈好吗?”
听了这话,不知为什么我全身都颤抖起来,只是依旧盯住她看着,不想回答。
“因为,”她说,“说起来很难过,我得告诉你,今天早上我听说你妈妈病得很厉害。”
一片迷雾突然在我和克拉克尔太太之间升起,她的身影似乎在雾中摇晃了一会儿。接着我觉得烫人的热泪流淌到我的脸上,她的身影也静止了下来。
“她病得很危险。”她补充说。
现在我全明白了。
“她死了。”
用不着这样告诉我了。我伤心地痛哭起来,觉出我已成了这个大千世界上的一个孤儿了。
克拉克尔太太待我非常仁慈。她留我在那儿待了一整天,有时还让我独自一人待着。我一直哭着,哭累了就睡着了,睡醒了又哭。当我再也哭不出来时,我就开始思索起来。当时我感到,我胸口的压力已沉重到极点,我的悲伤是一种使人木然、无法解脱的痛苦。
可是我的思绪非常散乱,并没有专注在重压我心头的巨大不幸上,而是在它的附近徘徊。我想到我们家门窗紧闭、一片静悄悄。我想到那个小婴儿,听克拉克尔太太说,他已经病了一些时候,非常瘦弱,他们认为,他也活不了啦。我想到我家附近教堂墓地中我父亲的坟墓,想到我母亲也要躺到我很熟悉的那棵树的下面。在留下我独自一人时,我站到一张椅子上,照了镜子,看看我的眼睛有多红,我的脸有多悲痛。过了几个小时后,我心里想,我的眼泪现在是不是真的流不出来了,要是果真那样,那我快到家时——因为我要回去参加葬礼——我得想到什么丧亲之痛,才能使我感到最伤心呢。我还清楚地意识到,在其他学生的心目中,我有了一种尊严的气派,由于我的不幸,我成了一个显要人物了。
要是说有哪个孩子曾真正感受过丧亲之痛,那就是我了。但是我却记得,那天下午,别的同学都在教室里上课,只有我独自一人在运动场上散步,我为自己变得这般显要感到很得意。他们去上课时,我看到他们一个个都从窗子里朝我看,我感到与众不同,便摆出更加悲伤的样子,走得也更慢了。下课以后,他们都出来跟我交谈,我觉得自己挺好,对谁也没有摆架子,对待他们完全跟从前一样。
我要在第二天晚上动身回家,不过坐的不是邮车,而是笨重的叫作“农夫号”的夜行马车,这种车主要是给乡下人作短途旅行搭乘的。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讲故事,特雷德尔硬要把他的枕头借给我用。我不知道他认为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因为我自己原本就有一个枕头。不过这可怜的人能出借的只有这件东西,除此之外,就是那张画满骷髅的信纸了。我们分别的时候,他把那张信纸给了我,作为对我悲哀的一种慰藉,帮助我的心灵得到安宁。
第二天下午,我离开了萨伦学校。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这一离开,就永远不回来了。车走得很慢,整整走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九、十点钟,我们才到达亚茅斯。我朝窗外张望,想寻找巴基斯,可是他不在。我只看到一个胖胖的矮老头,他外表欢快,走起路来直喘气,身上穿一套黑衣服,短裤的膝盖处镶有小束褪色的缎带,脚上穿的是黑袜子,头戴一顶宽边礼帽。他喘着气走到车窗跟前,问道:
“是科波菲尔少爷吧?”
“是的,先生。”
“请你跟我来,少爷,”他说着打开了车门,“由我送你回家,好吗?”
我把手放到他的手里,一面心里嘀咕,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们来到一条狭窄街道上的一家店铺跟前,店门上写着“欧默:零售布匹、服装、零星服饰用品,兼营服装加工、丧葬用品等”。这间铺子很小,屋子里很闷,店堂里满是做好的和没有做好的衣服,还有一个橱窗,里面摆满男式礼帽和女帽。我们走进店堂后面的一间小客厅。我看到有三个年轻女人正在干活,她们面前的桌子上摊着一些黑色布料,地上满是剪下来的布屑。屋子里有一只烧得很旺的火炉,还有一股暖烘烘的黑纱发出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气息。当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气息,不过现在我知道了。
那三个年轻女人,看上去非常勤快,干活显得很轻松。她们只是抬起头来朝我看了一眼,接着便又低头干活了。一针,一针,一针,飞快地缝着。同时,从窗外院子那边的一个工场里,传来一种有规律的锤子钉东西的声音;砰——嗒嗒,砰——嗒嗒,砰——嗒嗒,没有任何变化。“呃,”带我来的老头对三个年轻女人中的一个说,“明妮,你们的活儿做得怎么样啦?”
“试样时我们一准做好,”她没有抬起头,高兴地回答说,“你放心吧,爸爸。”
欧默先生摘下宽边帽,坐下来直喘气。他太胖了,不得不喘上一会儿气,才能开口说:
“很好。”
“爸爸!”明妮开玩笑似的说,“你真成了一头海豚了!”
“啊,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亲爱的,”他回答说,一面琢磨着发胖的原因,“我是太胖了。”
“你过得太自在了,你知道,”明妮说,“你什么事都不当一回事。”
“不这样有什么好处呀,我亲爱的。”欧默先生说。
“是啊,这倒也是,”女儿回答说,“谢天谢地,我们这儿全都开开心心的!是不是,爸?”
“但愿是这样,我亲爱的,”欧默先生说,“我这会儿已经喘过气来了,我想我得给这位青年学生量尺寸了。请到店堂里去好吗,科波菲尔少爷?”
听了欧默先生的话,我走在他前面,进了店堂。他先给我看了一卷布料,还告诉我说,这是特等料子,除了为父母穿孝使用外,做别的丧服就太高级了。说完,他就量我的各种尺寸,一边量,一边记在一个本子上。记尺寸时,他还要我看看他店里的存货,有些款式,他说是“刚流行的”,有些款式,他说是“刚过时的”。
“因了这种缘故,我们经常损失不少钱哩!”欧默先生说,“不过款式也跟人一样,没有人知道它们什么时候流行,为什么会流行,怎么流行;也没有人知道它们什么时候过时,为什么会过时,怎么过时。依我来看,一切都像人生,要是你用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
当时我太悲伤了,顾不上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即使在别的情况下,我大概也没有能力讨论这样的问题。欧默先生有些困难地喘着气,又把我带回到小客厅。
接着,他朝门后面一道很陡的小台阶下面喊道:“把那份茶和面包、奶油端来!”我坐在那儿,朝四周打量着,心里想着心事,耳朵听着屋子里的缝衣声和院子那边传来的锤打声。过了一会儿,茶和面包、奶油用一只盘子盛着端来了,原来这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我早就跟你认识了,”欧默先生朝我看了一会儿后说,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怎么去注意那份早餐,因为那些黑色的东西败坏了我的胃口,“我认识你已经很久了,我年轻的朋友。”
“是吗,先生?”
“你一生下来,我就认识你了,”欧默先生说,“也可以说在那以前。在认识你以前,我就认识你父亲了。他身长五英尺九英寸,他埋的那块地长二十英尺,宽五英尺。”
“砰——嗒嗒,砰——嗒嗒,砰——嗒嗒”,声音从院子那边传来。
“他埋的那块地长二十英尺,宽五英尺,虽说他只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欧默先生兴致勃勃地说,“这要么是你父亲的遗嘱,要么是你父亲的安排,我记不清了。”
“你知道我的小弟弟怎么样了,先生?”我问道。
欧默先生摇了摇头。
“砰——嗒嗒,砰——嗒嗒,砰——嗒嗒。”
“他在他母亲的怀里了,”他说。
“啊,可怜的小宝宝!他也死了吗?”
“你无能为力的事,就别操心啦!”欧默先生说,“是的,那娃娃也死了。”
听到这一消息,我的伤痕重新裂开了。我撂下那份几乎一点未尝的早餐,走到那小房间的一角,把头伏在那儿的一张桌子上。明妮急忙收拾掉桌上的东西,生怕我的眼泪会把上面的丧衣服给弄脏了。明妮是个模样俊秀、性情温和的姑娘,她用温柔的手轻轻地把我的头发从眼睛上捋开。但是,她因为快要完成自己的活儿,而且能及时完成,所以非常高兴,心情跟我完全不同!
过不多久,锤子的敲打声停止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穿过院子,走进了房间。他手里拿着一把锤子,嘴上衔着好些小钉子。他得先把钉子掏出来,然后才能说话。
“啊,乔兰!”欧默先生说,“你的活儿干得怎样啦?”
“好了,”乔兰说,“干完了,先生。”
明妮的脸上微微泛起了红晕。另两个姑娘相对微微一笑。
“什么!这么说,昨天晚上我上俱乐部时,你点上蜡烛开夜工了?”欧默先生说着闭上一只眼睛。
“是的,”乔兰说,“因为你说过,这活干完了,我们就可以去玩一趟,我们一块儿去,明妮和我——还有你。”
“啊,我还以为你们要把我给完全甩了呢!”欧默先生说着大笑,直到笑得咳嗽起来。
“——承你这么好心,说了那样的话,”小伙子接着说,“所以我就拼命去干了,你知道。你是不是去看看,给我提提意见?”
“我去看看,”欧默先生说着站起身来。“我亲爱的,”他又停下来转向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去看看你的——”
“不,爸爸!”明妮阻拦说。
“我本来想,这样做应该是合适的,我亲爱的,”欧默先生说,“不过,也许你是对的。”
我现在说不上来,当时我怎么知道他们去看的是我那亲爱的、亲爱的母亲的棺材。我从未听说过做棺材的事,也从未见到过我所知道的棺材,可是听到那连续不断的锤打声,我就想到那是什么声音了;而当那个年轻人进来时,我确信,我知道他在做什么了。
现在,活儿都干完了,那两个我没听到叫什么名字的姑娘,刷干净自己衣服上的线头、布屑,便到店堂里把店堂收拾整齐,等待着顾客的到来。明妮留在后面折叠好她们做好的东西,然后把它们装在两只篮子里。她跪着做这些事情时,嘴里哼着一支轻快、动听的小曲儿。乔兰毫无疑问是她的情人,在她正忙着时,他进来偷偷地吻了她一下(他对我一点也不在意),对她说,她父亲套马车去了,他得赶快去做好准备。说完就又出去了。随后她便把顶针和剪刀放进自己的口袋,把一枚穿着黑线的缝针利索地别在裙服的前襟上,照着门后面的一面小镜子,整整齐齐地穿上外面的衣服。从镜子里,我看到了她满面春风的样子。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坐在屋角的桌子旁看到的,当时我用一只手支着头,正想着各种各样的心事。马车很快就来到店门前,先往车子上放上那两只篮子,然后又把我扶到车上,跟着他们三人也上了车。我记得这辆车一半像载人的轻便马车,一半像运钢琴的运货马车,漆成灰暗的颜色,由一匹长尾巴的黑马拉着。我们都坐在车上,地方还很宽绰。
跟他们一块儿坐在车上,想到他们干的是什么活儿,看到他们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我认为我这一生从未有过这般奇异的感觉(也许我现在变得聪明一些了)。我当时并没有生他们的气,我更多的是怕他们,仿佛我已落到了一群在天性方面跟我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中间。他们都非常高兴。那老头儿坐在前面赶车,两个年轻人则坐在他身后。每逢他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朝前俯着身子,一个俯在他那胖脸的这一边,一个俯在他那胖脸的那一边,对他非常恭敬。他们也想跟我谈话,可是我避开了他们,愁眉苦脸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对他们的打情骂俏、又说又笑(虽然不到喧闹的程度)感到吃惊,我心里几乎觉得奇怪,他们这样铁石心肠,为什么竟没有受到惩罚。
就这样,当他们停下来喂马、吃喝和逗乐时,凡是他们动过的东西,我就决不去动,一直坚持禁食斋戒。因此,当马车刚刚驶到家门口时,我便尽快地从后面溜下车来,免得在那些充满严肃气氛的窗子(它们原来晶莹明亮,现在却像闭眼瞎子似的看着我)跟前,跟他们混在一起。哦,看到我母亲房间的窗子,还有隔壁我那间卧室(在当年美好的时日里)的窗子,哪里还有必要在回家时想些伤心的事来促使自己流泪啊!
我还没走进屋门,便扑倒在佩格蒂的怀里了。她把我领进家门。她刚一见到我时,伤心得哭起来了,不过很快就控制住了。她低声说话,轻轻走路,好像生怕会打扰死者似的。我发觉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上过床了。她晚上依旧坐在那儿守着。她说,只要她这个可怜的、亲爱的宝贝还没下葬,她就决不离开她。
谋得斯通先生坐在小客厅里,我进去时,他没有理睬我。他一直坐在壁炉跟前默不作声地掉眼泪,在扶手椅上想着心事。谋得斯通小姐正在写字台旁忙着,台子上摊着信件和单据。她朝我伸过来冷冰冰的手指甲,用刺耳的嗓音低声问我,我的丧服是否已量过尺寸。
我说,“量过了。”
“还有你的衬衣什么的,”谋得斯通小姐说,“都带回来没有?”
“带回来啦,小姐。我把我的衣服全带回来啦。”
这就是她的坚定所能给我的全部安慰。我毫不怀疑,她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表现她所谓的她的自制,她的坚定,她的意志力,她的常识,以及她那令人讨厌的品性中全部恶毒的东西,心里是十分高兴的。她对于自己的办事才能,特别得意。她现在把一切都化之为笔墨,以此来显露自己的才能,对别的任何事都无动于衷。在那天余下的时间,以及后来的几天里,她从早到晚都坐在那张写字台旁,用一支硬笔泰然自若地写着,用同样沉着冷静的态度跟每个人低声说话,脸上的肌肉从未松开,说话的口气从未温和,身上的衣服也从未蓬乱过。
她的弟弟有时拿着一本书,但是据我看来,他根本没有在看。他打开书本,朝书上看着,像似在看书,可是整整一个小时,从来不曾翻过一页,然后又放下书,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我一直合着双手坐在那儿看着他,一小时一小时地数着他的步子。他很少跟他姐姐说话,跟我则一句也没说。在整座死寂的房子里,除了时钟之外,他好像是唯一不安静的东西了。
在葬礼前的这几天里,我很少看到佩格蒂,只是在我上下楼时,我老在我母亲和她的婴孩停放的那个房间近旁看到她。除此之外,每天晚上当我要睡时,她就来到我的房间,坐在我的床头陪着我。在葬礼前一两天——我想是在这之前一两天,不过在那段沉痛的时日里,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根本没有注意到时间的进程——她把我带进那间房间。现在我只记得,在床上一块白罩布的下面,我觉得好像就是这屋子里庄严肃静的化身,床周围是一片很美的洁白和清新。当佩格蒂正想把罩布轻轻掀开时,我叫了起来,“哦,不要!哦,不要!”并抓住了她的手。
即便葬礼是昨天举行的,我也不可能清楚地记得了。当我跨进那间最好的客厅的门时,就感受到客厅里的那种气氛,壁炉里闪着熊熊的炉火,瓶子里的酒在闪闪发光,各色各样的杯子和盘子,糕点的微香,谋得斯通小姐衣服的气息,还有我们全都穿着的黑衣服。齐利普医生也在房间里,他走过来跟我说话。
“大卫少爷,你好吗?”他和蔼地说。
我不能对他说我很好。我把手伸给他,他握住了我的手。
“哎呀!”齐利普先生亲切地微笑着说,眼睛中像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我们周围的小朋友都长大了。他们大得我们都不认识了。是不是,小姐?”
这是对谋得斯通小姐说的,但她并没有搭理。
“这儿比从前更好了,是吧,小姐?”齐利普先生说。
谋得斯通小姐只是皱一皱眉头和稍微点了点头,作为回答。齐利普先生碰了这两个钉子后,便握着我的手走到一个角落里,不再做声了。
我所以记得这一点,是因为我记住了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因为我关心我自己,或者我回家以来一直关心自己。现在,铃声响了。欧默先生和另一个人走了进来,要我们作好准备。正像佩格蒂时常告诉我的那样,多年以前给我父亲送葬的那些人,也是在这同一间屋子里作好准备的。
参加送葬的有谋得斯通先生,我们的邻居格雷珀先生,齐利普先生,还有我。我们走到门口时,抬棺材的已经抬着棺材在花园里了。他们走在我们的前面,沿着小径,经过那些榆树,出了栅栏门,来到教堂墓地;这儿,每逢夏天的早晨,我经常听到鸟儿在歌唱。
我们站在墓穴的四周。这一天,我觉得跟任何别的一天都不一样。那天的天色,跟往日也不相同——显得格外惨淡。这时,四周一片肃然的寂静,这寂静是我们和即将入土安息的人从家里带来的。当我们都光着头站立在那儿时,我听到了牧师的声音,在露天之下,它好像从远处传来,但是清晰明白,他说,“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接着我便听到了呜咽的声音。在离我站的地方一段距离的旁观者中,我看到呜咽的原来是那位善良而忠诚的女仆。在世间所有的人中,她是我最爱的人。我这颗孩提的心完全相信,总有一天上帝会对她说“做得好!”的。
在那一小群人中,有不少我熟悉的脸。其中有的是我在教室里四处张望时见过的;有的是在我母亲充满青春活力初来这个村子时就认识她的。可是我并不关心这些脸——除了我的悲痛,我什么也不关心——不过我看见了他们,也完全认识他们;就连远在人群背后,正在张望的明妮,我也看到了。她的目光还时不时落在站在她近旁的情人身上。
葬礼结束了。开始往墓穴里填土,我们转身回家了。在我们的面前,耸立着我们的房子,仍旧那么漂亮,毫无改变,它使我在心中联想起过去发生的事情;跟眼下唤起的悲痛相比,我过去的那些悲痛都算不得什么了。他们带着我朝前走着,齐利普先生跟我说着话;到家时,他还给我喝了一点水;当我向他告辞,要上楼回自己的卧室时,他带着女人似的温柔跟我分了手。
所有这一切,正如我所说的,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至于后来发生的事,全都离我而去,漂向大洋彼岸了,一切忘却的事将要到那儿才能再现;可是这一天的事,却像一块高大的礁石,屹然耸立在大洋之中。
我知道佩格蒂一定会到我房间里来的。当时那种安息日般的宁静(那一天很像星期天!我把它给忘了),这对我们俩都很适宜。她跟我并排坐在我的小床上,握着我的手,有时还把我的手贴到她的嘴唇上,有时她又用自己的手轻轻抚摩着我的手,就像在哄我的那个小弟弟一样。就这样,她用自己的方式,给我讲了发生的一切。
“有很长一段时间,”佩格蒂说,“她一直觉得不很好。她心里总是恍惚不定,闷闷不乐。孩子生下后,我起初以为她会好起来,谁知反而更虚弱了,一天天地差下去。没生小孩前,她老爱一个人坐着,接着还会哭起来;生了小孩以后,她就老爱给小孩唱歌——她唱得那么轻,我听了以后,心里曾经想,这声音就像飘向空中,就那么飘走了。
“近一段时间来,我觉得,她变得更加胆小,更加惊恐不安了。对她说一句重一点的话,就像打了她一拳似的。不过她对我还是老样子,对她的又笨又傻的佩格蒂,她是决不会变样的,我的宝贝女孩是不会变的。”
说到这儿,佩格蒂停住了。她轻轻地拍着我的手,拍了一会儿。
“我最后一次看见她像原先的样子,是你放假回来那天晚上,我亲爱的。你离家回校那一天,她对我说,‘我再也见不到我那可爱的宝贝了。我觉得是这样。我知道,事情真的会这样。’
“在那以后,她还竭力支持了一段时间。有好几次,他们说她不动脑子、漫不经心时,她还装出承认是这样的样子。其实,当时她根本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了。她从来不曾把对我说的话告诉过她的丈夫——她怕对别的任何人说——直到有一天晚上,那是在出事前一个多点星期,她对她的丈夫说,‘我亲爱的,我想我就要死了。’
“‘我现在去了一桩心事了,佩格蒂,’那天晚上我侍候她睡的时候,她对我说,‘他愈来愈相信我说的话了,这可怜的人,他在这几天里,会一天比一天更相信的,然后一切都会过去。我太累了。如果这像是睡眠,那在我睡的时候,你就坐在我旁边,别离开我。愿上帝保佑我的两个孩子吧!愿上帝多多保佑我那没有父亲的孩子!’
“打那以后我一直没有离开她,”佩格蒂说,“她也时常跟楼下那两个人说话——因为她爱他们;对她周围的人,她是没有一个不爱的——不过当他们从她床前离开时,她总是转向我,仿佛只有佩格蒂在的地方才有安宁似的,要不她怎么也没法入睡。
“在那最后的一夜,那天晚上,她吻了我,对我说,‘要是我的小婴儿也活不了的话,佩格蒂,请你告诉他们,要他们把他放在我的怀里,把我们埋在一起。’(他们这样办了,因为那可怜的小宝贝只比她多活了一天。)‘让我那最亲爱的小宝贝跟我一起去我们安息的地方吧!’她说,‘你还要告诉他,说她母亲躺在这儿时,为他祝福过,不是一次,而是上千次。’”
说到这儿佩格蒂又默不作声了,她又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的手。
“一直到深夜的时候,”佩格蒂说,“她向我要水喝。喝了以后,她对我微微一笑,哎呀!——漂亮极了!
“后来天亮了,太阳正在升起。这时她对我说,科波菲尔先生待她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温存体贴,对他总是那么宽容;每当她对自己信心不足时,他就对她说,一颗仁爱的心,比智慧更宝贵,更有力量,由于她有这样一颗心,他感到很幸福。‘佩格蒂,我亲爱的,’接着她说,‘让我跟你挨得更近一些,’因为当时她已经非常虚弱了,‘把你那好心的胳臂放到我的脖子下面吧,’她说,‘把我转向你一边,因为你的脸离我太远了,我要跟它靠近一点。’我照她的吩咐做了。哦,大卫呀!那一时刻已经到了,我第一次跟你分别时说的话,应验了——她高兴地把她可怜的头放在她的又傻又笨、脾气又坏的老佩格蒂的胳臂上——就这样,她像个睡着的孩子似的,死去了!”
佩格蒂的叙述就这样完结了。打从我知道我母亲死时的情况那一刻起,她一生的最后那段生活,便从我的心中消失了。从那时起,我能记得的,只是那个给我留下最初印象的年轻母亲,那个老爱把自己发光的卷发在手指上一圈圈缠绕,以及常在黄昏时分跟我在客厅中跳舞的母亲。佩格蒂这会儿对我说的这番话,不仅没能把我带回到她一生的后期,而且使她的早期的印象在我心中扎了根。这说来或许有点奇怪,但事实确实如此。她这一死,就又飞回到她那宁静安详、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其余的一切全都消逝了。
躺在坟墓中的母亲,是我婴儿时期的母亲;在她怀里的那个小婴孩,就是我自己,像我当年曾在她怀里睡过那样,永远长睡在她的胸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