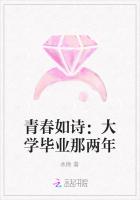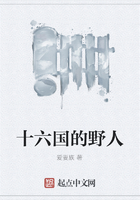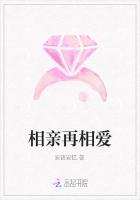整个民族的灭绝,就因为他的建国者是这样一个残暴的人。
我觉得骆以军是台湾近十年来最有创造力的作家。他苦学成才,上大学为了要学写小说的技巧,居然用最老套的方法——抄书,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巨著抄了一遍,把《百年孤独》也抄了一遍,甚至卷帙浩繁的《追忆似水年华》都抄过,简直是太变态了。
骆以军一出道就拿了很多文学奖,最新这部《西夏旅馆》得到2010年华语地区奖金最多的文学奖项“红楼梦奖”,在我看来是实至名归。这本书有四十七八万字,分上下两册,中间还夹附了一本作者的阅读笔记——《经验匮乏者笔记》。
小说家很在乎一样东西:经验。我们常说,任何艺术创作都需要比较丰富的人生经验,似乎一位作家的生活越是不堪,越是坎坷,就越能写出东西。相反,如果他含着金汤匙出生,从小到大一帆风顺,大概很难领略人生的种种不测与不幸,写作也会比较苍白乏力。
骆以军说:“对我而言,好写的东西有三样:少年、梦中的故人、鬼或者外星人;难写的东西有三样:贵族、博学者、说笑话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难易之分呢?其实都是因为经验的局限。”
“譬如太宰治的《斜阳》里,写贵族母亲,花丛中撒尿;或者章诒和写落难贵族灰扑扑年代的家庭巨宴——后巷一干侍女,由丈夫择也,换上华丽旗袍的场面,真是抓耳挠腮,心羡亦不是,临帖亦不是。”
他无论如何都写不好那种贵族生活,因为他没这个经历。但如果把这件事反过来,纵使你生活经历丰富,当过海上船员,游历世界各地,并不保证你能写出好作品。经验同时是一种主观感受,需要有一套框架去把生命中遭遇的事情承载起来,理解它,辨别它,使之成为有意义的事。譬如看到街边一个蜷曲身子的老太太,若是不敏感的人,可能只把她当成一道寻常的都市风景。但你如果敏锐一些,说不定会联想到她的身世……
经验就是这么来的。所以骆以军讲的经验匮乏,指的不是生活经历的匮乏,而是缺乏一套能够把生活经验组织起来的框架。他羡慕很多大陆作家不只经历过时代的沧海桑田,而且仿佛被赋予了一种叙事能力,去描述生命中事件的起承转合。
骆以军的生活经验有限,于是他拼命读书,在书本上为自己虚构出一个框架,如此就产生了一种带有书面感倾向的文字,跟大陆作家常常给人的口语感觉不一样。骆以军的作品强调“性”、“暴力”、“家族故事”,那些华丽的遣词造句背后是一大套近乎狂乱的想象力。这想象力愈演愈烈,每一次好不容易接近问题的核心,写出一些东西,又发现还有一些东西不够深入或被忽略,于是从头再来。《西夏旅馆》可以说是他过去所写题材的重现,而且写得更充满魔性的猖獗。
骆以军的父亲二十多岁跟着蒋介石来台,与过去生活的土地、族群全部切断,在陌生岛屿重新开始。这一代人常常怀念过去,回想那片失落的土地,可是当他们年老时真的有机会返乡,才发现那个现在的故乡早已是“他乡”了。骆以军在外省人的圈子长大,听大陆各地方言,吃大陆各地食物,想象那里的种种故事。然而一出门看到的是台湾本土之物,遇见“本省”同学,感到自己是那样格格不入。虽然如此,他自己有了小孩以后,这孩子就会成为彻彻底底的台湾人,外省人在他这一代终结了。
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灭绝的部族:西夏。西夏王朝的奇妙在于,它曾经非常强盛,有自己的文字和政治制度,但很快就像烟一样在西北荒漠上消失了。这是一个谜一样的王朝,它的文字到今天仍不能被完全读懂。骆以军用小说的形式把西夏的灭亡表现出来,骑兵南下逃亡与“外省”第二代流落孤岛异曲同工。然而,他要讲的还不只是以古喻今反映台湾外省人的生活状态,而是要找出中国历史上那种消失的人,他们的命运和消失的过程。
所以,旅馆是他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意象,很多旅人在此经过、居住、留下故事,但终究会离开,徒留一些神秘传说。《西夏旅馆》里许多不同时代的人一个个华丽登场,又突然进入虚空中。那些破碎的记忆无法用完整的故事穿起来,你只能像在旅馆一样,将一间间房子随机地打开,一瞥不同门后那不同的世界。
《西夏旅馆》时间感绵密,人称常常变换,情节推动缓慢,贯穿其中的主角图尼克自称是西夏后裔。他聊起外省人的遭遇时说:“很多别的民族,比如说犹太人,他们有《圣经》,有《出埃及记》,或者印度人有《摩呵婆罗多》,伊斯兰教徒有《古兰经》,可以把他们个体存在遭遇的所有事情融合进一个很大的整体。可是,我们这些人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只能一代一代断简残章传递着单一一代所发生的故事。我们一代一代说故事的父亲们全是一片一片的鱼鳞,永远无法镶嵌组成一条鱼。”
书中还有一个人物是旅馆里的老鸨,年轻时当妓女招待过无数恩客,记得旅馆里的每一个客人。“她见过、听过太多这个旅馆全盛时期进住然后搬走的那些鬼魂幽灵的幻异故事了,她变成了这座旅馆的回忆。所以她说起故事来像是失去了‘房客离开房间便是永远离开了’的时空认知。后来住进来的故事,无法把原先占据房间的故事赶走,永远不会让它有空出来的旧空间,这也是这间旅店像蜂巢一般持续长大的原因。它被它吞食的故事撑着胀着。”旅馆成了一个像大脑一样承载记忆的空间。
这就是《西夏旅馆》的结构,繁复而饱满,很难用简单语言概括它的内容。书的最后一部分“图尼克造字”写得有趣,用了很多西夏文字,每一字下写一段故事,仿佛要去解读这些字的真实意义。但那意义其实是非常可疑的,因为西夏文字本来就是西夏王朝的建国者李元昊突发奇想,命令丞相硬生生造出来的。
当年李元昊首创的蕃学院里有一个陷于造字苦思困境的老学者,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替皇上造出来的字,根本覆盖不住那每天滋生冒出的新事物。比如就以新发明的杀人方式来说吧;就以遥远的海边那些我们不曾见过的名目繁多的鱼类来说吧;就以男人的嫉妒,女人的嫉妒,老人的嫉妒,帝王的嫉妒,对才华高于己者之嫉妒,对交际美貌者之嫉妒,对财富之嫉妒,对青春之嫉妒来说吧。这些不同的字,汉字里面都没有,我该如何从虚空里面乱捞乱抓来发明呢?”
骆以军从造字的困扰说到台湾外省人的心境,老学者无法为文字命名,他们也无法为自己命名,他们是一群脱汉入胡的可怜鬼。“这是一个新人类巨大工程中的故障品、怪物或作为比对基因学的抗原在试验后的抛弃物,被称为他们的我们,威胁了称为我们的他们的自我制造工程。”这些外省人觉得自己是被废弃的实验品,他们无法融入这个小岛,他们弄不清自己是谁,他们的残片的记忆、凋零的故事、断裂的历史,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每一代王朝遗民共同面对的东西。
其实很多台湾作家都喜欢谈这种遗民心事,骆以军的独特在于他不会把这些状态写成静态的哀伤,相反,他写得非常狂暴。他似乎想告诉大家,台湾外省人一切的失落、遗弃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他们本来就是一群活该要灭绝的物种,像西夏王朝最后一队骑兵不断逃亡,却又把救济过他们的村庄屠戮一番;他们越来越不像人,退化成野兽,或者说进化成更原始、更本能的物种。
他用黏稠、华丽而又委靡的语言去描写这个王朝中的暴力与性。有一章“杀妻者”写道:“他见异思迁,喜新厌旧,遗弃、嫉妒。面对被遗弃者,歇斯底里,而心虚佯怒,乃至于暴力相向,因嫉妒而起的谋杀,造谣,借刀杀人。对情敌一家的灭门血案,淫人妻女,杀了最忠实的哥们,然后上他娇滴滴的老婆,也就是你该称呼她当嫂子的那个。杀掉情敌,还有他的儿子。上了自己儿子的女人,你该称呼她媳妇的那个,或是送自己的妹妹上哥们的床,怀上他的野种,好整个谋夺掉他全部的家产。林林总总,眼花缭乱,应有尽有,简直可以开一间败德爱情故事博物馆。”
这段话讲的就是西夏的建国者李元昊。李元昊娶的七个老婆全被他杀死。第一任卫慕氏是他母亲家族的女子,后来他怀疑这个家族想夺权,于是诛灭整族人,甚至毒杀了自己的生身之母。想象这样的画面:“他的阿姨们,浑身是血地躲进他母亲的帐幕,掩面哭泣着:‘你那头小狼,那个从小我们替他洗澡,玩弄他小鸡鸡的男孩,带着人,提着刀,把外头杀得一片血海。’”他杀掉这些人之后,又觉得他跟老婆生下来的儿子也是那个阴谋叛乱的族群留下来的孽种,于是把儿子也杀了。
他对待他爱过的女人永远是:“杀杀杀,杀光那些曾经欢爱销魂的女体,那些握在掌心的白色乳房,用劲的时候,她们会发出难辨是恐惧、欢爽,或单纯是疼痛的哀鸣。”
第五个老婆野利氏跟他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生性善良,劝他老爸,不要老是那么喜欢杀人。他老爸一听就骂,怎么能够不杀人呢?这儿子和爸爸说着说着,就气死了。第二个儿子长得像他爸,性格也像,后来李元昊要替这儿子娶个媳妇,悲剧开始了。
“眼前这个将来的太子妃,他要夺取的那个女人,胯下似乎喷散出一种朦胧韵白的香气,像鼻涕虫钻进他的鼻腔,蠕爬进他的脑额叶。那个浓郁的香味越来越浓,在满殿朝臣大庭广众下,秘密地、持续地从她的裙胯下,繁花簇拥地朝着他包围而来。”
“他看到她的第一眼,就决定要杀掉自己的亲生儿子了”,“事情有点复杂,还得杀掉他现在很喜欢的野利皇后。和眼前这个发光的神物相较,她简直是一匹穿着绣袍的母骡子。”
整个民族的灭绝,就因为他的建国者是这样一个残暴的人。骆以军的整本小说充满了类似的狂暴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