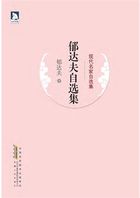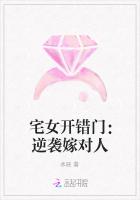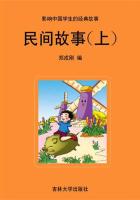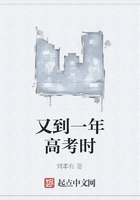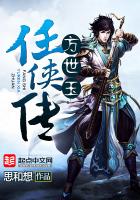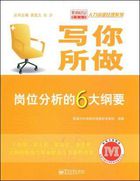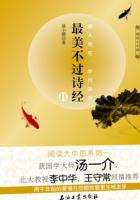二三十年前,涌现过一批知青文学。后来衰落了,但它的某些影响还在。比如《七十年代》这本书,其中的作者几乎都是下放的知识青年。有人认为那段日子太苦了,自己的光阴被虚耗了,说是去农村向农民学习,帮助农村建设,其实是荒废了人生中正常的求学阶段。
对于这些往事的看法多是从回城知青的角度出发。相反,当年知青下乡的时候,乡里的那些农民对这段历史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呢?《我与父辈》就描写过去被大家忽略这部分情况。作者阎连科先生过去写的小说常常让人觉得力量强悍,但这本书却回归到一种相当平淡的写作方式,甚至直白到让人有些不习惯。
在这本书里,阎连科谈的是他的父亲、大伯和四叔,他父辈那一代人。为什么要谈呢?书中一开始便说,忽然之间,他发现父辈全走了。2007年10月1日,当整个国家都在普天同庆的时候,他接到一个电话说四叔走了,之后他就发现父辈那整整一代人都不见了。他们曾经做过什么?说过什么?是不是应该把这些留存下来,说给后人知道?
他回忆起小时候跟父辈们相处的时光,那恰好是知青下乡的年代。有一天,大家正在田里劳作,不知道为什么,远处突然开过两辆载着革命青年的卡车,架着机枪从田间公路上驶过。那些红卫兵忽然朝着在田野里劳作的农民没头没脑地打了一梭子子弹,子弹就落在田头草丛里。草摇土飞之后,当过兵的退伍军人忽然大喊:“卧倒!”于是社员们都学着他的样子各自卧进红薯秧的垄沟,而卡车远去,载着青年革命者和他们的笑声。
看完这一段,你会怎么去想当年那些年轻人呢?那些知识青年、革命青年刚到乡里的时候,都觉得生活太苦了,但在当地老百姓看来,他们过的却是好日子。当地的农民很尊重这些年轻人,自己家里吃得不像话,还尽量做些细粮给知识青年吃,好活儿让给他们干,好事儿让给他们做,他们怎么还觉得苦呢?
有一段写得非常震撼,说有一个知识青年强奸了当地姑娘,跑了,后来什么事儿都没了。反过来,一个本地农村青年据说强奸了一名下乡女知青,而且仅仅是怀疑,没有二话,马上就被枪毙了。
作者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坛轰然而起的知青文学都把下乡视为炼狱,把一切苦难简单归结为某块土地和那块土地上的愚昧。知青下乡的确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就一直生存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几千年来的命运算不算是一种灾难呢?
这本书的力量就在于它直白而又沉着地描述了父辈们在农村
“过日子般的生活”,也附带提到了自己少年时的一些经历。那个时候他远离家乡,跟叔叔的儿子一起在一个工厂里打工。每天早上起床,拉着空车快步跑到三十里外的火车站,每人装上一车煤,再缓缓如牛地拉着重车回来,遇到上坡,还要走着S形一步一挪地慢慢上去。每天这么走,有时候连续做四十多天不休息,以至于连毛泽东去世了这样的事他们都不知道。
日子过得这样辛苦,有一次他哥说:“连科,你还回家读书去吧,读书才是正事……不读也行,读多了也不一定有用……明天周末,我们回去洗个澡吧。洗个澡,明天你好好睡上一觉……”两兄弟间的谈话,在他看来都是最为坦白也最为深刻的人生道理。他说:“那是一段我人生中最为辛苦的岁月,每每提起,都会欷歔掉泪。”
这样的写法好像没有什么文学修饰效果,可是当你看到后面
整段的文字谈他在农村的父辈和兄弟姐妹们怎样生了重病还要忍痛去种地,怎样受到羞辱而依然想要有尊严地活下去,怎样每天蹚过一条几乎是零度以下的冰冷的河只为了去远方砍木材、搬石头回来盖房……再回头看他说的“这是我人生中最为辛苦的岁月”,这“辛苦”二字的分量就非常扎实地落了下来。[1]
在《我与父辈》里,阎连科对他的父亲、大伯和四叔都作了非常深情的描述,书中有一段说他大伯的儿子,大我五六岁的发成哥,现在已经做了爷爷,可是他的子女们,那些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代人,却永远无法明白他的父辈们当年是如何为了生存而奋斗,为了婚姻而丢掉做人的尊严和舒展。
为什么说婚姻会使人丢掉做人的尊严呢?在农村谈婚姻是要有本钱的,比如家里有没有好房子,有了好房子你儿子才见得了人,人家才愿意把闺女嫁到你家。而以前农村的房子都是自己盖的,盖房真是非常辛苦。
他大伯家共有八个子女,你简直想象不出来这么多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尤其是“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其中的辛苦真是不足为外人道。有一年他的发成哥要跟别人相亲了,可是对方嫌男方家里穷、人口多,房子也不是瓦房。于是大伯就领着老老小小一家人每天去搬石头、砍木头,一片瓦一块砖地硬是搭起了一所简陋的房子。
盖房欠下了一笔巨债,一家十口平常还得吃喝过活,那时候种一天地只能赚一毛钱,怎么办呢?阎连科写道: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宣布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在新中国成立了二十多年后,一个北方乡村的农民站在他们一家人用血汗盖起来的三间瓦房门口,对着他的六男二女的孩子们说:“房子是盖起来了,债也欠下了。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欠,唯独不能欠的是人家的债。从明天起,我们一家人都去拉石头、卖石头,尽快把欠人家的债务还上!”
这是一些再简单不过的做人道理。父辈们就是这样,他们都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人,甚至连字都不认识多少,却有着最简单分明的是非观。他们教育子女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也很不科学,比如怀疑自己儿子偷了人家东西,就不分青红皂白先暴打一顿,打完之后看儿子还是坚决不认罪,才想到去问问清楚,到晚上确认他果然没有偷,便“叹一口气,摸摸他的头”。这样一种教育方法也许很不文明,但是阎连科却说,他现在多么盼望父亲再好好打他一顿,从前父亲每次这么打他,他都觉得非常踏实。
书中还提到他的大伯好赌,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心地非常宽厚。当年,大伯有个孩子去部队当兵,不知道为了什么,一个月之后就上吊自杀了,而且隔了大半年部队才敢让家里知道消息。这其中肯定有问题,他去问大伯怎么追究这件事:“‘铁成弟的事,就这样了结了?’大伯望着我,沉默了长天长地后,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去部队告他们,我知道会有人受处分,会把有的军官撤了职。可你弟弟死了,还能告活吗?处分了那些人,把那些军官撤职了,可那些班长和军官我问了,也都是从农村参军参到那里的,也都是家里无能无耐的,才不得不参军参到新疆的地界。人人都是从农村参军奔政治前程的人,你弟已经不在了,我们就别去毁了那些人的前程了。’”
这就是他的父辈,也是阎连科决心一定要记录下他们那一代人的原因。他前几年去世的四叔,从前在城里的水泥厂打工,看起来日子过得比较鲜活,到老年回到农村才发现自己是漂浮在半空的。他在城里打工的时候,城里人不把他当城里人;他偶尔从城里带一件好衣服回来送给农村的侄子们穿,家乡人又觉得他真是城里人。
城里人把日子叫生活,乡村人把生活叫日子,看上去似乎是对同一种事物的不同说法,本质上却有着天壤之别。日子是一天又一天,天天都一样,人在单调乏味中无奈地消耗着生命;而生活给人的感觉则是丰饶富足,有色彩、有人气、有宽阔的马路、明亮的路灯……然而到了最后,一个真正懂得了怎么去过日子的人,都是怎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啊[2]。
注释:
[1]“在赤贫之境中挣扎的父辈们却以亲情哺育儿女的善良感恩。亲情是养育善良的土壤、阳光和细雨。直到今天忆起大伯那次自杀的事,忆起父亲、大伯和叔叔间的兄弟情,忆起他们各自为了最普通的生存和人生中最普通的得失与过错,我都深刻地体会到,一个人的成长,最重要的需求不是物质的吃穿和花费,不是精神上大起大落的恩爱和慈悲,而是物质和精神混合在一起的那种细雨无声的温情与滋润。正如需要成长的草和树一样,缺光少雨当然不可以,可暴雨暴日的轮流与交替,似乎不缺水,不缺光,但最终迎来的却是不成材的疯生和疯长。而只有那种细雨无声的滋润和给养,只有那种光线充足却非暴晒暴烫的阳光和灼目的明亮,才可以让草成草,树成树,让人的心灵成为未来充满善与温情的一颗心……我是在充满贫穷与温情的家庭长大的。”(《我与父辈》精华摘录)
[2]“我的那些叔伯兄弟和姐妹们,也都是在充满贫穷与温情的家庭与家族中长大起来的。我们叔伯兄弟姐妹十五个,堂叔伯兄弟姐妹二十几个人,包括我,没有成才做官的,没有暴富到流金流油的,但没有一个不是善良的。没有一个不是把善良做为人生的底色后,再说在这底色之上去涂着别的色彩颜料,让人生尽可能的丰富、充满情谊和活着时多一些人间烟火的快乐与温暖……善良,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和源本……而家庭和家族中世代酝酿的亲情与温情,则是养育善良的土壤、阳光和细雨。”(摘自《我与父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