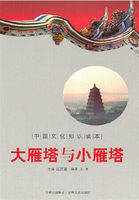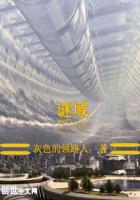林初青一直以为,亲情这种东西是需要培养的。
但很明显,她的观点错误了。
因为陆行恪表露出的哀伤,差一点要将她带回那段万劫不复的日子,她没道理怀疑他这些藏在眼睛里的情绪是假的。
可是他的表现越真实,她也越难过。
她油然记得他们第一次为这个孩子争执的早上,她摔门远去,他不加阻拦,喃喃自语:“我只是……”
她拿了银行卡里的钱去医院做了预约,他才后知后觉打来电话,意思是他要这个孩子。
她的骄傲不允许自己回头,即便他要,她也不会给了。
只要他曾经生过那种龌龊的念头,他就不再能成其为一个合格的父亲。
她坐在寂静里,越想越觉得凄凉,既然你曾经不要,现在又何苦将自己逼入这个境地。
陆行恪,你面对感情,其实恐怕同样不理智的很。
他们分床而据,一夜未眠。
林初青抱着那一本相册盘在床下侧卧,她在闹钟响起来的一瞬间还有踟蹰,以为自己身在什么异时空。
因为陆行恪自头至尾始终保持着疲累的姿势,现在的他看起来不堪一击。
她将怀里的相册放回抽屉,抚平压好。
然后她居高临下拍了拍陆行恪的肩膀:“起来吧,上班快迟到了。”
相较于林初青,他可以称之为死气沉沉了。
她在一夜之间,竟然见到了许多她以前从未见到过的陆行恪。
这一刻,他在她面前已非神祗,而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
她最后无奈,转身欲离开这个她不熟悉的陆行恪。
可她的手腕被及时扣住了,身后有床的响动,陆行恪起身了。
他一字一顿问:“我们的,孩,子,呢?”
到最后一个字,他几乎咬牙切齿,手上的力气随之加大。
林初青觉得生疼,手腕疼,心更疼。
她也不甘示弱,忍着涔涔冷汗,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回答他:“没有什么孩子了,早就没有了。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她吸了一口气,还是觉得心口闷生的厉害,于是接着说:“陆行恪,你在我说出你迟到了这种话后还不能理解,我就已经不想再跟你解释了。你非要逼着我再陪你走一遍那种痛苦的过程么?你非要这样吗?”
陆行恪在她咄咄逼人的问句里,颓然松了手。
他倒回床上,一手遮面,微不可闻地笑了一下,身体有轻轻的颤抖:“果然,我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明知答案的背后很可能是万丈深渊,我还是忍不住往下跳。可是初青,我多么不甘心。”
林初青默默无语。
他若不甘心,那么她呢。四年的养育,一夕间全成了泡影,Angel在生活里消失的干净,却永远在心里留下了烙印,谁人能知她有多么不甘心。
可她没有再盛势凌人地说出她这番感受,何必伤人伤己。
她还是选择离开这里,留他一人空追忆。
但她显然高估了陆行恪。
她以为他是如斯强大的人,怎么会走不出这样一个坎,可事实证明她用在他身上的论调都不太适用。
林初青将他放在房间里不闻不问,照旧出门上班,忙到天昏地暗筋疲力尽以驱赶内心巨大的空洞。
然后她正常下班,面容稀松平常,除了眼底憔悴,其它看不出异样。
她以为等她回到家,陆行恪已经自动消失。
但她房里依旧透着暖色的灯光,林潇潇拉着她的胳膊往里拖:“Mom,Mom,我觉得Uncle不对劲哎。你去看看他怎么了好吗?”
陆行恪果然还躺着,唇色苍白,四肢随意摊着,身上的衣服已经皱巴巴了。
她只是用指尖轻轻点了点他的眼皮,就被他骇人的高温吓到。
他居然发烧了,在她印象中永远刀枪不入的陆行恪,惊悚地在她房间里发烧了。
林潇潇嘟嘟哝哝埋怨她:“我打了好多电话催你回家看看Uncle,你都没有理我,现在信了吧。”
林初青连反驳的话都无法说出口。
最后她只能打120,因为陆行恪软绵绵的很不好摆弄,而且他一米八几的个子,她实在是搬不动。
救护车乌拉乌拉赶来,林初青没让林潇潇跟着,独自一人和救护人员一起进了救护车。
她对这一切无比熟悉,当年的车祸后,她也是这样亦步亦趋上了救护车,心焦难耐。
她没有料到这样一个消息对陆行恪的打击有这么大,颓废,示弱,生病,似乎都不应该发生在他身上。
但她确确实实遇到了。
医生的检查很迅速,没过多久就扯着单子来找她:“问题也不算很大,是病毒性感冒引起了发烧,加上轻微的并发症和肺炎。注意好好挂水吃药就行,不会住很久的院。”
林初青皱眉:“还需要住院?你不是说问题不大吗?”
医生冷眉倒竖:“怎么不要住院,虽说问题不是很大,但也是问题!你怎么可以拿病人的身体当儿戏呢?”
她也就不抱怨了,缴了费用,有在医院附近买了些口味清淡的食物回到病房。
陆行恪在打了退烧针后朦朦胧胧总算是醒了过来,辗转后地第一句话便是:“初青……”
“咔嚓”,她手里先前明明转的好好的苹果皮应声而断。
他竟然因为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微微笑了起来,冲她招了招手。
她面无表情地走过去,顺手帮他按了服务铃。
他只有打着点滴的那只手离她近一点,但还是碰不到她。
陆行恪挣扎不过,竟然一把撕开了胶布拔掉针头,毫不留情的样子看得她眼里心里皆是一酸。
然后他捉到了她垂在身侧的手,放在唇边轻吻:“初青,我们结婚。”
他的语气中没有任何看起来可以商量的字眼,即使是躺在病床上,他的态度也依旧强硬霸道。
这才应该是真正的陆行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