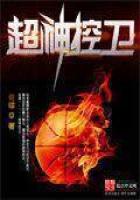情窦初开之龄,她记起戏园中看过的****悲欢,疑道:“二哥,人这一辈子总要喜欢一个人的吧,怎么可能不在乎什么,怎么可能无所牵挂。”
牧云凉极淡地笑笑,甚为轻蔑的模样:“谁说这辈子一定要喜欢谁,谁说这辈子一定非谁不可。方晗,人都是自私的,保住自己才最重要,只要自己还活着,就会有转机,就有一切可能。”
他惴惴教导如同兄长:“感情之事尤其莫测,一旦陷入再难抽身,方晗,男欢女爱人之常情,可捧场做戏,但别动真心。因为谁动了真心,谁就会输得一败涂地。”
她似懂非懂地点头。
牧云凉轻揉乱她的头发,指尖缓缓下滑,停在她的面颊之上:“朝堂不同别处,现今情势更是难料,一步踏错即是万丈深渊,所以第一要务就是学会保护自己。”
她歪着脑袋看他:“二哥,你有没有喜欢过什么?”
牧云凉静静地看她,墨眸若渊般深邃,良久道:“没有。”他顿了顿,收回落在她面颊之上的手,转过身,一字一句道,“没有谁非谁不可。”
七年之后,寂寥深夜,客栈之中。悲伤难抑间,她又记起牧云凉的教导,现在她才体会到其中含义。
方晗,人都是自私的。
方晗,男欢女爱人之常情,可捧场做戏,但别动真心。
谁动了真心,谁就会输得一败涂地。
没有谁非谁不可。
之前,她不肯信牧云凉,因为牧云凉总喜欢把事情想得很坏,仿佛世上之人全是随时会倒戈的恶人,需处处防备,仿佛事情转眼之间就会变得无可挽救,所以要做最坏的打算。而她往往将事情想得很好,认为总会一些人值得完全信任,认为柳暗后定会有花明之时。
现在她才明白,牧云凉的话并不全是在骗她。
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涟涟而落,她蹲在门口,哭得哽咽。
窸窣脚步声渐行渐近,停在她的面前。
有人俯身,将一块帕子递到她面前,温声道:“谁欺负你了?哭得这么伤心。”似曾相识的嗓音。
她抬头,便见那张极为熟悉的俊朗容颜。张口结舌,她半天才回神,磕磕绊绊道:“你、你怎么回来了?”
他扬了扬手中的药材包:“我出去买了点药。作为大夫,手中没有应急药物,总不太安心。”他怪异地看她,“你怎么了?哭得这么厉害,还蹲在门口哭,也不怕隔壁的客人出来跟你理论。”
她一跳而起,忙不迭抹去眼泪,窘得红了脸:“没、没什么。突然感伤而已。”说着转身进了房间,生怕他再问下去。
彭古意看着她落荒而逃的身影,不禁暗舒一口气。他本准备借此躲开她,但又担心她追上来,想了片刻,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索性身形一闪隐在尽头的储物间中,只待她追出去,他便反方向离开。
不料,她却蹲在门口哭了起来。
他听得极为郁闷,于是自储物间挑拣了些简单药材包好,拎着走出。
方晗怕他再提刚才之事,不再有先前的小动作,而是埋头用饭菜,恨不得三两口扒完就回自己房间。然而,她扒了三两口,又扒了三两口,再扒三两口……碗中菜肴不见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迹象。
她疑惑地抬眼,正见他夹菜放入她的碗中。
彭古意见她看过来,不闪不避,颔首道:“多吃点。”
她面颊微热,支吾地应一声,忙低头用饭。
“慢慢吃,饭后我为你换伤药。”他扫一眼她头面处的层层纱布,笑道,“包扎水平真不怎样,缠得这么丑。”
她窘迫着,不敢抬眼。
饭毕,彭古意唤人收拾了剩余饭菜,又着店小二送来伤药和纱布。他将她头面上的纱布取下来,用水清洗伤口,为她敷上新药,接着指尖抚着她的面庞,一圈圈轻绕而过。
方晗僵着身子,一动不动。
彭古意笑道:“将军怎得如此紧张,这是医伤,又不是上断头台。”
方晗尴尬地咳了一声,试图转移话题:“彭公子,我们的协议还有多久到期?”
“……五天。”
“今后有什么打算?”
“回临沧城,继续行医赚钱。”
方晗“哦”了两声,不再多话。
彭古意将纱布的尾端缠入先前的纱布中,包扎得利落清爽。
方晗见已处理完毕,起身笑道:“时间不早,我回房了,你休息吧。”
“不用,你今晚歇在这里。”他对上她惊愕的目光,若无其事道,“唐德元此行不成,定会着人四处搜拿你我。我想着分开只会增加彼此的危险,于是把你那间房退掉了。”
方晗停在门口,憋了半天,末了,着实想不出拒绝的理由,只得应了声“好”。
夜深了,熄了灯,两人躺上床,如先前般一内一外隔着尺许距离。
虽然同床共枕睡过许多次,但这次她却不禁紧张,僵着身子一动不敢动弹。了无睡意,强迫自己闭上眼,不料眼前却浮现出那晚旖旎情景,方晗忽然口干舌燥起来。
许久,不见他那边有动静,她鼓了鼓勇气,侧了眼目,试图觑他一眼。
然而,目光转来的刹那,正对上他注视的目光。不知何时,他竟侧转了头,一直在看她。
方晗慌得心跳如雷,目光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半晌,窘迫着强笑道:“你还没睡啊。”
黑暗中,他的神情不甚清晰。
方晗见他不答,讪讪地笑道:“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赶路。”说着就要转过身去。
彭古意叫住她:“方晗。”
她扭头看他,正要问何事。
然而,她还未开口,他的身影便已压下。灼热的吻铺天盖地,瞬时封住她的唇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