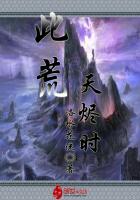果然,一个喝的醉醺醺的男人借着酒劲,不偏不倚地大胆无畏地向我走来,之所以说说他大胆无畏是当然是因为他喝了酒,喝了酒的人就是有种傻疯傻疯的劲儿,一到干起坏事来,这劲儿还能加倍。
我抬起头看见他的时候,他的同伴还拉了他几下,必然没拉住,而且被重重地甩了一耳光,当然是这个醉汉不小心,甩手的角度偏大的原因。但这一甩恰巧就铸成了这位拉劝者之后的旁观心态,以及更多人旁观而引起的一系列后果。
“小妹儿,被你男人甩了吧,别伤心!跟着哥哥,哥就喜欢你这号!”这种小混混我本来是不想放在眼里的,几句酒后疯言疯语我也不会放在心上,我要做的就是憋气憋气,然后走人。
我想绕道而行,但是他那只刚刚或许还握着酒杯畅饮的手已经向我粗暴地伸了过来,好吧,今天碰到的不只是个无聊想发泄的小混混,还是个自以为风流倜傥的年轻力壮的蜉蝣之流。
我躲闪着,对着他飘散的眼神怒目而视,显然毫不起威慑作用,我心想我要忍,没有什么忍不起的,你一个人热闹,哪怕我是那个被热闹的对象,我也以一种旁观者的心态看你。可是这个蜉蝣之流有一种令人厌恶的执着。
“躲什么躲,来这种地方你还装,也不看看你自己。”
我血气上涌,呼吸开始不均匀,我讨厌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他让我看看我自己,我不过一身最普通的打扮,我的T恤我的牛仔裤招谁惹谁了,哪里碍着他的眼,或者吸引他的眼了。
“你们女人就是会装!******一个个都是口是心非,都是毒蝎!”
这些个强加在女人身上笼统的绰号使我明白,原来这厮这股疯劲另有源头,一定是他和自己哪个相好的发生了矛盾,来这里把自己灌的烂醉,我不过是恰好用自己激烈的语言无意撞上了他激烈的思想,在我抗拒现实的时候,他正在抗拒思考,于是注定是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冲突。
“你这个白痴,你刚才说什么,你有种再说一遍。”我早说了,我是也是血性青年,他不仅侮辱我,还侮辱我所有的女性同胞,最重要的是以他这副熊样,根本一点资格都没有!我气愤,这种男人根本就该下地狱,让他在十八层地狱里一个人跟自己的思想厮磨。
我的手用力拽着他的领子,眼睛死死地盯着他,连我自己都能感受到从我自己眼睛里迸射出愤怒的火花以及冲动的波涛。
“妈的,你敢跟老子动手,滚开,给脸不要脸,硬往屎堆里蹭!”他很熟练地就把我的手甩开,仿佛这个动作他已经演练过千百遍,并顺势猛推了我一把。
我后来才知道,那一刻,我面对着穿制服,戴大檐帽的警察时,我已经泪流满面了,我本个头就不高大,一个女人泪流满面的样子实在与杀伤力无关了。我当时只是意识到,自己居然被现场逮着打架斗殴,要被拘留了。
该死的!我今天不是来拿书稿的吗,我不是打算翻译了这本书稿拿的了工资我就能买了礼物回家看老爸吗。我怎么跟这个小混混一路,跟他一路走向警车了呢。
更令我愤然的是那个约我到此的编辑老头儿至此都没有出现,而为了赴他的约而遭来这么一起祸事的我,却很可能面临着失去好多天的人身自由并被索赔医疗费。这该死的酒吧,该死的编辑,你们都该跟这个跟我打架的男人一起下地狱!
我以为事情就要按照这个趋势平庸地结束了,我最终还是不能明目张胆地去责怪那个编辑,而且还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接受批评,最后俯首帖耳地去请求他还是把书稿交给我翻译。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和出现的人,却完全改变了我想象中的一切,把我拉回到另一条人生轨道上去,让我心怀感激却历经沧桑,重新做回自己却重新改变自己。
从酒吧里走出来,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迎面而来的新鲜空气,第二感觉来自一股视觉冲击,那是街道拐角处的公安局,在纵深的街道末端,那个因距离而显得像个旮旯的拐角处。即使现在天空过于深蓝,夜色已有几分,我还是一眼就看见了它。
如果不是这段距离,我想我可能已经逃离现场,我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去,留下一个被打得找不着北的小混混理所当然地为他的肇事行为负责。
可酒吧老板是聪明的,他也许在某个角落里窥伺到这一切,因此他没有叫人,没有强行制止,一棒打晕一个,然后用敲诈勒索的数目要求我们赔偿一切损失。但也许他正是那个报警的!
总之事情到此,跟这一切偶然因素都有关。早知道公安局就近在咫尺,打死我也不出手啊,不出手我就是受害者,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受害者,然后在天下为公的警察叔叔面前我展示展览一下我受摧残的身心,毫无疑问我就可以走人了,当然还能能到赔偿。
可是他公安局的网点就是无孔不入,要不怎么是公安局,要不怎么保证人民的是人身财产安全。于是,在我人生的舞台上,出现了一个让我几乎抹不去的污点,我居然一斗殴者的身份被警察逮捕,在众目睽睽下,散射的杂色灯光下,由一个又壮又高,另一个很瘦也高的警察的隔空押解下,走向警车。
而这次和上次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
说实话,我很感激他们,因为通常我看见小说上电视上斗殴打架被举报的一干人都是先是二话不说就被警察兄弟制服得屁股朝天面贴地,一点反击能力都没有,一点威胁都构不成以后再押走,但是今天很神奇也很怪异,没有一个人碰我。
可是踏上警车那一刻我面对一片狭窄憋屈的空间,面对一群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我就悲从心生,我觉得对不起我们家身为警察的父亲,也对不起多次教导我请我吃饭的女警金蝉,对不起一****愿意记起或不愿意记起的人。
那一刻我居然听到一个来自天堂也是来自地狱的声音,那声音飘渺却不虚无,远远得传过来,像一股有着救赎力量的甘泉,滋润我久涸的心灵。
“等等!"
那是金蝉的声音,我从没觉得她的声音这么好听过。
“你们先别把她带走!”
在一个陌生环境陌生人群里穿透而来的熟悉音色,我于惊恐中万般期盼地转头一看,不费力地就看见金蝉身穿她的制服马甲,和一位中年的男警察一起走了过来。
我:“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金蝉:“夏荷,你不像个跟人打架的人,你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
我:“为了生存。”
金蝉:“你……”
我:“我他妈在这儿等那个该死的编辑!要不是他我能这么气愤吗!我能打架吗!”
金蝉皱着眉很严肃,即使这样我还是猜不透她在想什么,我准备着迎接她独特的训人方式,可她没有对我责备什么。
“同志,这是我朋友,她是来这儿等人的,我想中间可能发生了些误会。”金蝉很容易就在同类中找到了一个头儿,她说话寻求目标也能一发命中。
警察头儿:“可是这位女同志刚才打伤了人,目前还没有确定是谁挑起的争端,我们必须带她回局里调查。”
我:“女同志,女同志,领导您性别歧视啊?”
没人搭理我。
金蝉:“既然这样,我不妨碍你们办公,但是她现在情绪不好,如果态度上有什么使人不待见的地方,还请你们谅解,她平时很听话,如果事情严重,请你们打我的电话。”
警察头儿:“好的。”
金蝉又对身旁的那位警督说:“张叔,这就是我跟您说到过的那个女孩儿,她叫夏荷。”
张叔:“哦?是吗?今天真是巧了,如果真的照你说的那样,我想今晚的事情也应该是个误会。几位同志,小金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这么晚给你们添麻烦,真实幸苦你们了。”
警察头儿:“不敢当,麻烦算不上,不过我们一定尽快处理这件事情,请首长放心。”
金蝉掏出随身带的笔,把她的电话号码写在一张随手撕来的广告纸上,交给了这边的警察。
那天晚上金蝉刚刚值完班,而我推断那位看起来跟他关系不错的领导实际上一定在和她商量某件案子的调查方案或者聊着进展情况。后来我才知道,金蝉看见远处被带上警车的我时,那位姓张的叔叔正在给他说亲,而对象正是他自己的儿子。
也许一切都是机缘巧合,或者真有命中注定这么一说,从认识金蝉,到初见这位警督,我的命运也许就悄悄地在酝酿着,发生一些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事情。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可我,还是被带走了。我打架了,我这个女同志打架了。爸,我又闯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