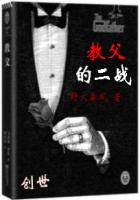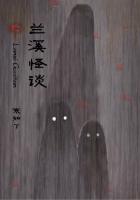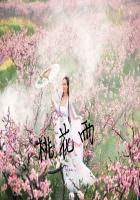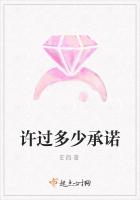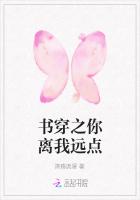依我的拙见,大家先不妨做一件工作。将近七十年前,陈寅恪先生提出了一个意见,我先把他的文章抄几段:
若就此义言之,在今日学术界,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未发展,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无过于对对子之一方法。(中略)今日印欧语系化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之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难也。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系统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概括万族,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变为普通语言学音韵学,名学,或文法哲学,等等,而不复成为某特种语言之文法矣。(中略)迄乎近世,比较语言之学兴,旧日谬误之观念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互相比较研究,于是系内各种语言之特性逐渐发见。印欧系语言学,遂有今日之发达。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盖不如此,则不独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因同系之语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绎递变隔离分化之关系,乃各自成为大同而小异之言语。故分析之,综合之,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之方面,比较其差异。由是言之,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胤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引文确实太长了一点,但是有谁认为是不必要的呢?寅恪先生之远见卓识真能令人折服。但是,我个人认为,七十年前寅恪先生的狮子吼,并没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好像是对着虚空放了一阵空炮,没有人能理解,当然更没有人认真去尝试。整个20世纪,在分析的微观的科学方法垄断世界学坛的情况下,你纵有孙悟空的神通,也难以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中外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又焉能例外!他们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分析微观的道路,这是毫不足奇的。更可怕的是,他们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与以分析的思维模式为基础的印欧语系的语言迥异其趣的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源头的汉语,其结果必然是用寅恪先生的话来说“非驴非马”、“认贼作父”。陈先生的言语重了一点,但却是说到了点子上。到了21世纪,我们必须改弦更张,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除此之外,还必须认真分辨出汉语的特点,认真进行藏缅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庶几能发多年未发之覆,揭发出汉语结构的特点,建立真正的汉语语言学。
归根结底一句话,我认为这是继承发扬赵元任先生汉语研究传统的唯一正确的办法。是为序。
2000年8月30日写毕于雷雨大风声中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
听到孟实先生逝世的消息,我的心情立刻沉重起来。这消息对我并不突然,因为他毕竟是快九十岁的人了,而且近几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如果他能再活上若干年,对我国的学术界,对我自己,不是更有好处吗?
现在,在北京大学内外,还颇有一些老先生可以算作我的师辈。因为,我当学生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教授了。但是,我真正听过课的老师,却只剩下孟实先生一人。按旧日的习惯,我应该称他为业师。在今天的新社会中,师生关系的内容和意义都有了一些改变。但是,尊师重道仍然是我们要大力提倡的。我对于我这一位业师,一向怀有深深的敬意。而今而后,这敬意的接受者就少掉重要的一个了。
五十多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念书,我那时是二十岁上下。孟实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三十四五岁吧。他只教一门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我选了这一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年。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做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
孟实先生在课堂上介绍了许多欧洲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新理论,比如李普斯的“感情移入说”,还有什么“人的距离说”,等等。他们从心理学方面,甚至从生理学方面来解释关于美的问题。其中有不少理论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忆不忘。要说里面没有唯心主义成分,那是不能想象的。但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只要是一个有良心、不存心骗人的人,他总是会在不同程度上正视客观实际的,他的学说总会有合理成分的。我们倒洗澡水不应该连婴儿一起倒掉。达尔文和爱因斯坦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吗?但是,你能说,他们的学说完全不正确吗?我们过去有一些人习惯于用贴标签的办法来处理学术问题,把极其复杂的学术问题过分地简单化了。这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这种倾向到了“十年浩劫”期间,在“四人帮”的煽动下,达到了骇人听闻的荒谬的程度。“四人帮”竟号召对相对论一窍不通的人来批判爱因斯坦,成为千古笑谈。孟实先生完全不属于这一类人。他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自己认识到什么程度,就讲到什么程度,一步一个脚印,无形中影响了学生。
离开清华以后,我出国一住就是十年。在这期间,国内正在奋起抗日,国际上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连八年,家书抵亿金”。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完全同祖国隔离,什么情况也不知道,1946年回国,立即来北大工作。那时孟实先生也转来北大。他正编一个杂志,邀我写文章。我写了一篇介绍《五卷书》的文章,发表在那个杂志上。他住的地方离我的住处不远。他的办公室(他当时是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我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和我的办公室相隔也不远。但是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我曾拜访过他。说起来似乎是件怪事,然而却是事实。现在恐怕有很多人认为我是什么“社会活动家”。其实我的性格毋宁说是属于孤僻一类,最怕见人。我的老师和老同学很多,我几乎是谁都不拜访。天性如此,无可奈何,而今就是想去拜访孟实先生,也完全不可能了。
我因为没有在重庆或者昆明待过,对于抗战时期那里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对于朱先生当时的情况也完全不清楚。到了北平以后,听了三言两语,我有时候也同几个清华的老同学窃窃私议过。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按朱先生的地位,他完全有资格乘南京派来的专机离开中国大陆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毅然留了下来,等待北平的解放。其中过程及细节,我完全不清楚。然而这件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先生毕竟是经受住了考验,选择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我常常想,解放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分为三类:先知先觉的、后知后觉的、不知不觉的。第一类是少数,第三类也是少数。孟实先生(还有我自己),在政治上不是先知先觉,但又决非不知不觉。爱国无分少长,革命难免先后,这恐怕是一条规律。孟实先生同一大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几十年的观察与考验、前进和停滞,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最终还是认识了真理,认为共产党指出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因而坚定不移地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孟实先生有一些情况我原来并不清楚。只是到了前几年,我读到他在抗战期间从重庆给周扬同志写的一封信,我才知道,他对国民党并不满意,他也向往延安。我心中暗自谴责:我没有能全面了解孟实先生。总之,我认为,孟实先生一生是大节不亏的。他走的道路是一切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走的道路。
这一条道路当然也决不会是平坦的。三十多年来,风风雨雨,几乎所有的老知识分子都在风雨中经受磨炼。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十年浩劫”。孟实先生被关进了牛棚。我是自己“跳”出来的,一跳也就跳进了牛棚。想不到几十年前的师生现在成了“同棚”。牛棚生活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在这里暂且不谈。孟实先生在棚里的一件小事,我却始终忘记不了。他锻炼身体有一套方术,大概是东西均备,佛道沟通。在那种阴森森的生活环境中,他居然还在锻炼身体,我实在非常吃惊,而且替他捏一把汗。晚上睡下以后,我发现他在被窝里胡折腾,不知道搞一些什么名堂。早晨他还偷跑到一个角落里去打太极拳一类的东西。有一次被“监改人员”发现了,大大地挨了一通批。在这些“大老爷”眼中,我们锻炼身体是罪大恶极的。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它的意义却不小。从中可以看出,孟实先生对自己的前途没有绝望,对我们的事业也没有绝望,他执著于生命,坚决要活下去。否则的话,他尽可以像一些别的难兄难弟一样,破罐子破摔算了。说老实话,我在当时的态度实在比不上他。这一件事,我从来没有同他谈起过,只是暗暗地记在心中。
“四人帮”垮台以后,天日重明,孟实先生以古稀之年,重又精神抖擞,从事科研、教学和社会活动。他的生活异常的有规律。每天早晨,人们总会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头在大图书馆前漫步。在工作方面,他抓得非常紧,他确实达到了壮心不已的程度。他译完了黑格尔的《美学》,又翻译维柯的著作。这些著作内容深奥,号称难治,能承担这种翻译工作的,并世没有第二人。孟实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和湛深的外语水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争分夺秒,锲而不舍,“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赞扬。
孟实先生学风谨严,一丝不苟,谦虚礼让,不耻下问。他曾多次问到我关于古代印度宗教的问题。他对中外文学都有精湛的研究,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他的文笔又流利畅达,这也是学者中间少有的。思想改造运动时,有人告诉我说喜欢读朱先生写的自我批评的文章。我当时觉得非常可笑:这是什么时候呀,你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来欣赏文章!然而这却是事实,可见朱先生文章感人之深。他研究中外文艺理论,态度同样严肃认真。他翻译外国名著,也是句斟字酌,不轻易下笔。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蜘蹰。”我在朱先生身上也发现了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解放后,他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现在,孟实先生离开了我们。他一生执著追求,没有偷懒。将近九十年的漫长的道路,走过来并不容易。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他都碰到过。顺利与挫折,他都经受过。但是,他在千辛万苦之后,毕竟找到了真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找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归宿。现在人们常谈生命的价值,我认为,孟实先生是实现了生命的价值的。
听到孟实先生逝世的消息时,我并没有流泪,但是在写这篇短文时,却几次泪如泉涌。生生死死,自然规律,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古人说:“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孟实先生,安息吧!你的形象将永远留在你这一个年迈而不龙钟的学生的心中。
1986年3月
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
读了本报指《文汇读书周报》。1993年8月11日《文学》王辛笛师弟(恕我狂妄,以兄自居,辛笛在清华确实比我晚一级)的《叶公超先生二三事》,顿有所感,也想来凑凑热闹,谈点公超先生的事儿。
但是,我对公超先生的看法,同辛笛颇有不同,因此,必须先说明几句。在背后,甚至在死后议论老师的长短,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尊师之道。不过,我个人觉得,我的议论,尽管难免有点苛求,却完全是善意的,甚至是充满了感情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要交代一点时代背景。
老清华人都知道,在30年代,清华大学同别的大学稍有不同,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有点“洋气”,学生在校刊上常常同老师开点小玩笑,饶有风趣而无伤大雅。师不以为忤,生以此为乐。这样做,不但没有伤害了师生关系,好像更缩短了师生的距离,感情更融洽。
这样说,有点空洞。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吴雨僧(宓)先生。他为人正直,古貌古心,但颇有一些“绯闻”。他有一首诗,一开始两句是:“吴宓苦爱×××(原文如此),三洲人士共惊闻。”当时不能写出真姓名,但是从押韵上来看,真是呼之欲出。×××者,毛彦文也。雨僧先生还有一组诗,名曰《空轩十二首》,最初是在“中西诗之比较”课堂上发给我们的。据说每一首影射一位女子,真假无所考。校刊上把第一首今译为:
一见亚北貌似花,
顺着秫秸往上爬。
单独进攻忽失利,
跟踪盯梢也挨刷。
下面三句忘了。最后一句是:
椎心泣血叫妈妈。
“亚北”者,欧阳也,是外文系一位女生的姓。这个今译本在学生中传诵,所以时隔六十年,我仍然能回忆起来。然而雨僧先生却泰然处之。
第二个例子是俞平伯先生。他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红学专家。在清华时,我曾旁听过他讲唐宋诗词的课。大家都知道,他家学渊源,是国学大师俞樾的孙子或曾孙,自己能写诗,善填词。他讲诗词当然很有吸引力。在课堂上他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而朗诵之。有时闭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于诗词的境界中,遗世而独立。他蓦地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在等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已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了。昔者晋人见好山水,便连声唤“奈何!奈何!”仔细想来,这是最好的赞美方式。因为,一落言筌,便失本意,反不如说上几句“奈何!”更具有启发意义。平伯先生的“就是好!”可以与此等量齐观。就是这位平伯先生,有一天忽然剃光了脑袋,这在当时学生和教授中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于是轰动了全校。校刊上立即出现了俞先生出家当和尚的特大新闻。在众目睽睽之下,平伯先生怡然自得,泰然处之。他光着个脑袋,仍然在课堂上高喊:“好!好!就是好!”
举完了两个例子,现在再谈叶公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