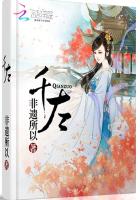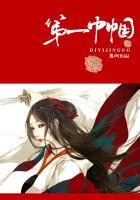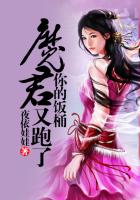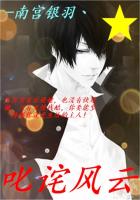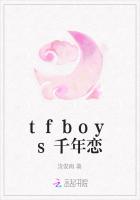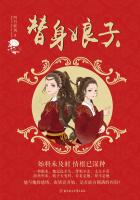因为时候还早,得到燕妃的允许后,我来到刚进宫时住过的屋子,里面的陈设一点都没有改变,让我徒生物是人非之感。这时,我感到有些内急,昭庆殿的路线图我自然熟悉的很,于是直奔出恭之所而去。转过两个回廊,在经过后花园出口处时,从一个角落里隐约传来两个宫女的窃窃私语。
“今天,我听一个在两仪殿执事的姐姐说,前不久宫里来了个道士,对陛下说姓武的人会谋反,结果陛下就把那个很得宠的武才人给贬到冷宫里去了。秀儿,你说这事儿是真的吗?”
那个被称为“秀儿”的宫女说:“不对,我表哥在太极殿当差,听他说那个道士叫李淳风,能算出五百年以后的事。他对陛下说‘唐三代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皇上想杀尽姓武的人,李道士又说杀不得。武才人因为姓武,所以失宠啦,是不是贬入冷宫我就不知道了。”
“哎,可我昨天去太极殿还看到武才人在服侍陛下批折子呢?”
“谁知道,没准已经贬成宫女啦!”
“唉,武才人得宠的时候多风光啊!想不到竟然有这种事,真够倒霉的。不过,能保住一条命就算不错啦!”
“嘘──,小声点!......”
......
后面的对话声压的更低,已经听不清楚。宫中向来壁垒森严,容易祸从口出,所以宫女的私议一般都十分小心,能听到这番谈话实属难得。没想到我无意中竟得知这惊天大内幕,原来那个“唐三代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谶语确有其事。我真为武媚娘捏一把汗。
不对,李淳风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听过,我甚至隐隐感到,自己曾经见过此人!可现在我什么头绪也理不清,只能我轻轻的走开,继续出我的“恭”去了。
晚膳时分,宫女传报:越王殿下到。
一身朝服的李贞步伐稳健地走了进来,对着燕妃就是一拜:“孩儿来迟,请母妃恕罪!”
燕妃慌忙上前扶起:“我儿快快起来,让为娘好好看看你。”
看着眼前这对小别重逢的母子,我忽然有种幻觉,就像看到当年的杨妃对李恪,我想也是一样的温馨吧。
我及时止住幻想。因为李贞正满含笑意地看着我。与以前相比,面前的李贞好像又长高了,身材更加颀长,五官也更加秀美,很像李恪,区别在于李贞总是一脸稚气未脱的笑容。
我躬身施礼:“遗墨见过越王殿下。”脑海里却总在回想曲江池的事情,不敢抬头看他。
李贞却丝毫也不拘谨,爽朗地笑道:“墨儿,好久不见,你怎么腼腆许多,以前的你可不是这样呀。”
原来李贞并不因为以前的事而耿耿于怀,是我多想了。我抬起头,正迎着李贞那友善而亲切的目光。我们相视一笑“泯恩仇”。
晚宴上我们相谈甚欢。不觉已月上柳梢,天色已晚。李贞和我与燕妃依依惜别,我们各回各府。李贞顺便送我。
秋风送爽,明月当空。在点点灯火与浓浓月色的交相辉映下,远处的万间宫阙若隐若现,更显壮阔华美,近处的水榭亭台婀娜幽雅,越发梦幻迷离。身处在这重重美景的环抱之中,我和李贞漫步在曲折蜿蜒的回廊上,向甘露门的方向走去。
看着眼前繁华似锦美不胜收的景象,我略感遗憾地想:此时若是李恪陪伴在我的身边该有多好啊!
“墨儿。”李恪轻唤我的名字。
“嗯?”我答应着。难道恪哥真的来了?我侧身一视,看到的却是李贞稚嫩而灿烂的笑脸。李贞不愧为公认的大唐第一微笑王子。在月色的掩映下,李贞的微笑更显温馨迷人。
原来又是幻觉。我这才发现,他们的声音也那么相像。难怪我第一天见他们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墨儿,你多大了?”李贞忽然问道。
“我多大?这......”
我不知该如何作答。在这里,我是房遗墨,今年十七岁,但是只有我清楚这不是事实。
“殿下明知故问。当然是十七岁。”我还算镇定地扯着谎。
“几月生的?”李贞不依不饶地追问道。
“唔,这个,五月吧。”这完全是我的临场发挥了。
李贞饶有兴致地击掌道:“原来墨儿比我大三个月,那么我该叫你墨儿姐姐啦?可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还称我为表哥呢!”
似乎这件骗吃骗喝的陈年旧事会一直成为李贞揶揄我的最佳把柄。我有些尴尬的笑笑:“遗墨怎么敢做殿下的姐姐呢?还是叫我墨儿吧。”心里却想:我何止是大你三个月的姐姐。
李贞忽然话锋一转:“墨儿,你可知道,父皇就要给我议亲,也许过不了几个月,我就要纳妃了。”言语之中有些许落寞伤感。
我却不配合的佯装欣喜状:“刚才听娘娘提起过,墨儿这里预先恭喜殿下了!”
李贞的微笑戛然而止,面上骤添郁结之气,他不无失落地说:“恭喜?恭喜我即将娶一个我不爱的人做王妃吗?”
李贞的直抒胸臆令我有些措手不及。的确,和一个陌生人结婚有什么值得恭喜的呢?现在的李贞不就像当年李恪被迫纳妃时一样痛苦吗?我有些后悔,为什么自己说话如此不经过大脑,说出那番欠斟酌的“贺语”。我轻轻跺着脚责怪着自己的冒失,却想不出一句可以挽回的话。
李贞像个孩子似的一歪头,用试探的口吻道:“难道墨儿你真的那么高兴看到我娶别人为妃吗?”
“这......”这是个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出答案的“刁钻”问题。
李贞则继续着自己的闷闷不乐:“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个中规中矩的皇子,父皇很少关注到我,我不感到失落;几位皇兄为大位之争势如水火,我无意介入;和我年纪相仿的九弟成为太子,我也并不羡慕。我的心愿就是做一个与世无争的皇子,娶一位心爱的女子做王妃,在封地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李贞的话让我不禁开始心驰神往,那不就是不久前我和恪哥一同憧憬过的美好未来吗?
刚走到一处拱桥边,刚才还很平静的李贞忽然上前急走两步,转而挡在了我的面前,用双手执住我的双肩,深情款款地注视着我。我不得不止住脚步站定。不知李贞意欲何为。
李贞用富有磁性的声音感性十足地说:“墨儿,此生能和你长相厮守是我一成不变的心愿,那日若不是你拒绝了我,我一定会启请父皇恩准我娶你为妃的!”
李贞不顾我的窘态,更加情真意切地表白道:“墨儿,我向你发誓,除了那最最至高无上的荣誉之外,我可以给你一切你想要的幸福!”
没想到曲江池一别,李贞对我的感情不仅未曾淡化,反而日渐浓郁。眼前李贞凌厉的告白攻势让我一时间手足无措,主张全无,口中喃喃道:“不,不,我不能......”目光颇为无助地向四处张望,希望有什么人适时出现可以化解目下这难以应对的场面。
就在这时,我发现在李贞身后不远处的桥中央立着一人:修长伟岸,气宇轩昂,一身素雅庄重的锦秀朝服,秀美而立体的五官在月色的映照下更显精致华贵。他像一尊雕像一样矗立在那里,神色冷峻地望着我。
是李恪!
顷刻间,我恍然不知身在何处。李恪为何会在这里?放眼望去,才发现在李恪身后不远处,静静屹立着的,正是庄严肃穆的淑景殿!每逢佳节倍思亲,重阳之夜,李恪定是念母心切,宫宴之后便来到此地睹物怀人,以解追思之情。
虽然今晚最想见到的就是李恪,然而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形下和他相遇。我负气地用力挣脱了李贞的双手,想要跑上桥去,却总也挪不动双脚,反倒是一身战战兢兢汗不敢出的惊惶之状。我怕极了刚才的一幕会令李恪有所误会。
而不远处的李恪,仍像一尊雕像一样立在那里。
李贞转过身,看到李恪,略显惊疑地拱手见礼道:“三皇兄!”
李恪缓步下桥,未发一言,冷冷地看了一眼早已红了面庞的李贞,蓝眸中射出一道凶狠锋利的寒光,似在厉声责问:“你刚才说什么?”
在李恪敌意深重的傲睨之下,李贞宛如不知错在何处的孩子一般,他看看李恪,又转眼看看我,现出满是无辜与疑惑的神情。
两人都需要我的解释,但此时的我早已脑中空空,口不能言。
奇怪的是,李恪凶冷的目光只在李贞的脸上巡视一番后就鸣金收兵了。当他再次看向我的时候,已经恢复了曾经的温情脉脉。
李恪丢下李贞,昂然走至我面前,高大的身躯挡住了空中的一弯明月,在地上映出深深的背影。
李恪轻轻抬起我的下巴,深沉而坚定地说:“你终究会真正成为我的人。”然后俯下身来,在我的唇上轻轻一吻。
在这个月色怡人的重阳之夜,在李贞惊奇的注视之下,李恪夺走了我的初吻。
吻罢,李恪俯在我的耳畔耳语道:“原来你的拥泵很多,不用怕,没有人能把你从我的手中抢走。”说完,目不转睛地直视着我,深邃的眼神中闪现出一丝狡黠的笑意,嘴角也微微上扬,露出绝美的笑容。与李贞阳光少年式的灿烂笑容不同,李恪很少笑,而他的笑容勾魂摄魄,美的令人窒息,有种无法抗拒的魔力。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半晌如痴如醉。平静后的我如释重负,以李恪的明察秋毫,无须我的解释,他已然明了刚才的一幕是怎么一回事,全然没有误会。他对李贞凶冷的目光其实是在宣誓“主权”,是一种震慑,同时也说明:他在吃醋。
当然,我不会忘记,此时此刻真正需要我解释的,是一直矗立一旁的李贞。
此时,在李贞的脸上再也看不到微笑。他的表情惊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嘴角轻轻抽搐着,眼神中透着无限的震惊、绝望,还有愤怒。眼角早已噙满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整个身体微微颤抖着。
“墨儿,我送你回府。”李恪不容分说地拉起我的手。
我回视李恪,他的脸上永远都是胜利者的自信,永远那么霸气十足。相比之下,李贞好像一只受伤的小鹿,楚楚可怜地在一旁默默舔舐着自己的伤口。
李恪轻轻握着我的手,拉着我走上了拱桥。
我怀着无比的歉意回头看了一眼仍一动不动立在原地的李贞,当眼泪无声地顺着李贞那俊美的脸庞流下的一霎那,他露出一抹凄惨哀怨的笑容。那笑容看得人越发心痛,好像在说:“我明白了,墨儿。”
那一夜,李贞的惨笑让我久久无法忘怀。对李贞,用这种突然而直白的方式以绝其望,是不是太残忍了?然而也惟有如此,才能让李贞彻底明白我爱的人并不是他。李贞,我万分的歉疚难以尽言。请原谅我深深地伤害了你的心,也请原谅我对李恪的这份情有独钟。
贞观十七年九月,庚辰,新罗遣使言百济攻取其国四十余城,复与高丽连兵,谋绝新罗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赐高丽曰:“新罗委质国家,朝贡不乏,尔与百济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发兵击尔国矣!
自魏晋以后,中原操戈终日不息,南朝划江偏安一隅,国乱纷纷,边关难顾。辽东地区的高句丽部族趁势崛起,攻城略地,割据一方,实力逐渐壮大,至隋时遂成气候。且野心膨胀,蠢蠢欲动,常怀不臣之心。隋炀帝因之不惜耗费国力,三征高句丽,可惜都功败垂成,铩羽而归。
自唐代隋有国以来,在李世民大帝英明神武的统帅之下,帝国的精锐部队在广袤的大陆上扫清六合,席卷八方,追亡逐北,凯歌频传,马蹄踏处,突厥、吐蕃、焉耆、高昌、吐谷浑、薛延陀纷纷降服,称臣纳贡,同举大唐天子为天下共主,尊为“天可汗”。
眼看是四海承平,万邦来朝,然而却还未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此时的高句丽虽然因为隋炀帝的数次征伐与自身政权频频内乱而实力大不如前,逐渐衰落,却野心未泯,不肯臣服于大唐,且异动连连,实为大唐一大边患。目下高句丽联合百济国侵犯依附于大唐的新罗国,新罗遣使告急,皇上遂有征伐之意。